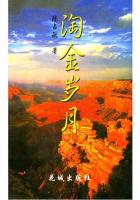记忆是一种会随风飘逸的东西,有时候会挂到树梢,有时候会洒落平地,常常由不得谁做主。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好像无所不能,可是对于自己的记忆是否重现以及重现什么内容、何时重现又常常显得苍白无力。香玲的记忆像山里的野兔,动不动就蹦出来,溜达溜达……
童年时代的常香玲,总爱缠着妈妈讲好听的故事,妈妈搜肠刮肚费尽心思也不能满足女儿精神需求的日益增长。于是经常将自己的经历编成故事,一段一段地讲给孩子听。从此,在香玲的幼小心灵里就埋下这样的种子:自己是父母自由恋爱的结晶,也是父母挣脱包办婚姻的束缚而结下的苦果。
和所有的青年男女一样,风华正茂的常香玲的父母看对眼(被丘比特箭攒射中)的时候,已经不再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当年,香玲的母亲被她姥爷视为掌上明珠,举到头上,怕跌着;含在嘴里,怕化了。那个时候,她在村里任幼儿教师,单调的学校生活也没有扑灭她爱情的火焰。她对英俊青年常江波的喜爱,如雨后春笋,一夜之间冒出来。到了纸里包不住火的时候,才传到香玲姥姥和姥爷的耳朵里,膝下无儿的夫妇如闻惊雷。他们规划的未来女婿的蓝图是:一军官,二机关,三工人,四教师,宁死不嫁这庄稼汉。虽然江波人长得不错,但是不仅是个庄稼汉,还出身于富农家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把女儿嫁到这样的家庭无异于将女儿推进火坑。可是涉世不深的女儿怎么能懂得这些,何况踏进爱河的人是最不能自拔的。她父亲当时就扬出风来,就是把闺女放到猪圈里攒粪也不嫁给这庄家老。何况当时已经有媒婆给她介绍一个在外地广饶上班的国家干部,还互相交换了照片,虽然是四个眼(戴近视眼镜),瘦得像刚刚提出来的排骨,毕竟是国家干部。她不管你干部不干部,就是看不上,开口闭口说拉倒,也不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起初,香玲的姥爷好言劝,让女儿跟江波散伙。香玲的母亲却像吃了秤砣铁了心,好歹不识金镶玉。各种原因只有她自己明白,自己找对象挑着样找,江波虽然人品不错,一表人才,但那年月媳妇并不好找。如果走到现在自己跟他吹了,这不是耍弄人家吗?对他的打击将是无法估计的,也将是致命的。很显然,香玲母亲在深深的爱情里还掺杂一些对时代的叛逆和对江波的怜悯之情。这样的婚姻如同绑上定时炸弹,应该说是潜在着危险的,说不定哪一天就会爆炸,就会出乱子。对此,香玲母亲凭自己那点阅历怎么能知道?
香玲的姥爷先礼后兵,见女儿一旦拿定主义就是套上三头老牛也拉不回来,不管是用情,还是用理,都不能将自己的女儿打动,就是用钢钎撬也无济于事。于是,施出最后一计,竟然将女儿软禁起来,提供吃穿,不准跟外界接触。谁知香玲母亲就用绝食抵抗,不吃不喝,以死威逼。谁知道这下子捅了马蜂窝,从小没舍得打女儿一下的香玲姥爷将对女儿的爱全都化为一场冰雹,在一个乌云密布的晚上,陡然降落。他先把老婆支出去,然后将门关严,逼女儿拉倒。所有的门窗都如同变魔术一般事先关闭。当人们在外面叫门,陈述他们的请求时,没有人回答。这场戏导演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狠。
见女儿大米换粲子——十声(升)换不出一声(升),始终不理不睬。他拿出白天准备好的绳子,折成四股,没头没脑地朝女儿身上打去。香玲母亲从来没吃这么大的苦头,浑身上下如乱箭穿心,叫喊声撕肝裂胆。但是,尽管拼命大喊,却依然不屈不招。当时的情形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哭声从窗户缝里钻了出去,在漆黑的天空中回荡,香玲的姥姥未进家门,先闻其声,觉得味道有些不对头,撩起“三寸金莲”往家赶。门闩紧紧地插着。她叫门,无人理会;敲门,没人开门,竟然一时慌了手脚。邻居们听到喊声,从墙头上爬进去,撞开门。只见香玲母亲披头散发,衣衫褴褛,伤痕累累,顷刻之间变成了《红色娘子军》里被南霸天打得遍体鳞伤的吴清华。香玲姥姥顾不上跟老头子算账,抱着女儿哭成泪人……痛哭声吸引了众多的街坊,有的从窗户中探出头来,而更多地人则从不同的方向走到大街上悄悄议论,甚至惊讶得目瞪口呆。
半个月以后,在众多离乡背井闯关东的盲流中多了一对青年夫妇。女人身上的伤口已经痊愈,心灵上的创伤还在滴血。他俩几经周折,几经流离,落脚在关东的一座小城。男的到火车站当了火车道搬道岔的临时工人,女的有零活就干一点,无活就闲居在临时的家里。日久天长,周而复始。他俩本来准备先斩后奏,将生米做成熟饭后再一锅端出,抱着孩子回家,她父母就是一万个不愿意,也于事无补。
岁月悠悠,斗转星移,时间将当年的壮小伙子雕刻成一个男子汉,也将当年的黄花姑娘雕刻成了半老徐娘。常江波以山东大汉特有的忠厚能干,博得了周围人的好评,不久,转为正式工,有了固定的工作,就在异地他乡安营扎寨。抱着哪里的黄土都养人的满腔热忱,驱散了缠绕在他俩心头多年的回乡梦幻,让他们把根紧紧扎在肥沃的东北大地上。
江波媳妇也一发而不可收拾地为他生了两女两男,刚出来时的小两口,几年的时间,演变成了一个有几口人组成的大家。
世界上的事物大概都遵守这样一条发展规律:就是物尽其长吧!常江波一天到晚泡在铁路工段上,媳妇自然成为家里的“一把手”。她理家的才能也在不知不觉中滋生暗长。一家几口需要的油盐酱醋,全由她一人办置。孩子们的吃喝拉撒睡,全由她一人张罗。她一天到晚进进出出,忙里忙外,不分白天黑夜地奔波操劳。有时候披星戴月出,有时候深更半夜回;有时候不知道是星期几,有时候忘了是初一还是初五。云天的日子分不清头晌还是下午,甚至有时连饭吃过没有都不记得,总算把家操持得有点模样。可是捉襟见肘的日子并不少见,经常还要吃探头粮。
江波媳妇是个要强的女人。她不肯把今天要洗的衣服拖到明天去洗,她更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穿得比别人家的孩子差。即使是旧衣服她也要浆洗得干干净净,缝补得整整齐齐。妈妈精心打扮自己的儿女,给女儿留下的印象是:女孩子应该永远是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繁重的生活负担压得香玲母亲喘不过气来,压得她一天到晚紧绷着脸,连女儿的漂亮脸蛋都无暇去欣赏。哪怕香玲帮她端洗脚水,或者倒洗脸水,她都从来没有好声气。有时候在外面遇到不顺心的事,心头的无明之火常对着自家的孩子发泄,对孩子不如意的表现动辄就骂,拉过来就打,嘴里还不停地唠叨着:“没有你们这些穷东西,我不用遭这么多的罪。”有时候甚至把对左邻右舍的不满也借着骂孩子指桑骂槐地发泄出来。
一次,一个不知什么原因得罪她母亲的高个子烟鬼女人从她家门外路过,原先好端端的母亲,对着没犯半点错的香玲便是一顿臭骂,骂的香玲狗头喷血。等到那个麻杆似的烟鬼女人知趣似的远远躲开,她母亲的骂声戛然而止,让香玲感觉到一种无可名状的困惑。
繁重的家务劳动夺走了香玲母亲女性的青春气息,抢走了她美丽的容颜,改变了她窈窕淑女的形象,让她过早地成为家庭主妇,成为典型的管家婆。
香玲回想起与妈妈有关的凄婉故事,常常泪流满面。这些故事伴着香玲长大成人,并清晰地刻印在脑海里,任凭岁月的流逝,都不曾将它们从记忆中带走,反而越来越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