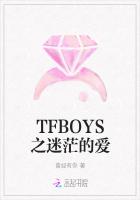天依然很黑,但离县衙不过五六百米的浦宅大门前,数个大白灯笼将十几米的地方照的通亮。
灯笼是白的,大多在出殡的时候才要这种颜色。
尽管是炎热的夏天,在太阳没有升起的时候,寒气透过薄薄的衣衫,有点冰凉的感觉。尤其是新剃的额头,光溜溜的竟然出了露珠,更是让那些心存汉念的江南人士说不出的难受。
呛,呛……锣鼓声渐渐小了起来。
浦宅门前,聚集着三四百人,在凶神恶煞的兵丁的阻隔下,伸长着脖子往前挤着。在全城戒严的时候还敢出来看行刑的,都是娄东当地的才子读书人,有儒子,秀才,退休官吏等。毕竟张鼎和侯峒璞二人名气不小,经过这次起义,更是名声大震,在这些没有胆量起来对抗满清统治的读书人心里,俨然成为了文天祥般的英雄。
不敢出来反抗,至少给英雄送行还是可以的吧。这批读书人如此想着。至于普通老百姓,这种时候还敢出来看热闹的显然极少。
而在这些人中间,十几个神色焦虑的人物咬紧着牙关,互相悄悄的对着眼色。躲藏在张家的张政,就混在其中!他们可不是来眼巴巴的看着张侯二人被砍头的。
与此同时,浦峤站在自家大宅的门口石阶上,眯着眼睛,心中却阴郁无比,人来的太多了,超出了他的预估,甚至让他感到后背发凉。也许是知道历史上汉奸的下场,他看向分列大门两侧、昂首不跪的张侯二人,两人表现出来的气质刺痛了他的眼睛。明明昨天已经严刑拷打,折磨的皮开肉绽,今个儿两人还是硬骨头一般又臭又犟,游街过程中甚至谈笑风生,简直没有半点临死的自觉。
“处斩反贼,天经地义!”浦峤如此说道,显然底气大为不足。读书人里窃窃私语,眼神不善的看着自己,浦峤知道自己的名声彻底到了臭不可闻的地步。他反而恼怒这些人,自己又没有抢你们娄东才子的钱财,反而是去临镇捞一笔,你们凭什么恨我,有本事你们也去抢啊!
愤恨的人群和兵丁不时发生着摩擦,火药味渐渐浓郁,直到几个兵丁亮出白花花的大刀,场面才稍微控制住。但谁都知道,双方的神经都绷紧着,流不流血已经不好说了。
就在这个时候,浦宅大门打开,绑的和木乃伊一样的浦嶂被下人抬了出来,这老东西被朱总煜等人割舌断了浑身骨骼,被浦家花重金请大夫好不容易吊住了性命。浦峤特地把他拉出来,打的主意是给自己分担压力。
果然,浦嶂一露面,人群立刻炸开了锅。
“快看,浦大汉奸成了废人!”
“现世报啊,浦峤,下一个就是你!做汉奸不得好死!”
“哪位英雄好汉干的,张某一定出书立传歌颂他的事迹!”
……
浦峤脸色铁青。而浦嶂却是浑身颤抖,可是每动一下,身子骨钻心的疼痛,下人只以为他是气的,可是认真看就会发现浦嶂的眼睛惊恐万分的盯着人群中的一个角落。张政冷笑着与其对视,眼中杀气毫不掩饰,可惜除了无法开口说话的浦嶂本人,没有人注意到张政的表情。
“反贼,反贼就在人群里!”浦嶂恨不得大喊,可是根本出不了声音,呃呃的沙哑声反而让人感到心烦。
浦峤不愿意场面失控,看看时间差不多了,遂走到张鼎和侯峒璞两人中间,叫刽子手准备,拖着长音,道:“张鼎,侯峒璞,你们两人聚众谋反,刺杀当朝命官,扰乱地方,可知罪?”
“哈哈哈……好你个狗贼,聚众谋反?我为大明天下抗击满清鞑子和其走狗,哪里有罪!刺杀当朝命官?笑话,我杀的是忘祖求荣残害同胞的狗东西,既然是狗,就不是人,杀狗焉来罪过!至于扰乱地方?你等屠戮地方,生灵涂炭,贼喊捉贼,莫过如此!”张鼎愤然疾呼,周围一众读书人听的热血沸腾,跟着大呼:“张鼎,无罪!侯峒璞,无罪!”
浦峤老脸涨的通红,指着张鼎的手剧烈的颤抖,厉声喝道:“大胆刁民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给我跪下!”
啪!
刽子手从后面一脚踹在张鼎和侯峒璞的小腿上,两人吃疼,条件反射的跪倒在地,咬着牙又站了起来,浦峤大怒,又命刽子手下狠手,张侯二人的膝盖被顶碎才跪倒在地,但依然昂首挺胸,气势不减。
“浦老贼你残害义士,人神共愤,早晚会遭报应的!”在张政的冒头喊叫下,人群再次沸腾。一个读书人冲上前去,想要扶起张鼎,被一个兵丁用刀子砍在胸口,顿时倒地吐血。
那个读书人生死不知,一下子点燃了火药桶,场面反而更加混乱。张政等人暗中潜伏在人群中,推波助澜,很快与兵丁扭打在一块。张政这些人都是行动失败后躲藏在附近民宅里硕果仅存下来的义士,冒着生命风险,在牺牲了好几人的代价下才再一次串联了起来。
侯峒璞看着眼前的景象,眼眶湿润了。抬头望着黎明前的黑暗,忽然想到了四个字:“就死也罢!”
这四个字是江阴那边传来的,江阴县衙的书吏在县令命令下把常州府发来的严令剃发的书文写成布告张贴,在写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句时,义愤填膺,把笔扔到地上,不写了,对县令道:“就死也罢!”消息传到全城,引起了接下来的杀县令,满城抗清的壮举。
侯峒璞知道自己必死,但如果能唤起一个地方的反清情绪,那也值了。
他与张鼎相视一看,同时笑了起来。
“侯兄,有你这朋友,张鼎死而无憾!”
“侯某亦有此感,哈哈哈……你我年龄相差一辈,但乡野有句俗话,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生,不妨你我结为异性兄弟,到了黄泉道上也不算孤单。”
“好,张某也有此意!”
……
两人竟然在临死前,开始结拜起来。
“妈的,怪哉,这两个妖人,不能再留了!”浦峤见了鬼似的,离两人远远的,跳回门槛,眼睛瞪圆,命令兵丁强行镇压蓄意闹事的人群,转身对两个刽子手呵斥道:“愣着干嘛,给我动手!我不要这两个人看到明天的太阳!”
“是,大人!”两个刽子手吆喝一声,拎起大刀,高高举过头顶。
“再闹,你们就是他们这个下场!”浦峤嚣张大叫。
大刀在白灯笼的照射下,凛冽的寒气瞬间笼罩住四周。这个月来,不知道多少亡魂死在了这两柄刀下。
行刑的一刻,人群中一个个满脸煞白的读书人又怒又气,所有人反而噤声,无助的看着大义凛然张侯二人。
上百的兵丁严阵以待,将浦宅门前团团围了三层。
如果不出意外,下一秒,大刀落下,张侯二人必定人头落地。
不能再等了!
“兄弟们,上!”千钧一发之际,张政怒吼一声,从袖口里拔出匕首,往兵丁的队形中冲杀。话音刚落,十三个同伙一同发难。
十四个人对上百个全副武装的兵丁。
兵丁们早就严阵以待,长枪列出,大喝一声,往前直刺。
“呵呵,就这么点人也敢劫法场!”浦峤松了口气,不过脚步挪移到了自己哥哥的后头。
两队实力悬殊的人马还没有拼上刀子,张政一方中一个大汉猛的从身上飞出十几个装满黑油的牛皮袋,封口的绳子早就事先解开,牛皮袋飞入兵丁的头顶,黑油呼啦啦的如豆大的雨点般落在他们身上。
“大家散开!”大汉叫道,取出火折子朝兵丁一扔,后者瞬间面如土色,哪还管什么队形,慌不择路的朝四周推攘逃跑,火折子正好落在一个兵丁的背上,轰!顿时火光大耀,点燃了附近一个,两个,三个……一个眨眼的功夫,十几个活人成了火人,哭爹喊娘的在人群里乱转,哀嚎声惨不忍睹。那些沾有黑油的兵丁最是害怕,丢盔弃甲,第一时间跑了。
兵丁们只能挥刀砍向朝自己奔来的着火的同伴,唯恐波及自身。
张政等人趁着混乱的大好时机,冲向张鼎和侯峒璞。两个刽子手互相看了看对方,丢下大刀,扭头就跑。
“弟弟!”张鼎激动不已。侯峒璞厉声喝道:“快跑,这里有埋伏!”
就在这时,浦家大门内猛的涌出五十多个手提大刀的清兵,这些人不同于浦嶂控制的当地兵丁,乃是李成栋的精锐。这些清兵身后,又涌出一队手拿鸟铳的火器兵。
一个照面,五个冲在最前头的义士被砍死。
“这些都是反贼,杀光他们!”浦嶂插着冷汗,暗自庆幸自己的后手。
鸟铳架设好,啪啪啪,一通不待瞄准的射杀,张政等人又死了几个,而那些读书人却倒了霉,好几个人倒在了血泊中。
人群骚乱。绝大多数读书人四下逃命,少数几个热血上涌,捡起兵丁掉落的兵器,加入了张政的行列。但这点人并没有什么大用。
张政左臂擦过一颗弹丸,掉了一块皮肉,脸上一阵煞白。心知今天有死无生,不由提起勇气,和其他人一道慷慨就义。
混乱过后的兵丁与清兵一起将张政等人围了起来。
刀光剑影,血末横飞。
几个呼吸后,张政身边只剩下了两人。
“把他们头割下来挂在城门上,看谁还敢在我浦家门前撒野!”浦嶂见大事已定,一开始的恐惧化为狰狞,现场的血腥气激发了他残酷的本性。他居然没有注意到家门口流了这么多血,风水上可是极其不好的兆头。
啊!又一个倒下。
张政浑身浴血,孤军奋战,被清兵围在中间。
“哥哥,我先走一步!”张政用匕首刺向心口,事到如今只有自杀了。
“不!”张鼎大吼。
就在这时,轰!三眼铳朝天放了一炮。
一骑飞马奔腾而来,身穿蓝色八旗棉甲,居然是个八旗骑兵!
“全部住手!反贼一个都不能死!”八旗清兵声嘶力竭的大吼。
“什么?”浦嶂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这一嗓子下来,清兵生生停下了动作。这些清兵谁敢违抗八旗骑兵的命令。而且对方棉甲的等级,绝对不低。
张政的匕首已经刺破了皮肉,血还没有流出,只见场面一下子诡异了起来。抱着必死决心的他呆呆的望着八旗兵拨开清兵,看了自己一眼后来到浦嶂面前。
“你就是浦峤?”八旗兵问。
浦峤点了点头。
“贝勒爷有令,浦峤作恶多端,斩立决!”说完,马刀一挥,浦峤没来得及问个明白,便人头落地。
所有人都震惊了。一向作威作福的浦峤居然被满人给宰了,而且如此干净利落。变故来的太快,所有人措手不及。
一旁无法动弹的浦嶂胆寒无比,盯着死不瞑目的弟弟的人头,在冰冷的青石地上翻滚,那双死人眼直勾勾的盯着自己,似乎要自己下去陪他,浦嶂一口气咽不下来,忽然口吐白沫,头一歪,吓死了。
那八旗骑兵对清兵命令道:“贝勒爷原话,听朱总煜大人的要求,把张侯等人送往县衙,不得伤到一根汗毛!马上给我动起来!”
“朱总煜!”
“朱宗室!”
张鼎、张政和侯峒璞三人呆滞了片刻后,瞬间狂喜:“他真的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