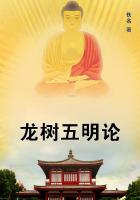全福楼是寰州城内最大的酒楼。顾井匀和顾流芳挑了个二楼靠窗的位子,点了一壶上好的碧螺春。顾流芳有滋有味地品着,顾井匀却有些焦灼不安,不时探头望着街上来来去去的人。
及至一杯茶下肚,顾流芳终于忍无可忍,收起折扇,在顾井匀面前的桌子上轻轻一敲。“我说你能不能自然点?生怕别人看不出你是来和人接头的吗?”
“别忘了你我犯了教规,云宫的教众四处追杀咱们。”
“你没听说过大隐隐于市吗?越是人多热闹的地方越不容易被人发现。再说我也并非云宫教众,最多算是一个外围家属。你若今日与我割袍断义,明日我就找人在各州县衙布告栏前张贴告示,说你我从此恩断义绝、两不相干,保准云宫教众没那个闲心思搭理我。”
“尽是歪理。”
“歪理也是理。”
“且不说这里招人耳目,这样高档的酒楼,菜肴定然价格不菲。你点了这么一大桌子,结账的时候可别哭鼻子。”
“钱的事儿还用你操心。我这个做兄长的几时让你饿过肚子?”顾流芳说话间将一个精致的钱袋甩在桌上。
顾井匀哭笑不得。“你偷了耶律贤的钱袋?”
顾流芳啧啧嘴:“怎么能是偷呢!耶律贤和我是什么关系?没有我设计的暗门,他能从云宫的地牢里逃出来?没有我发现密道,他能从刺史府里探到那么重要的军情?没有我为他设计铁菱角和鬼箭,他能以少胜多守住涿洲?我可是他的救命恩人。正所谓大恩不言谢。”顾流芳点了点桌上的钱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顾井匀知道他满肚子歪理,越与他争辩他越来劲儿。如此纠缠下去势必没完没了。适逢店小二来上菜,她趁机将话题转到菜品上。“这几道菜做得甚为精美。想不到西南五州虽然灾情严重,遍野饿殍,可寰州城里还能吃到这样华贵的菜式。”
顾流芳果然被她拐离了方向,道:“如今这世道哪里不是饿死穷人,撑死富人。”
两人正说着,二楼楼梯拐角处上来一个古铜肤色、宋才潘面的契丹少年。少年一看便是店中常客。熟门熟路找位子落坐,用契丹话对店小二吆喝着:“来十只香酥鸭。一盘在这儿吃,剩下九只打包。”
寰州虽然富庶,但眼下正值荒年,能来酒楼里消费的人不多。酒楼二楼空荡荡的只有三四桌人。虽说能来酒楼用饭之人必然阔绰,可像少年这般张扬,十分引人注意。
顾流芳对顾井匀使了个眼色。“我说的没错吧。灾荒之年再饿也饿不死这些公子王孙。”
酒楼里客人不算多,顾流芳说话的声音不算小。少年显然是听见了。走过来一作揖用熟练的汉话道:“兄台桌上也是琳琅满目,这样说别人不合适吧。”
少年眼中隐隐有怒气,可他说话之间仍然十分有分寸。一看便知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我又没指名道姓,你怎知我说的是你呢?再说了嘴长在我身上,我爱说什么你管得着吗?”顾流芳的性情顾井匀最了解。他那张嘴口没遮拦,不知道得罪过多少人。他人来疯,最怕就是没人和他拌嘴。此时为了与少年杠起来,更是夸张得将纨绔嘴脸做到了极致。
谁知那少年闻言并不上当,微微一笑。“汉书上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兄台远道而来,是客。我不与兄台计较。”
顾流芳正要驳回去,就听顾井匀道:“公子是如何知晓我们是远道而来呢?”
少年笑道:“西南之地久旱,日头烈、风沙大,哪里会有小姐这样冰雪姿花月貌的美人呢!”
正所谓礼多人不怪。本来是巧言令色的恭维话,可少年笑容爽朗、眸色正气,话中没有半分轻薄之意。倒让人觉得这话是他真心实意。
此时店小二将少年点的鸭子送上了桌。除了一只摆放在盘中,剩下的全部用油纸打包好。少年没有回座就餐,而是招呼小二将八宝鸭送到顾流芳这桌。“这是全福楼最有名的菜‘八宝鸭’。每日限量只做十只,而且要事先预订才有的吃。相逢即是有缘,这只八宝鸭就当是我尽地主之宜请二位品尝。
顾井匀收下鸭子。“公子是读书人,讲究待客之道,我们唯有却之不恭。”
少年爽朗一笑,对顾井匀拱手道:“在下今日还有些事情,不知兄台与小姐可会在城中盘桓几日,若能有缘相遇,在下可为二位引荐城中其他美食。”少年说完拎着打包好的鸭子大步流星地走出了酒楼。
少年人还未到楼下,顾流芳已经不客气地动筷子往嘴里塞香喷喷的鸭子。果然外酥里嫩,人间美味。见素来饕餮的顾井匀动也不动,只是出神地望着少年消失的身影,他取笑道:“你莫不是见这少年郎面如冠玉、唇红齿白,便动了什么歪心思吧。”
“早就听闻西南民风耿直,想不到竟有这样爽快之人。”
她话音刚落,就听那少年已经走到楼下。二人坐的位置刚好能将酒楼门口的声音尽数听入耳中。只听少年招呼掌柜道:“老规矩,都记在账上。”
顾流芳啧啧嘴:“看来妹子你看走了眼。这少年郎不过是个纨绔子弟。”
顾井匀看了他一眼,似笑非笑。“就算是,恐怕也不及某人。”
少年刚走不久。便有一玄衣劲装男子风尘仆仆进了酒楼。顾流芳半个身子倚出窗外,对下面吹了声口哨。男子男子抬头看了他一眼,大步流星奔上二楼,不客气地自己落座。
看见男子周身打扮,顾流芳一口鸭肉哽在喉咙里。吐也不是,吞也不是,猛地呛咳起来,好半天才顺过气。他看看顾井匀,又看看坐在面前大口灌茶的玄衣男子道:“你们俩还真是主仆情深。奎宁你大白天的穿着一身黑做什么?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探子么?”
被唤作奎宁的玄衣男子闻言不气也不恼。仍是大口灌茶,仿佛已经渴了三五天滴水未进。直到壶里的茶水见底,他才得空张嘴。“你知道我日夜兼程从代州赶来累死了多少匹马吗?我若是和你一样白衣胜雪、风流倜傥,只怕现在满身脏污早叫人当叫花子撵出去了,哪里还能进来与你们喝茶?”
顾流芳闻言赶紧去瞧奎宁抓过的茶壶把手,果然黑漆漆的五个手指印。顾流芳看奎宁的眼神就像猫儿看老鼠,一脸兴味。他眼珠滴溜溜一转,故意找茬道:“你跟我说话就不能客气点。好歹我也是你家右护法的兄长。难道你们的教规没教要尊重长官吗?”
“教规二十三条确实说要尊重上级,可并没有尊重长官兄长这一条。”奎宁白他一眼。
顾井匀实在看不下去他们两人斗嘴,只能适时打断:“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耶律适派的人已经到了代州。”奎宁顿了顿,“耶律璟派去的人比他先一步。”
顾流芳闻言抚掌大笑。“果然姜还是老的辣,狐狸还是老的贼。”
“我让你查的那个冢呢?”顾井匀又问。
“在云州西北三十里,一个叫做勒祥的石烈(乡)。”
顾井匀淡淡一笑,夹了只鸭腿到奎宁碗里。“你辛苦了,就在寰州歇几日,迟些我还有事情吩咐你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