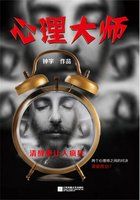舒立凡是什么年代的人,已经很难考证了,关于她我们唯一知晓的就是——她很美。
这可能是很多女孩的梦想。甚至在中国古代,也很难有女人只留下“美”的名声。昭君和貂蝉的美是为了匡扶社稷,冯小怜与杨贵妃的美使得国家一落千丈。是啊,哪个国家的历史学家会有足够的境界和人文情怀在史料中记载这么一条:王二家的女儿很美,大家都喜欢她,后来她死了。可舒立凡做到了这一点。
舒立凡的美名能够流传下来,还多亏了一首民歌。
舒立凡很美。
她知道自己美,也是到了十五六岁的年纪。小时候,舒立凡只是认真地帮妈妈做牧场活儿,和别的小姑娘们一起玩耍,在田野里摘花。可到了15岁,舒立凡发现男孩子总来找她玩。过路的男人们,目光更是离不开她的面庞。有一次,一个又能弹冬不拉,又会写诗的男孩子来找到她。他只是结结巴巴地说了句:“你,你的脸庞比月亮还要白。”然后就害羞地跑走了。
哈萨克的男人总是这样的,他们飞翔在诗歌的天空,却在语言的大地上沉默。
舒立凡开始想:男孩们都是没脑子的傻瓜蛋,可谁想后来,关注自己容貌的男人越来越多。舒立凡才想:或许真是自己太美了。
舒立凡跑到湖水前,望向水中的自己。水中的影子只是显得有些孤独罢了。面容在湖中颤抖着,单薄而脆弱。真是这么一张面孔,使得男人们痴迷神往吗?可为什么?在高山与河流面前,在大地与天空面前,这张泛白的脸,藏着什么样的宝藏,竟让男人们如此追寻。她越想越生气,往湖里扔着小石子。石子落进湖面,打出一层层涟漪。
“扑通”,一声闷响。
这闷响更让她感觉心仿佛被裹在了牛皮中。她感觉到不erkindik(自由、舒畅),不erkin就是无法舒展的感觉。
她觉得这都要怪那些愚蠢的男孩子。她决心不再理会他们了。每次看到男孩,她都会瞪着他们,然后害羞着跑回毡房。可越是这样,男孩子们却越认为她美。有的男人过路时吹着放肆的口哨,有的男人带来自己打的猎物,更多的人只是用双眼不停张望。他们明明已经走过了毡房还要不停回头望着,以至于走得跌跌撞撞,像走在冰面上。
哈萨克人经常会有大型的toy(聚会),如果不太远,舒立凡便和姐妹们一起去玩。而每次去的时候,总会碰见那个愣头青一样的诗歌少年。他在阿肯弹唱会上能言善辩,谈笑风生,可见到舒立凡,他连句整话都说不利落。他只磕磕巴巴地问舒立凡:“姑娘,你还好吗?”这时舒立凡旁边的女伴,会笑得直不起腰来。舒立凡涨红了脸,不回答。她现在长大些了,也明白点道理了。她知道女伴的笑声中,有一部分是真心的,又有一部分带着说不清的恶意。她们笑得那么夸张。唉,自古以来,人类就是如此,总是没有原因地笑。
而且只要有人笑,就会有人忧伤。
舒立凡想某些女伴们可能会对自己很嫉妒。而流言马上印证了她的想法。部落里碎嘴的女人们彼此诉说着舒立凡的恶毒。她喜欢招惹男孩子,到最后又不理睬他们。上次,她的朋友跟她去toy(聚会)了。有一个特别英俊潇洒的男孩子,能写一首好诗,又是阿肯弹唱的好手。他向舒立凡表达爱意,舒立凡不仅没有领受,还用恶毒的言语羞辱了那个男孩子。这样美的女孩却有着如此的毒蛇心肠,真令人胆寒。
谣言在部落里飞舞,可舒立凡所有女伴见到她时,却还是那么真诚。舒立凡不知道谁的真诚是真的。而无法辨别真伪的真诚,也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舒立凡跑到没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她想:真主为什么非要把美貌赐给我啊。这下子,我变成孤独的女孩子了。
哈萨克族一直有个说法,叫作koz tiyedi(夸赞里有毒)。所以当被夸赞时,哈萨克人总会非常地小心谨慎,认为过度的夸赞是坏运气的开端。舒立凡的母亲也这么想,所以她让舒立凡天天在家绣花织毛毯。
后来舒立凡的青春一直就是这么度过的。
生活是有惯性的。到了应该嫁人的年龄了,很多人家的公子前来求亲,但舒立凡总是一口回绝。她喜欢绣花。绣花很自由很安全也很安静。
在孤独的毡房里,她的脸庞变得越来越白。在绣毯子的劳作中,时间过得很慢也很快。
终于有一个春天,她走出家门,看见苹果树开花了。舒立凡走过去仔细瞧了瞧,她心想:真奇怪,这朵花开得怎么跟我绣的一样呢。可怜的舒立凡,她怕是都忘记了,毛毯上的花是照着外面的花绣的。
单纯的舒立凡以为:是人类先绣出来了毯子,然后苹果树才照着毯子上的花纹开的。
当初的女伴们,如今多已嫁人。只有舒立凡,还没找到如意郎君。近来来求婚的人越来越少了。此时,舒立凡突然想结婚了。她觉得原来那个会写诗会弹琴的阿肯少年就不错。可惜不知道他在哪里,很久没有见到他了。有人说那个男孩在一次旅行中,被毒蛇咬中,已经死去了,却也不知道是否真是如此。
舒立凡跑到湖边,她望向水中的自己。水中的影子只是显得有些孤独罢了。面容在湖中颤抖着,如今不再美丽了。短短几年间,容颜就衰老了。她想在湖边放声大哭,却也哭不出来,正如一位我热爱的北欧诗人①所写的那样:痛哭似乎轻而易举,实际上却万分艰难。
难道真是自己,使所有男人痴迷神往过吗?在高山与河流面前,在大地与天空面前,女人的美,竟只能是那样可怜的一瞬吗?她越想越生气,往湖里面扔着小石子。石子落进湖面,打出层层涟漪。
“扑通”,一声闷响。
这声闷响更让她感觉心仿佛被裹在了牛皮中。
舒立凡忽然觉得青春算是白白晃过了。她回到家中,对着自己织出来的毯子发呆。如今没有人再追求她,她只是一个因为织毯子而远近闻名的女人罢了。
毯子傻愣愣地躺在毡房的角落。舒立凡忽然感觉毯子这事物本身就是泛着孤独和冰冷的所在。毯子和自己一样试图证明着什么东西的存在,但什么也证明不了。它们只是毯子而已,却耗费了一个女孩最美的青春。
舒立凡抱着自己的毛毯,终于放声哭了出来。
舒立凡不知道的是,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女孩子的青春能够有什么用处。织毛毯中流逝的青春与被男人注视中流逝的青春,都是同样一种流逝。女孩子的青春是那么美丽,有时我想它正是因短暂而神圣的,也是因为无用才值得人类更长久珍惜和热爱的。
这个故事很长,如果把它缩写,反而会更动人。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姑娘,她脸庞像月亮。后来很多人爱她。后来她没有跟那些男孩子走,她一个人在毯子上绣花。然后一生就过去了。然后她不知道一生怎么过来的。
这个故事是任何时代任何女性的故事。
翻阅着唐诗宋词,里面一个个红颜,只留下了一两个姿势。哈萨克女孩要是孤独了,肯定不是为了写诗,也不是为了春愁登楼起相思。哈萨克女孩要是孤独了,就是真孤独了。茫茫草原没有高楼,已经没有意象显示得出自己是孤独的,故而只是在心里。乍看到她们,竟不像孤独,倒更似是平凡……
在这个世界上,女孩子孤独不是由于孤独。
是因为女孩子的青春,太美。
不知是谁听说了舒立凡的故事,并为她写了一首歌:
苹果花开
冰清玉洁心上人,你的面庞,宛如月光。五湖四海,示好之人,不可胜数。
他们深情望着你,怎忍离去。平地之上,如行冰面,跌跌撞撞,慌慌张张。
苹花灿烂,织之于毯。一针一线,寓以何情?
青春逝去,你我不觉。白驹过隙,追悔不及。
姑娘走上那山岗,每天都在,静静眺望。她的耳环,闪动银光,叮当作响。
思念缠绕在心头,日见憔悴,怎能忍受,伴着琴声,我要将你,唱入歌中。
苹花灿烂,织之于毯。一针一线,寓以何情?
青春逝去,你我不觉。白驹过隙,追悔不及。
如此,舒立凡的青春,才得以流传下来……
屋顶上,我身畔躺着的是刚刚认识的女孩子,她也叫舒立凡。刚认识,我们之间就有了些火花。
我是说,我爱上她了,一见钟情。
我曾写道一想到当她卸了妆后,会是清雅的。所以我便兴奋,便感觉爱上了她。
这是假话。
我爱舒立凡,只因为她是年轻的。躺在她身畔,我能闻到青春的味道。那是种甜甜的荷尔蒙的味道。青春真好。
舒立凡让我给她讲故事,我便把这首哈萨克民歌改编成了故事,讲给了她。她听完后,轻轻叹了口气,仿佛什么东西压到了她的心。
她转过去背对着我。这样,我就又闻到了她头发上的香。
闻着那香,我很想爱她。但品味着歌曲中所携着的诗句,忽然觉得爱似乎真的很难。
只好再次套用北欧诗人的那个名句:
爱看起来无比简单,但其实万分艰难。
夜空中悬挂着一轮还算明亮的月亮。
我轻轻抚摸着舒立凡的长发,她没有任何动作。
这时,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忽然浮现到我的脑海中:是因为我爱她,她才是我的舒立凡的,还是因为她是我的舒立凡,我才爱她呢?
当我陷入到这个愚蠢至极的问题时,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身畔的舒立凡,面颊上挂着一两颗闪亮的泪水。
人类的泪水是世上最渺小的星星。
注释:①亨里克·诺德布兰德(Henrik Nordbrandt,1945—),原诗如下:
在旷野上
那些最初的浮云
在蓝蓝的天空上
投下沉重的影子
在高高的枯草上
痛苦似乎轻而易举
实际上却万分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