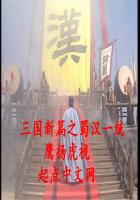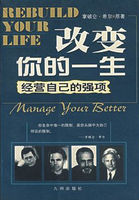没一会儿就开了工,我铲了棉花钵放进芭斗里,爷爷封完了土问我:“累不累?”
奶奶在另一列用打钵器钻土,笑说:“吃嘞胖,有劲!”
我拎起芭斗,说:“不累。”
在一天傍晚,我们终于种完了棉花。晚上我在家取柴禾烧锅的时候,奶奶去院子里掐菜,邻居走过和她聊了一会儿天。
邻居看了我一眼说:“你们家宜宜真能干!”
奶奶将掐好的菜用手握着,笑说:“可不是,家里六亩的棉花,她一个人拎完又摆完!”
奶奶的声音异常响亮,这句话陡然有夸奖我的意思,但我从来不把它当作称赞。我想纵然爸妈不寄钱,我做得这些加上自家五亩地打的粮食,足够付我和老三的学费和生活费了。
小麦再减产也能收个一千块钱吧?
何况我和老三的学费加在一起才一百多块钱!
第二天是星期一,学校开完周会我搬着板凳回教室,两条腿的膝盖总觉得直不起来,胳膊又痛又酸又麻。写作业时握着拳越来越厚的茧子碰到手指,有的蹭出来了皮,我就把它揪下来,还有一层就用小刀的尖头把它们挑破再揪。
我在那会儿特别喜欢学校的老师,觉得除了爸妈之外,他们是真真要好的人,他们都很关心我的成绩,有时候在全班同学面前夸我的字写得真好。
上学变成一件幸福的事。
也许是因为别人对我有期许,没落过一次奖状,我总捧着奖回家。但奶奶说:“女孩儿家上学好有啥用,早晚都是别人家的人!”她有一次这样重复说被爷爷听到,爷爷就对我说:“宜宜,别听你奶的,她懂个啥!把学上好才是正事!”
——
学校不久后放了麦忙假,早在冬天的时候,家里就开始补袋子,因为收麦要用。夏天越来越热,我和老三变得没有鞋穿,老三的鞋子坏了,总没有新的。我把妈在前年买的大红色拖鞋找出来,上面黑漆漆的,我每天拖着上学下学下田。
奶奶在一天早上赶集,老三和她讲了要买鞋子。她在那天早上带回了一双酒色的拖鞋给老三。制鞋的塑料特别硬,很磨脚,老三穿着总把它脱下来。
麦忙假的第一天,我和奶奶就在地里等机子。以前总是镰刀割麦子,现在家里没人,就等下乡的机器过来收割。
收割机也不是时时都有的,从早上等到晚上,从晚上等到半夜,终于轮到我家,机器一过,我和奶奶就在麦茬子上面铺了层油纸,等机子倒麦。
很快六亩的麦子收完了。棉花苗碾死碾残碾歪的不少,奶奶很心疼。老三骑着修好的三轮车和爷爷一起过来时,我和奶奶已经开始装袋了。
夜色很浓,满天的繁星点点,干燥的天气在夜里也散去炎热的温度变得有些寒意。
装了一多半,奶奶说:“拉回家吧!”
于是就开始往拉车上面装麦袋,我和奶奶抬麦袋子,遇到小一点的就自己搬上去,扶着车把的爷爷总是叫起来:“宜宜,快放下来和你奶抬,累吐血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