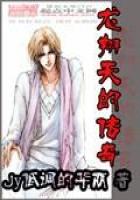在此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昏睡是怎样的一件事。也一直认为那晚“宜宜,挂着针可别睡觉啊”是在梦中得到的一句话。
这场病并没有使我痛苦,相反地,从内心来讲,我甚至是享受这段时光的。
每次家里有人生小病时,爸总会在一旁乐呵呵地说:“啊,不能活了啊!”
我妈就会笑他,遂后对我们说:“听你爸胡说去罢。”
我从不担心自己的病情怎么样了,会不会好,到了喉咙嘶哑到爸妈都要反复听我讲话的时候,我也没有这样担心过,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死。
很多天,爸没有心情开玩笑,仿佛家里都笼罩着一层病痛的雾气。而这在这层雾气当中,所有人都痛苦,唯独我快乐的不能言语了。
那个时候爸妈眼里不再只有老三。在那个当下,我是备受重视的一个人。甚至姐姐和老三因为我生病的原故,对我越发的好。
大夫在早上又了一次,拿听诊器诊听了几下,在堂屋和爸妈又说了一番。
大夫走后,不到晌午,爸又把车子开了出来。妈也铺陈好了棉被,抱着我上了车。
婶娘从街里走过来,两手抱着孩子,对着我们道:“是给宜宜看疹子啊,我家浩俊也出疹子了,想乘乘你家的车。”
我将脸彻底露出来,妈又给我盖住,对婶娘说:“快上来吧。”
婶娘把孩子抱上来,妈接过,又喊姐姐搬一个板凳过来。婶娘把板凳放进车厢里,也上了车。
看病的地方还是开中药的那家,爸停了车,背着我下来,妈把又用大衣把我的头蒙住。婶娘一人抱着孩子,捂得很掩实。扎了一回针,药店的先生又抓了几副药。我是对那个老头一点好感都没有的,药很难喝这件事也包括在印象之内,再加上这么一大包,却还没有西药一点点有用,只当他是个庸医。
回到家,妈又煎了药。黄色瓷碗里黑糊糊的中药,这次无论妈说什么,我就是不想喝,开始耍了脾气。
妈说等下去买大白兔糖,买大白兔糖我也不喝。我磨蹭了半天,妈把柜子里放的一罐蜂蜜拆了,往药碗里放了半勺,搅匀了对我说:“这回是甜的。”
我勉强喝了。药香层层的扑在脸上,却实没有上几回难喝。中药吃了很久,依旧没有太大效果。爸妈只得另寻医院,这次找的是家西医,拿了药后几天,热度慢慢的退下来。
在还没有完全利落的时候,老三也得了这种病。老三没有吃过中药,不知道吃中药的痛苦。所幸家里有两个病人,看病也都一块去。姐姐成了完全被忽略的那个。
老三的麻疹和我的差不多是同时好的。快复原的那几天,妈准许我们去院子里玩。我和老三拿了弹珠,在院子里耍。
已入冬,天越来越寒了,我回到学校时同学差不多都到齐了,整个教室满满的读书声,没几天后,老师也复了课。
不知道是不是秋风的问题,以红眼病和麻疹为例的两种传染病,几乎成了“见面传”。为此,校长请了人来学校消毒,我们在上课之外的时间里,被老师安排把花坛里的草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