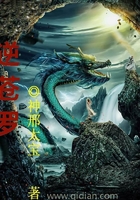我一直以为爸和妈吵架都是奶奶从中搅扰,遂也从不和奶奶亲近。没多久,天气大旱,庄稼渴得奄奄一息。全家人都在商量如何抗旱。周五我们从学校直接去了田里,走了一路,因为口渴,便喝了一碗井里的凉水。
夜幕还没有完全褪下去,我躺在车厢里头痛的喊妈过来。妈走过摸了摸我的额头,她说我发烧了。
奶奶则很生气地说:“现在正是忙时候,搁在这个时候闹,再闹就扔井里去。”
我听完就哭了。妈带我回了家,去到乡里的诊所里量了体温已经到了四十,打完针又开了药。到了晚上又腹泄起来,已是半夜,爸从田里回来,一身衣裳到处都是泥水。
我的烧还没有退,一直在发热。爸和妈一起又带着我去了趟诊所,那个大夫已经睡下。只得拍门把人家喊醒,又打完一针回家。我一直都以为自己不像老三那样多病,但也没有想过自己一病就到了足不能出户的地步。
已是秋,天渐渐凉了。风一吹到处都是杨叶在翻飞。红眼病闹得很厉害,基本全校都得了这种病,连老师也不能例外。每天最痛苦的时候就是早上要睁眼时,每次睁眼都要费很大力气,我觉得撕扯的眼皮都要裂掉了。
试着睁开好几次才能成功把眼睛睁开。
红眼病过后,一场麻疹来袭,一个邻村的女同学告了病假。随后全班的人都像是约好了生病一样,纷纷告假。老师的课停了,休息时间我一个人在教室门前的花坛里玩,上了课就按老师的安排念书,教室里空荡荡的坐着几个人。
那天夜里睡觉时,身上特别痒就去抓,妈以为是被虫子咬了,就去园里摘了薄荷,碾碎了涂在身上。
这样的疹子一连两天都没有退,第三天高烧到连课都上不了。下午妈又带我去看,大夫说是出麻疹他这里看不了。
妈又把我的头蒙起来,说不能吹风。回到家,喊了爸。妈把车厢里铺上被子,又把我蒙起来。再一停车,就到了一个我自今为止都不知道的地方。只还记得当时那家的房子像地下室一样,门前的楼梯不是自下往上,而自上往下走,一推门一股浓重的中药味儿。
看疹带了许多剂中药,天越来越黑,等到我回家时,姐姐与老三已经睡下,妈让我躺在床上,又吩咐睡意十足的姐姐和老三不能用我的杯子毛巾,开始去厨房煎药。
一个黄色的瓷碗里,里面黑糊糊的中药水,还没有喝闻到那股味儿竟下去口。妈说:“把药喝了,病就好了。”
我忍着喝了。
那场病好得很慢,什么都没有胃口,什么也都不想吃。爸经常会和我说:“想吃什么都去买。”
一天夜里,我告诉爸:“想吃葡萄干。”
在乡村还没有商店,只有一些小卖部售着一些孩子的零食。爸到那里买了二十小袋葡萄干。我吃了半袋就不想再吃,剩下未拆封的给了姐姐和老三。
到了半夜,只感觉右手像泡着冰水一样凉。我睁开眼,听见妈说:“醒了醒了。”
再往上看,灯线上挂着一瓶吊水,大夫检查完又嘱咐了番。我看了看手背上的针,右手始终麻麻木木的冰凉,脑袋昏昏沉沉的又睡去。
拔针的时候我醒了,弄完这些,母亲才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