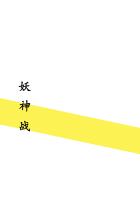”天地君亲师,乃世之典范!我蔡伯喈贵为一师之长,自仲道入我门下,除了教他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对他的言行疏于管教了,才导致今夜的惨祸,实在是未尽一师之责,愧对其父,更辱没‘师’之一字!“
蔡邕走进大火熊飞的院子里,拱手向死去的福伯尸体深深一躬,然后神情悲痛,歉意的道。
刚才,他从山岭上缓慢走下来,看到一群贼人落荒而逃,知道老君观里面危机已经解除了,心思大定。
等到他赶到老君观的时候,正好碰到徐晃神情灰暗,眉宇间透着一丝愁色,驱赶着马车从老君观里出来,心中惊讶,然后走上去询问,才知道老君观里发生了何事。
在听到大家陷入危机之中,蔡邕心中一惊。
可没想到他这心里荡起的涟漪还没有平静,就又听到卫仲道心胆俱裂,头脑发热,失去了冷静,情急之下,跳了出来,出声惊喊,吸引了贼人的注意力,落入生死危难关头,心里为他捏了一把汗。
可是这最后的结果令他意想不到,福伯竟然不顾生死跑了出来,救了卫仲道一命!
他这心里对年迈的福伯陡然升起一丝敬意!
就在蔡邕感叹福伯视死如归,可歌可泣的时候,徐晃又语出惊人说刘恕要打死卫仲道,为死去的家翁老仆报仇雪恨。
蔡邕就静不下来了,迈步走向正在燃烧熊熊大火的老君观里。
”小友,此错在我……若要领罪,这最后一脚也是我蔡邕受之,方可息小友心中怒火!“
蔡邕看着躺在地上,口鼻流血,蜷缩着身子,昏死过去凄惨的卫仲道,摇了摇头,这苍老的面庞上也露出一抹苦涩。
”先生,你这是折杀我刘恕了!“
刘恕赶紧将腿放了下来,从蔡邕明亮的眸子里看到一抹抹真诚,羞愧,苦涩,多种情感掺杂的眼光,这俊秀的脸庞上露出惊慌的神色,眸子深处一丝愧色一闪而逝,但心里却跟明镜似的。
他知道,若想今后洛阳里少走弯路,能够顺利的认祖归宗,光耀门楣,今晚老君观里的这出戏,他必须得唱。
不但要唱,还要唱得更好,让人无间隙可挑,这样福伯才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
”若我这一脚下去,恐怕这天下读书人都会可饮我刘恕的鲜血,啖肉而食……先生出面求情,我这最后一脚不管怎么说都不能踢下去了,可……“
说到这里,刘恕望了一眼躺在地上福伯冰冷的尸体,鼻子一酸,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哀声大哭了起来。
”求先生看在福伯的面上,为我正名,为我正名啊!“
”这……“
蔡邕被刘恕这一出弄晕了,好端端的怎么哀声大哭了起来,让他正名,这是唱得哪一出呢?
”伯庸小友,你先起来,这里火势太大了,稍有不慎,你我等人就会葬身火海啊,咱们先出去,一切容后再谈!“
蔡邕上前将刘恕扶了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指了指放在地上的福伯,然后走上台阶,看了看墙脚的卫仲道,伸出手探了探鼻息,见还有呼吸,只是受伤过重,昏死过去了,就走向了大雄宝殿里,探望自家的女儿蔡琰了。
没一会儿的功夫就领着蔡琰,怀抱竹卷走了出来,看了眼卫仲道,就向刘恕寻求帮助,说道:”贤侄,还望你施手将仲道抬出去,莫让他落在这无情的大火之中了。“
”小兰,那卫仲道交给你了,我去将福伯抱出去!“
刘恕看了眼卫仲道,就对着蔡邕点了点头,然后和夏侯兰说道。
吩咐妥当,刘恕等人很快就往老君观外面走去。
就在刘恕抱着福伯走出老君观那破落的大门的时候,那左面燃烧的围墙轰隆一声幡然倒塌,落入火海之中。
随着那面墙的倒塌,老君观越发的孤立寂寥,眨眼间就让大火吞噬了,演绎着风水轮流,老君望气,生死一轮回。
今夜,注定是无眠的!
刘恕在大火肆虐,通明的火光照耀下,将福伯的尸体安葬在这小小的马蹄岭上。
人一死,入土为安!
尘归尘,土归土,以往的一切将烟消云散!
福伯的墓碑,是他砍下粗壮的树木做的,而碑文则是由蔡邕刻之,以鸣谢他救人之恩!
逝者如斯夫!
刘恕相信好人终究有好报,福伯在那个世界里一定会过得更快乐,开心!
将这些事情办理好之后,刘恕、蔡邕等人就钻进马车里,安心的等待天明。
而徐晃就安安心心的当起了斥候,站起了岗,以防不测。
马车里,蔡邕睡意全无,一双历经沧桑的眸子安静的盯着刘恕,缓缓将心里的疑问说了出来:”伯庸,刚刚老君观里为何跪在地上,喊我为你正名?“
“不知先生知廮陶王么?”
刘恕跪坐在马车里,匍匐着身子问道。
“你是说熹平元年已故渤海王刘悝?”
蔡邕身子一震,脸露奇色,惊问道。
刘恕点了点头,蔡邕那震惊的神色没有逃过他那毒辣的眼睛,哽咽着说:“家父乃渤海王刘悝,熹平年间,遭人诬陷,惨遭入狱,不经酷刑,苍然而亡!”
“什么?”
蔡邕一颤,心里掀起了轩然大波,顾不得从容,抓着刘恕的手,追问道。
“小友,你所言甚真?”
要知道,当年渤海王刘悝一案,可是牵连甚广,死了很多朝中要员,当时他就觉得事有蹊翘,只是那时候他只是已故司徒桥玄征召为掾属,官小职低,虽然私下里向司徒进言过此事,只是那时候圣上年幼,受奸邪蒙蔽双目,难辨忠奸,最后这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只是没想到,当年那场隐秘竟然在这小小的马车里又起了风波。
所以,这就容不得他不惊讶!
刘恕知道光说这些很难令蔡邕相信,遂将随身携带的族谱,家书,王侯印绶拿了出来,然后在这舒适豪华的马车里说起了当年的隐秘。
“先生,当年我娘亲在大火之中将我送到福伯手中,福伯杀出重围,潜逃到真定边远小村庄,隐姓埋名,整整十七年!
若非福伯,焉有今日之刘恕呢?
可卫仲道这厮一嗓子,使我福伯魂归西去,我又如何不怒?”
蔡邕耳边响荡着刘恕那沙哑富有磁性的声音,手上接过刘恕递过来的包裹,翻看着里面的物事。
车厢里,刘恕的声音渐渐消散了,唯独剩下蔡邕翻转着蜡黄色的信笺,仔细的读了起来。
等到将所有的物事看完之后,蔡邕表情不平静了,心里激动了起来,看向刘恕的脸色都不一样了。
“小友,按照信笺所言,你父身前虽有罪,但乃小过,以得先皇赦免,是无罪之身了。那居心不轨,阴谋叛乱之言纯属子虚乌有,欲加之罪!”
蔡邕平息了激动的心情,将东西叠好整齐,放进了包裹里,还给了刘恕,只是那瞳孔里闪烁着浓浓的复杂之色。
刘恕跪坐在软榻子上,察言观色,抱拳深深一礼,说:“先生,有话就请直言,恕洗耳恭听!”
“小友,你父遭人陷害,获罪狱中,迫不得已才自尽在牢房之中,若你知晓仇人,当如何处之?”
蔡邕凝视着刘恕,希望从他那有神的眼眸看出点什么。
从刘恕拿出印绶,书信,族谱的时候,他就相信刘恕所说的一切了。
只是作为人臣,他不得不为君上考虑。
若是刘恕头脑发热,发誓要找刘宏报仇雪恨,那他蔡邕就是整个大汉的罪人。
”先生,我知你所忧!“刘恕看着蔡邕表情严肃,欲言又止的样子,就知道他心目中担忧什么,遂接下话,说道。
“家仇血恨,若说让我放下,不闻不问,那我刘恕做不到!陛下初登皇位,对朝中之事,知之甚少,又受阉宦佞臣蒙蔽双眼,盛怒之下才颁出这错误的旨意!
我不敢找陛下寻仇解恨,但冤有头,债有主,当年那些栽赃陷害我父之人,我作为子嗣必将他们碎尸万段,以慰我刘府三百二十多口人在天之灵,沉冤昭雪!”
蔡邕见刘恕恩怨分明,并没有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和心智,心里泛起淡淡的喜悦之情,点头感叹道:“伯庸,你有如此见解,我心甚慰,我心甚慰啊!”
刘恕感受着蔡邕那紧绷的心终于松了下去,暗松了口气。
只要消除了老头子的心里负担,那么他才能全心全意为你指点明津。
心中一大块石头去掉,蔡邕的心情无限得轻松愉悦,说:“伯庸,你想找到那首恶可能难如登天,毕竟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十七年了!”
“我自知在洛阳人生地不熟,言辞甚轻,力量薄弱,想要将当年的隐情翻出来,肯定会困难重重!
所以,我恳请先生看在我福伯援救卫仲道,身死已故的情面上,助我一臂之力,让我刘府三百二十多口人得见天日,使我能够归宗认祖,光耀门楣!
就算不能报仇雪恨,我也要为大汉出一份力,为我刘氏流尽最后一滴血,以告我父在天之灵!”
刘恕躬身行礼,再拜蔡邕,希望他能伸出援手。
蔡邕听完刘恕说完,顿时沉默了。
刘恕举着拳头,匐匍在地,恭敬的拜倒在蔡邕的身前。
他相信蔡邕一定会答应他的请求,施以援手,让他归宗认祖,荣归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