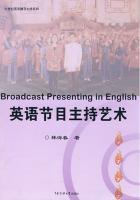”阿爹,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府衙后堂里,田单走了进来,看着自家老爹拽着笔杆子,坐在那低头不语,顿时就不高兴了,嚷嚷着嗓子,叫喊道。
田牧坐在蒲席之上,拿着紫色狼毫笔,低头苦思,脸上表情不断变化,听到那嚷着嗓子叫喊的田单,抬起头脸上露出一丝丝苦涩。
”单儿,非是我见死不救啊,而是无能为力!“
”田公为何有此一说?“
高干从前厅走了进来,正好听到田牧说这句话,神色一动,暗思难道这里面真有什么难言之隐?
”你们知道我为何一听那常山贼名号,就言禀明府君大人,立马拒绝吗?“
高干,田单对视一眼,摇了摇头,表示不理解。
”他们是常山贼,是黑山军,是以前的黄巾余孽!“
田牧说到这里,脸色的苦涩更甚。
”若是这伙贼人是一般山贼强盗,我一纸军令,自有县尉领兵剿灭,可他们不是啊……那黑山军大帅张燕名声有多响亮,你们不知,但我知晓啊!
朝廷年年派大军剿贼,只要这伙贼人一旦听到风吹草动,立刻遁入山林,隐匿起来。
到了最后,贼不剿成,反而年年劳民伤财,哀声一片!“
”这……“
两人面面相觑,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一丝震惊,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常山贼来头如此之大。
自黄巾之乱暴动以来,大汉皇朝仿佛在叛乱中度日如年。
蚁贼叛乱虽镇压了下来,但也让大汉伤了筋骨,动了元气,仿佛人到高龄,步入暮年。
汉帝刘宏为表天下太平,改元中平,预兆天下安康,百姓兴隆。
也许是老天和汉帝刘宏开了个玩笑,这年号刚改,就又传来了凉州羌人北宫伯玉伙同同州李文侯、韩遂、边章等人起兵叛乱,这天下太平没有,****倒是不休。
汉帝刘宏得知雷霆大怒,即刻下诏,命皇甫嵩,张温出兵讨贼,镇压叛乱。
直到中平四年,凉州叛乱才镇压结束,可又有谁想到,大汉皇朝仿佛多灾多难。
渔阳郡人前中山相张纯、前太山太守张举两兄弟联合塞外乌桓在幽州发动叛乱,斩杀护乌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气焰嚣张,声势浩大。
就在去年,又有凉州人王国起兵叛乱。
这大汉皇朝,每年一叛乱,岁岁年年,就如同那一脚步入黄土的老人,只剩一口气吊着,日薄山西。
现在,朝堂之上,又暗流涌动,杀机四伏。
外戚,宦官,党人三方角力,追逐着那权利的诱惑。
”阿爹,就算剿贼不成,但不能一直这样放任不管吧!
若是这样,那穷苦百姓岂不心生不满,对朝廷怨声载道?“
田单见里面弯弯这么多,一时听得头都大了。
”管,怎么不管!“
田牧瞥了眼自家儿子,没想到今日他竟然主动询问起这些朝廷时事,又接着道:”自光和年间,蚁贼蜂涌起事,天下震惊,朝廷对此非常重视!
前不久,那黑山大帅张燕不知怎得竟派人上表,请求招安,归顺朝廷!
这不,昨日府君大人差遣心腹派人送信来,言及朝廷使臣将至,前往黑山营寨招安,受封黑山群贼,以绝后患!“
田牧说到这里顿了下,悠悠道:”那常山贼这些年所为,若非今日那赵家村的刘恕告诉我,恐怕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呢。
可这又能怎么办?
黑山招安,天使亲临,此时正值多事之秋啊,我又怎么能亲口答应那刘恕?“
田牧说完,心中渐渐升起一丝丝无力,仿佛全身气力都被抽光了一样。
要说一开始没有忿怒,那是假的。
可在忿怒又能怎么样,在国家安宁和赵家村覆灭之间,田牧选择了前者。
毕竟能成为一县父母官,考虑的问题非一人一村了,而是整个真定县了。
做官做成他这样的,也是头此一家,别无分号。
高干听田牧讲完,眸子里精光闪闪,眼神灼热。
他终于知道为什么自家舅父,前不久托心腹之人送来密信,让他前往真定了。
原来事情在这!
府衙后堂,听田牧道出了原委,高干胸中仅有的那点怨气便烟消云散了。
而作为子嗣的田单更是知晓自家老爹身为一县之长,自有苦衷,也就不再吵闹,纠缠了。
就在田牧一个人独坐后堂苦思冥想之际,远在真定四十里之外的一处山谷之间,潜伏着一批人。
这群人蒙着黑巾,只露双眼,手持器械,压着身子,趴在半山坡,居高临下,眼神凶戾,紧紧的盯着下方那条地势陡峭,环境幽静的小道。
这小道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鸡鸣道,日间夜晚时常会有山雉鸣叫,奔跑,而得名,更重要的是这鸡鸣道横在常山郡与真定县之间,是前往真定的必经之路。
鸡鸣道两面环山,地势陡峭,两侧山坡上树木繁盛,杂草丛生,倒算是个埋伏潜杀的好地方。
“渠帅,他们会来吗?”
一道略带疑虑的声音在山坡上响了起来。
随着这道声音响起,山坡众人纷纷将目光望向趴在前头的一位黑衣男子。
看情形,这黑衣男子是他们的头头。
“昨日得到消息,那群人日间时分就出了城,若我所料不差,以他们的速度,最迟在正午之前就会经过这里,而且从这到真定,是必经之路,除非他们不想来,否则必从此过去赶往镇定!”
黑衣男子趴在地上,眼睛依旧盯着前方,并没有回过头来,沉着声音说道。
既然他们头头都这么说了,那么作为手下之人只有静心等待下去了。
等待的时间是漫长,也是枯燥的,大概过了一刻钟的时间,只听那趴在地上的黑衣头头睁开眼睛,喊了声。
“来了!”
众黑衣人一听,精神一抖,立马提起神来,紧紧了手中的器械。
就在那黑衣人头头话音落下,只听见小道的尽头传来了一阵阵马蹄声。
哒哒哒!
这马蹄声简洁有力,整齐干练,一听就知道是一群训练有素的精兵。
顺着马蹄声望去,只见小道之上,来了一群身披盔甲,骑乘高头大马,手持着长枪,头戴兜鍪的精兵队伍。
这队伍看上去人数大约有五百左右,步履整齐,动作娴熟,持枪挺马,雄赳赳,气昂昂,奔腾之间,一缕缕红色流缨镶嵌在兜鍪之上随风飘荡,自有一股震慑人心的气势。
在这队伍的中间,是一辆墨色雕梁,金黄澄亮,华顶遮盖的车舆。
《管子·禁藏》有言:“故圣人之制事也,能节宫室,适车舆以实藏,则国必富,位必尊。”
舆又叫车厢,后转意为轿子,在车厢前端,是一根稍微弯曲的长木(也有用直木的),叫做车辕,一头与车轴相连,令一头与轭(一种与车辕垂直,弯曲置于马脊颈上的木结构桥形装置)垂直相交。轭的两端以绳环扣在马颈上,马前行时,拉力依次通过轭,辕,传递至车轴,最后带动车轮向前滚动。
车轮的中心是一个金属的带孔圆环,称为殻,用以贯轴。车轴两端露出殻外,末端套有青铜的轴头,成为軎。
轴上有孔,用以纳辖,以防车轮脱落。辖多以青铜或铁制成,扁长形,俗称销子。轮的边框,成为辋,辋和殻之间以辐相连。
在古代早期的时候,车厢多不封闭,仅以木栏或木板围合,有时车上还有盖,即由车上一根竖杆支撑的伞状覆盖物,用于遮阳、避雨及显示身份,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帝王将相出行,会有华盖遮顶之说了。
而且在古人乘车时的座位方式也有讲究。
古时乘车尚左,一车三人,尊者居左,陪乘者居右,御者居中,但兵车则不同,如为将帅所乘之车,则主帅居中,便于指挥,御者居左,护卫居右,一般战车,则御者居中,左右甲士一人持弓,一人持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
所以,一车驾御多匹马,对于驾御者的技巧就要非常高超了,不然很难使所有马朝一个方向前行。正因为这样,孔子所定六艺之中就有“御”这一技艺。
更甚者,古人还从驾御马车中总结出一些的治国道理,如西汉的韩婴在其《韩诗外传》中,
就有说到:“御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则马和而欢,道得则民安而集。”
好了,言归正传,从这车厢的外观以及护卫的甲士来看,就知道车内坐着一位地位尊崇的大人物。
这大人物也并非他人,正是奉大汉天子刘宏之命,前往黑山招安,受封张燕官职的朝廷天使前北中郎将,现任尚书之职,海内知名大儒卢植卢子干。
山坡上,望着下方精兵队伍渐渐走来,步入眼底,黑衣人头头缓缓举起右手,突然一挥,下令道:“放箭!”
咻咻咻!
随着这一声令下,那早已蓄势待发,迟迟不动的黑衣人如临大赦,纷纷两臂用力,弓满如月如那漫天蝗虫,席卷田地,风卷残云般飞向山坡小道上的精兵队伍。
一轮箭雨落下,仿佛巨石落水,激起千层浪花,下方那精兵队伍顿时出现了混乱。
“啊!”
“我的脚!我的脚!”
“敌袭,敌袭!”
“保护大人,保护大人!”
眼望着小道上的队伍死伤慎重,出现混乱,黑衣人头头又岂会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时机。
“杀!”
一声虎吼,瞬间爬了起来,抓起手中的环首刀,就率先冲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