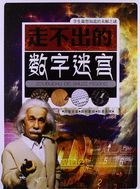太阳将要搁岩的时候,波儿几口扒完红苕饭,小跑着去找六千娃。
六千娃的家在海子边的大竹林中。波儿隔了竹林喊:“六千娃六千娃!”无人回应,他就钻进竹林去。六千娃家的房屋很破陋,原来横三间木板房现在只剩西头一间,且那一间的木板壁也没有了,是划破楠竹夹成代替的。木板壁到哪里去了呢?乡政府计生队拆那两间房的时候,顺便把西头这间房的木板拆去了。
波儿站在房坎地下喊六千娃,还是无人应声,便看穿枋上。穿枋上的锄头不见了,人一定是上坡了,便往坡上跑。
六千娃果然在帮他妈妈挖红苕。
六千娃很瘦,有点像《红岩》里的小萝卜头,细细屑屑的样子,细耳朵、小鼻子、尖下巴,只有额头很宽、很高。上码头村有人打趣说:“六千娃,长大了你额头可以卖给黔江城作广场。”有人就议论:“只怕全身卖了也不够还账,”“刚从娘肚子生下来就遭罚几大千,这辈子难搞。”“那娃儿八字大,把他酒鬼老汉克惨了。”
能听懂话的六千娃默默应对着村人的议论,在心里说:我要发奋,总有一天,我一根头发也要值几千。
六千娃家确实欠了很多账。母亲连生三个都是女孩,生三胎时,乡政府处罚了三千块,他家便卖牛、卖猪、卖粮食,终于花两年时间缓过劲来,可是父亲说:“女娃都是别户的,传宗接代总得要一个。”后来,就有了六千娃。
酒鬼本姓牛,儿子何以叫六千娃呢?
酒鬼连续超生,实在影响乡政府政绩,乡政府太生气了:哼,生两个不行要生三个,生三个了不知足还要生四个!视国策为儿戏?那只有重处:房子拆了,罚六千!六千块钱把他家整晕头了,一家六口要吃要穿,当时有两个还要交书学费,钱是一文没有。父亲就被扣在乡政府,寒冬腊月,罚他立正,头上顶盆冷水,动一动水就泼出来,泼出来就成冰凌,不几天酒鬼就恹得无有生气。做母亲的心下着慌了,在月子里四处拼借到一千一百块钱。乡政府叫酒鬼具书盖指印放回找钱。酒鬼花年半时间,走亲串友东挪西借终于交了罚款,后来牙一咬就给他的宝贝儿子起了个名“六千娃”。
“六千娃,你给老子要争气!”父亲常常教导儿子要争气,他自己却不大争气,老是醉酒,在一个下雪天,他喝了酒去捞鱼虾,掉进小南海再没有爬起来。
日子更难了,雪上加霜这个词实在是为这类人家造的。
时至六千娃12岁的今日,三个姐姐相继外出,不知漂浮在哪些乡场或城市。母亲硬是咬紧下巴送六千娃在海口小学读了四年半,今年上半年硬是撑不下去了,六千娃才被迫辍学。他母亲对别人说:“书学费难,但最难是船费。”
怎么最难是船费呢?上码头村村子小学生不多且参差不齐,就没设村小,到海口上学坐木船,有两个多小时水路,要么是自家船,要么是一次花三块钱坐班船到海口小学。六千娃家无钱造船,他上学多是坐班船,每天来回六块,长此以往,他家拿得起?
六千娃比较懂事,六千娃不和母亲使性子。
六千娃有心思,他的心思给波儿讲过。波儿与六千娃是同班,他家里也穷,穷的原因很简单,他父亲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有一年上山砍柴时摔成了植物人,家里只有他妈妈一个劳力。他妈妈正怀孕,可是什么事情都落在她的身上,有天中午在湖里起网的时候动了胎气,她正下船,孩子突然降生,一下子就掉到了水里。她赶忙捞起来,后来这孩子就起名波儿。波儿才上两年学就辍学了。可波儿很佩服在班上当学习委员的六千娃,六千娃说的事他都喜欢做,于是他就记住了六千娃的心思。
“六千娃,你还,还在挖,挖红苕啊?”波儿一着急就有些口吃。
“么子事,波儿。”六千娃蹲着捡红苕很淡然的样子。
“么子事!你叫人盯到问那送,送信的,我问到了,今,今晚上放映。”
“放映么子?”六千娃两手拿着红苕站起来。
“除开放映故事片外,要加映花白鲢养,养殖。”
六千娃把红苕丢在背兜里,看着波儿磨盘似的大南瓜脑袋,说:“你扯谎,波儿。”
“扯谎是狗儿,在海口放,邮递员亲口说的。”
“好,我们去。”六千娃给他妈打个招呼就和波儿小跑起来。“没有班船了,只有借只小船。”波儿说。
“好!”
于是一条小船便划行在小南海的湖面上。
小南海的船形式多样,有红红绿绿的旅游机动船,有着篷载货的齐屁股船,有行若飞针只乘一人的三板船,还有一种人工船名字很美:双飞燕。双飞燕比齐屁股船小,比三板船大,一般有篷,船头尖而微翘,其身躯好似一位修长而不瘦弱的美妙女子,此船可载背篓、茶叶之类小小货物,也可乘坐五六人。船尾左右挂两支桨,一人双手分别握了,劈浪斩波,俯仰有致,远远望去,碧水绿波上,宛然那翩翩飞翔美丽燕子,三两闲情游客多爱坐这种船游小南海。
六千娃和波儿划的就是双飞燕。
可惜那船飞不起来,因为年久失修,船底船帮板材没有重新刷过桐油,渍水严重,不沥水,船速慢。
夕阳刚沉到鸡公山后面,留了一些条条块块红红黄黄云彩在山顶亮着。湖面像一面镜子,牛背岛红红的枫叶,老鹳坪虬劲的古松,朝阳寺岛的挺拔楠竹、浓绿垂柳,都在微风中轻摇细笑,润生出一派朦胧的醉意。远远望去,湖中景物汇同那西边山顶的斑驳云彩,在那浩大平展的镜面上铺开一幅色彩斑斓的中国画。
六千娃们的船开始在这幅画中穿行了。这幅画是如此地绚烂壮丽,六千娃们小小的行程同这幅画相比较,也许是那么不起眼,那么微不足道。因了经历的瘦小,六千娃对人世间事还是懵懵懂懂的,什么希望,什么现实,他不可能在理念上衔接起来,但是他把向往托付给一个梦,并企望着梦的实现。
那个梦是他躺在一只船上时做的……
后坝河边那个大瀑布,轰隆隆冲下来,跌进那口宽潭,旋转着又汇成一股激流,绕几个弯冲入后坝河进入小南海。一米多长的花鲢们在激流奔泻的浪花中翻滚交尾产子……
花鲢、白鲢究竟是个啥子模样呢?这些图像在他眼里只是团团幻影。他是偶然在一次乘船时听人说花鲢白鲢一条能长到几十斤,但小南海这样的平静湖水中不能繁殖,必须在激流中冲撞着才能产子,并且还要打催产素。
可是真正的养殖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他多么希望获得这方面的知识。
希望终于要实现了呀!听了这个消息时他几乎高兴得跳起来。但他没跳起来,苦难过早地光顾他,使他少年老成,他只是毫不犹豫地同波儿上了船。
船由波儿先划着,湖边上的孩子人人会几桡子。波儿比六千娃长得蛮实,加之湖面尚未起风,波儿把桡子划得吱嘎吱嘎很有节奏。
“天气安逸。”波儿说,“不像往天要黑了就起风。”
“快划,波儿,”六千娃看着晚霞渐渐变黑,“我担心的就是没有风,天黑前后是不会没有风的,天又闷沉沉的,这时候还没起风等会儿怕有问题。”
“有问题也不怕,电影八点半,两个半小时后我们已经坐在小学操场看电影了”。话是那么说,波儿手上还是加了劲,“哽—唰”,“哽—唰”。
“六千娃,我觉得要重新上学也不难。”
“为啥不难,没钱就是难。”
“我听说张北有个张素珍,很爱读书,家庭困难失学了又读不起书。北京那个总书记爷爷去看了她一下。全国好多人就给她寄钱,她就重新上了学。我们两个给总书记爷爷写一封信,让他在电视里给大家一讲,全国许多人不就会寄钱吗?”
“想嘛,想多了就会成个偏颈。”六千娃白了波儿一眼,“我们村就有二十多个失学的,全国有多少?他们都写信,总书记爷爷都在电视里都讲?”
“那就没得法了。”
“啷个没得法,你脑壳那么大,多想想呀。”
“多想想,噫,你是不是想养花白鲢赚钱读书哦?”
“你说呢?”
波儿大脑壳摇两摇说:“我脑壳转不过弯,说是也不是,说不是也像是。”
“你是在唱广播里那首歌哟,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六千娃讥笑波儿说:“我说一个字,是!我就是要养鱼赚钱读书,赚很多钱,在上码头修个学校,让失学的伙伴个个都读上书。”
“你是在款天话哟,六千娃。”波儿惊奇不已,眼睛鼓得像颗皮蛋珠,“即使你懂得了技术,买鱼种、买饲料的钱从哪里来?小南海这么宽,你怎么管得过来?”
“波儿波儿呢,说你笨还是不笨,你问了我这么多问题,我都是想过的,我来回答你。”六千娃搬块舱板横搁在左右船舷上坐了,看着波儿说,“乡政府几个月前就宣布小南海承包,至今无人承包,原因是这深山老林里有知识有票儿的太少,我如果懂了技术,我就叫我妈拿粮食到场上换点钱,我到黔江城,甚至到重庆市区找有钱的老板来联合承包。问题不都能解决吗?我想两年下来就会有收益,人就可以边读书边办事,几年后不就可以修一幢小学教室,请几位老师吗?”
“嗨,真还有你的。那你莫把我忘了。”
“怎么会呢!前两年我还可请你当管理呢。”
“那就好。要是你找的老板不愿进山呢?”
“我听广播里讲了。大城市有很多有钱老板想在乡下找种养项目。我要先印点文字,找乡政府盖了章拿出去。如果一个不愿,我找二个,二个不愿找三个,一直找到为止!”六千娃眼里透出一种直直的光,神情很坚定。他站起来,说:“我来划。”
夜幕渐渐笼罩下来,远山已成剪影。六千娃将船划得平稳且无“唰”的那一下水声。他划船很注重技巧,常常观察老水手们的动作,桡片斜切入水,发力时正切在水下,起挠时又正在力尾,斜斜的,故无水声。若细细观察,他每划一桡片后的水面便现出四个小旋涡,许多小伙伴看着常常惊讶,因为他们连一个旋涡也划不出来,他们划的桡片水面常常一片散乱。可六千娃并不满足,心里总觉得有欠缺,他希望像优秀的大水手那样一桡片划出八个旋涡。他做事总想做得最好,但在这种事情上他还做不到,因为一桡片划出八个旋涡不单单是技巧,而且必须附上成年人的力量。
船在继续行进中,六千娃突然感觉到一片水浪将船推了一下。他立即停止划船观察着水面,看上去水面仍是那样平静没有变化。未必是我感觉错误?正在这时,他已分明地感觉到船舷又被无声无形地推了一次,船身因此向左面荡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