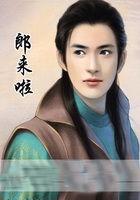比翼(三)
2005-10-6
“他们不懂我的音乐。”瞿风坐在客厅里叹气,“没有意思。”眼皮下面一团阴影,整个脸皮好像要掉下来。他刚刚从一个座谈会上回来,被同行批得体无完肤。
闪闪刚刚听完瞿风给她放的另一部自创音乐剧,汗毛在背上立着还没平伏。纳博科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总是让读者“倾听你的脊背”的反应,不知道包不包括这种反应。
一个人听瞿风的音乐,闪闪八成会吓成神经病。
闪闪虽然音乐素养有限,却并不是完全的音盲。布兰妮和玛丽亚·凯莉让她感觉像吃大量的冷猪油,最喜欢的音乐家叫Erik Satie。他的曲子像下雨天里儿童随手弹出的曲子,又干净,又忧郁。每次听他的钢琴曲,闪闪就想,要是这个作曲家把自己的曲子弹给她听,她就算是8个孩子的妈妈,也一定会抛家弃子跟他跑掉——幸亏他80年前就死了。
闪闪还知道,瞿风是个才子,然而不是她那杯茶。
但是面前这个男人,明显地需要安慰和鼓励,女人天生总有点惜才。当下似乎只有一条路可走,假冒知音。
“他们嫉妒……”闪闪说。
瞿风笑了:“当然是嫉妒,他教出来的学生连纽约卖艺的都不如。”
“你在乎他怎么看吗?”闪闪问。同行相轻的对话开始让她觉得不舒服。
“我在乎你怎么看……”瞿风说,在沙发上向她靠过来,凑近了看她。闪闪担心他发现自己鼻翼上正在酝酿的那个大疱。
闪闪去看过一个挺出名的实验话剧,那个话剧里的演员不断地在座位上走来走去,假装这是个机舱。英俊的男演员好几次坐在她旁边,和她搭讪。闪闪天生好色,难免受宠若惊。但是话剧实在太糟了,人物刻画只到达表皮层的深度,罗里八嗦的独白像地摊文学的自慰,装模作样的对话就是减缩了的自慰。话剧嘲讽现代城市白领,但是剧本那么苍白轻薄,浪费了这些漂亮动人、记忆力超群的演员。
“你觉得这个剧本怎么样?”闪闪带点同情问那个“濮存昕”。
“你觉得怎么样?”咦,反应很快。
闪闪一下管不住嘴:“不怎么样。”
英俊的脸忽然拉长了8厘米,好像上面画的妆忽然褪色。半响:“不怎么样就对了。”冲上台。接下来再回到她身边的时候,再也没和她说话。
闪闪忍着生理上的恶心看完了那部劣质话剧,临了还被那个漂亮女演员泼了一脸矿泉水——他们假装飞机失事在颠簸,不是故意的。
这是闪闪学到的非常重要的一课:艺术家的心是脆弱的。
但是现在,木偶皮诺曹又要接受考验了。瞿风很近地看着她,她下意识摸了摸鼻子:“要是我说你的音乐我不太容易接受呢?”
出乎意料,瞿风笑了:“没关系,我只是想知道你怎么看我。”
闪闪笑了,她无限真诚地、温柔地、像对自己的幼儿园知己一样地对他说:“你很可爱……”
说完,她忽然知道,今晚不会去西藏了。
桃花
2005-4-17
一个事业顺利而且还知道照料自己的女人,到了一定时候,总会发现自己命犯桃花。
自从孟苏和同居多年的男友分手,她忽然发现自己生活的大门骤然敞开。30岁是个奇怪的年龄,你忽然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无人管辖,自制力大增,而身体状况又很好。这个时候,桃花挡都挡不住地往你身上飞,尤其是暖春时节。
就在孟苏和华裔英国商人温进行了一段秘密的“空中关系”之后,距离的折磨使她难免开始灰心。但是毕竟爱情还是真实的,因此虽然奔波不定,人却总带着满足欢喜的气息,反应也比常人灵敏。
这时候,她被邀请去参加一个朋友的晚会,在那里认识了斑马。斑马是个野外运动爱好者兼自由作家,非常滑稽,把孟苏逗得一晚上大乐。聊着聊着,斑马忽然直勾勾地看着孟苏说:“我爱上你了。”
孟苏还是大乐,只当是另一个笑话。
但是随后几天,斑马的进攻开始源源不绝,恭维、哀求、自怜……“我正在家里忍受慢性死亡。”一副中国“垮掉一代”先锋派的做派。
虽然孟苏对中国当代文学毫无兴趣,但是对斑马还是开始有点心动。毕竟这是个近在咫尺的、活生生的健康男人,老能让她高兴。虽然斑马好色的名声在外,但是他毕竟也结过婚,有过几任长期女友。看着他在春日艳阳天下露出的健壮胳膊,孟苏心想,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她就试了一下。打个电话,斑马就来接她了。
那是孟苏经历的最单调的尝试。
非常奇怪,平时很会说话的斑马,忽然无话可说了。一路上沉默着,到了家里,各自宽衣,然后微笑着开始运动。
斑马的身材非常好,大约可以拍个写真集,在中小城市促进他写得不怎么样的文集销路。但是奇怪的是,从一开始接触,孟苏立即坠入非常冷静的半睡眠状态。她试图做一些努力,但是到肚脐眼就干脆放弃了。斑马倒是断断续续地努力着,虽然一直无法进入正题。孟苏只觉得滑稽,一切都很滑稽,连接吻的方式和他发出的奇怪的短促的声音,仿佛是嗤之以鼻。她想大笑,但是一笑起来,情况更糟,仅有的一点冲动都没有了。好在斑马尚且持之以恒,最后在她沉默的忍受中完成作业。
她把这个过程告诉苏丝黄。苏丝黄道:“看来不能和笑星做爱,太分散精力。”
但是斑马不这么认为,在回去的路上,他对孟苏的沉默无法理解:“你感觉好吗?”
“床很不错。”孟苏问,“在哪儿买的?”
斑马对孟苏说:“我知道你感觉不错,我已经对你有所了解了……”
孟苏再次大笑,不过笑完之后,她感到自己对斑马的兴趣已经烟消云散。
回头再想想自己和温的关系,觉得简直完美,不知先前为何庸人自扰。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你必须跨过半个地球来寻找的东西,否则就不会有东印度公司和微软了。这个发现的确让孟苏高兴了好一阵子。
替代品(一)
2005-11-5
没有谁能在一生之中摆脱替代品——伟人像和天安门招贴画、假钻石镀金戒指、假牙、心脏起搏器、塑料花、人造革皮鞋、《欲望都市》中夏洛特的粉红色兔子……替代品部分有时象征着我们心向往之而不可企及的事物(比如天安门),有时帮助我们实现我们自身不能实现的任务(比如心脏的正常跳动),有时部分满足我们不可满足的欲望(比如真的钻石白金戒指和一个完美爱人)。
“比如说我爸爸,他这一辈子只跟替代品打交道。”薇薇对苏丝黄说。
薇薇的爸爸从来不欣赏她妈妈,他总是在马路上目标明确地左顾右盼;他不仅摆塑料花和伟人像,还买三合板仿实木家具和人造革沙发;他带假发和满口假牙;他用全化纤的“古罗马式”帷帘遮挡家里所有舍不得扔掉的破烂,包括漆黄铜色的石膏马和碧玉色的塑料象;他唱卡拉OK时要求家里所有人都像真正的歌迷一样闭嘴倾听;他热衷于一切“像真的”东西,但是他从来不买“真的”东西,因为价格总是太高,拥有一个相似的东西就可以了。
你怎么理解一个热衷于积累替代品的人?他拒绝接受关于自己的已有的事物和现实(比如带假发);浪漫主义(比如向往遥远的城市);或者实用主义(还有什么比用假金戒指满足爱美的欲望更实用?)。但是不管怎样,属于“酷”一代的薇薇总是对此非常难堪。她下定决心过“真实的”生活:纯棉窗帘、真金耳环、鲜花和……一个真正的、了不起的爱人。
所以她到了30岁,依然没有一个男朋友(她只需要能和她结婚的“真”男朋友,这很成问题,因为她给对方考虑的时间总是太短)。她很着急。
但是有时候,有些需要是非常迫切的,非用替代品不可。
有时,她和一大堆朋友去那些有中式古床和红罗帐的酒吧里,玩一些暧昧的游戏,输了的人相互接吻;有时,她在网上聊天,偷偷开一些过界的玩笑。
“所以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其实这些都是替代品啊,所以我就想,不如找一个更实在的替代品。”
有一天,她和同事克敬聊天,夜一深,两个人自然感慨起感情挫折:他们都找不到“那一个”。而且两人心里都明白,对方不是那一个。不过等克敬邀请她去他家坐一坐的时候,她还是答应了。
对不得不凑合的完美主义者来说,有时这样的场合非常尴尬:你希望自己完全被冲昏头脑,不必正视自己的行为,但是因为对方实在不是那一个,被冲昏头脑的机会很小,除非你喝得有一点点醉,看不到对方略秃的头顶和不够理想的胸围。
还好,他们的“真相”在对方眼里都不算太离谱,所以替代性行为能够相对顺利地得以进行,积累已久的需求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过了某个转折点之后,结果几乎是非常满意的。
然后,克敬很自然地从后面拥着她睡着了。
薇薇心里升起一点希望的暖意,一面却觉得很悲哀:这是她这辈子用过的最重要的替代品,她觉得自己堕落了,而且堕落得一点也不酷。
这时,她毫不自觉地又模仿了父亲的另一个行为模式:她决定拒绝承认现实,明天一早就偷偷溜走,从此假装没这回事。决定之后,她安心睡去。
替代品(二)
2005-11-5
第二天,薇薇偷偷溜走了,再遇到克敬的时候,他也假装没这回事。互相给对方当一回替代品,还是很公平的。
虽然薇薇的虚荣心颇受打击,不过理智上接受了,克敬当然有同感。他们还是经常在一起谈论自己心仪的对象,好像超级密友,当然说话的时候不知不觉增加了点亲密感:“为什么她看不上你,你很好啊!”就像慷慨地谈论一件价格昂贵,但是自己有钱也绝对不会买的家具。
过了一个月,柏林爱乐乐团在北京演出。去晚了,票价2000一张,薇薇和克敬说起来,很惋惜,克敬不吭气。开演当天,克敬打电话给薇薇:“我有一张多余的票,你来看吗?”
薇薇有点受宠若惊,简直顾不得客气:“好啊!”
回过身,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镜子里的人很值钱。
为了答谢,她先请克敬吃晚饭。餐桌上,克敬叹气道:“这张票本来是送给我喜欢的那个女孩的,不过她把票送回来了。”
薇薇的筷子停在菜碟上方半寸的地方。
她受够了,小时候穿姐姐淘汰下来的衣服,现在给别人填空座位。
克敬看出来有问题,连忙道歉:“对不起,我以为你肯定会喜欢……你要是不喜欢可以不去,真对不起。”
出于礼貌,她还是去听了,但是腰后面像顶了个锥子。
终于明白但丁对地狱的定义:“地狱就是与没有亲密感的人近距离相处。”
苏丝黄说:“哦,我有个朋友最近离了婚。她老公什么都好,特别安静,包办一切家务,但是完全不是一路人。所以她经常失眠,后来离了婚,失眠症就好了。”如果你是个完美主义者,长期使用替代品会让生活无法忍受。
但是替代品还是有很多好处,比如可以随时置之不理,不致于心碎而死。薇薇很快就忘了这回事。
两周之后,薇薇忽然发现自己胸部有个小突起,大恐慌,疯打了一晚上电子游戏,不敢跟家里人说。
第二天中午,克敬刚好来电话,请她来家里的大阳台上喝茶。她捡起包跑到克敬家里,浑身发抖。克敬看她异样:“等等,我先给你削几个柿子。”
他削了几个小柿子,柿子太软,被捏成一堆不成形的稀泥。他勇敢地端上来,请薇薇一起吃。
薇薇给他解释情况,说着说着,忽然看着他,嘴动不了——柿子心是涩的,克敬忘了削掉。克敬也瞪着她,好像嘴巴里被恶作剧施了胶水。两人闭着嘴大笑起来。
放松下来,薇薇忽然觉得很疲倦:“我想睡觉。”
克敬躺在她身后,抱着她,她安心地睡着了。醒来时天近黄昏,看不见人。她轻轻地吻克敬的手。他们又替代了一回,感觉很好,这一回,他们一直睁着眼睛看对方。
后来的检查没什么事,克敬给她庆贺了一次。经过这次经历,他们终于正式巩固了在对方生活中替代品的地位。经常打电话,但是也经常把对方忘掉。
苏丝黄笑道:“简直可以现编一首广告歌:‘寻找正确的替代品,正确使用替代品,你让我活得更容易。’”
维尼(一)
2006-7-28
莉莉安要升迁到香港了,她和朋友去一个花园酒吧庆祝。
事实上没什么好庆祝的,更像是哀悼:因为莉莉安很喜欢北京,但是她工作太狠,公司给她一路升职,到后来,只好让她升到香港总部去——好像跳远跳过了头,冲到沙坑外面去了。要回到沙坑里,还得重新跳……
谁知道,朋友在酒吧里消失了。莉莉安等她,一面沮丧地喝酒,还没喝两口,就听到有人问:“你喝的是什么?”
转过身来,看到一个高大的胖男孩,唇红齿白,身形像毛绒玩具店里最大的那种teddy bear。
顺便说一句,据说很多美国女孩的大毛绒熊都是她们最早的性伴侣。
“你多大了?”她仰头审视他,带点居高临下的口气。
“25,”美国男孩比尔犹豫了一下,“再过一个月就26了!”
莉莉安笑,心里一小块地方一动。好像在幼儿园里看到低年级仰慕自己的男生,有点得意,又有点可怜他。年轻的、胖而不自信的男人总不敢和她搭讪。这个居然不怕她,很新奇。
中途比尔上洗手间,刚才和比尔打招呼的一个熟人也走过来,和莉莉安说话。
比尔回来看到,毫不客气地把他庞大的身体挤到他的熟人和莉莉安之间,继续喋喋不休,那个人好像被他挤到后面的树丛里去了,变成了负鼠。
最后,她决定不再等那个神秘消失的朋友,起身要回家,比尔说:“我再请你去别的地方喝一杯好吗?”
她怜悯地看着他,微笑不言。这个钟点,北京哪里还有酒吧营业呢……连个谎都不会说……
“我还舍不得让你走!”比尔略带羞涩地直视她,身体左右晃。
莉莉安忽然感动了,她的北京同事也对她说过这句话。而且,酒精开始起作用了。
“带我上你那里去。”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