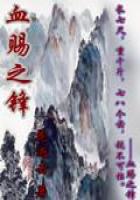电影《摩纳哥王妃》里,褪去光环的格蕾丝·凯利受不住宫廷繁文缛节的束缚,渴望跟希区柯克再次回到好莱坞演电影。就在这时,法国和摩纳哥外交冲突爆发,国家需要她放下个人的事业心,做一个“深情的母亲,忠诚的妻子,富有同情心的领袖”。换句话说,格蕾丝,那个被人指着鼻子骂的“东区来的下贱小婊子”,要在危难之际陪伴那个不成器的王子,共渡难关。
后半段最感人,也最让人诟病。皇室内部的夺权斗争和法国的武力威胁,这两个最大的戏剧冲突都是编剧一手杜撰,那么格蕾丝的坚忍和智慧也就成了泡沫。人们需要励志偶像,导演却选错了偶像胚子。
即便如此,抛开人物传记的写实要求,我还是被这个高度提纯的童话故事感动了一把。移情心理作祟吧,这部电影的基调让我想到少女时代的小伙伴阁阁。十一假期的时候跟阁阁偶遇,心里特澎湃,想写写她的故事。看完这部电影,决定动笔。
阁阁名字富贵,人却命苦,五岁没了亲妈,亲爹是酒鬼,对她不上心,任她自生自灭,用她自己的话说:“不知道怎么就在街边儿跟流浪猫狗一起混大了。”
初三那年她转学到我们班,据说是因为违纪被前一所学校开除,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进到我们学校──更有意思的是,花大力气帮她办手续的不是亲爹,而是“干爹”。那时的学生初通人事,“干爹”的意义虽然不及今天这般意味浓重,但嗅觉灵敏的狗儿们总能从这个名词里提前捕捉一些不同寻常的气息。
像所有转到新学校的“新生”一样,阁阁成了班里的新焦点、新玩具,关于她的八卦新闻一浪高过一浪,有人说她其实比我们大一届但成绩不好只能留级,还有人说她勾三搭四跟坏学生谈恋爱,甚至有人说她男朋友是黑社会的并且她怀过孕打过胎……一个漂亮而不安分的女孩似乎脑门儿上写着原罪,她的所有喜怒哀乐都会被人贴上各种标签作为品评咂摸的谈资。
阁阁从来不解释,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们都穿着傻里傻气的肥大的蓝色运动校服,她穿日本偶像剧里的白衬衣黑裙子。班主任批评她,她就换上了一套粉色的休闲服。学校整顿校风校纪,男生一律剃寸头,女生不许染发烫发不许披头散发,阁阁仍旧染了大胆的栗色。班主任批评她,她把栗色的头发又染回黑色,却烫出了好看的波浪。她很早就学会了用香水,视为“招蜂引蝶”的最佳利器。老师、家长都不让孩子跟“坏学生”交朋友,我竟有一丝庆幸,美丽的阁阁就坐在我身边,她偶尔心血来潮想学习的时候,就会把脸凑过来问我某道数学题的解法。
我和阁阁渐渐熟络,知道她慢热,乍一看清高孤傲,郁郁寡欢,熟悉之后就变成一个笑点很低会哈哈大笑的傻子。那是因为威哥宠她。
我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威哥是一次放学后,一大群学生涌出校门,却瞧见校门口霸道地停着一辆白色奔驰。那会儿不像现在名车遍地跑,有辆“大奔”在街上呼啸而过是不得了的大事。我们推着自行车流着口水想知道是谁这么有面子有车来接,却看到阁阁拎着书包拖着步子不慌不忙地踱到车前,对着车窗里的人喊:“不是说了不让你到学校来吗?闲得没事儿干啊?”不过说完还是愉快地笑了,在众多学生或羡慕或嫉妒或鄙夷的眼神中上了“白马王子”的车。
当然,骑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也可能是马匪。威哥的身份比阁阁还要扑朔迷离,有人说他开小煤窑,有人说他炒股票,有人说他在南方炒房地产,反正毋庸置疑的是,他有钱,有背景,有手段,在我们那片儿有一席之地,属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的威哥把阁阁宠成了不会吃惊的小孩,给了她太多华美昂贵的东西使她不会轻易为外物所动,但对身边的人和事又保持着原始简单的明朗态度。阁阁对我说:“我六年级的时候几个男孩子在路边儿欺负我,大威把我救了,从那以后我就一直跟着他。我孤星入命,已经记不得有爸妈疼是啥滋味儿了。大威对我很好,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她说这句话时同样是一天放学后,威哥没来接她,她和我一样推着单车沿着街边儿慢慢地走。秋风凉了,树叶子哗啦啦掉了一地,脚踩上去嘁嘁喳喳地响,让人心烦意乱。我希望有人对她好,但是看到威哥那种做派,想着关于威哥的种种传闻,又免不了替她悬着心。
后来我读高中,阁阁考了中专。我们学校搞封闭式管理,要求学生必须住校,我的消遣就变成写信。给阁阁写,说读高中很无聊很累很闷。她说:“活该,谁让你那么爱学习的。”还给我寄各种外出旅行的照片,身边有时候是威哥,有时候是别的我不认识的帅哥。
我继续写,长篇大论又无病呻吟地说:“我觉得自己老了没有初中那会儿的激情了。”她说:“我比你老得还快我都有皱纹了。”
我说我喜欢班上一个男生但是他对我完全无感。她说:“下次寄照片给我让我认认脸,以后找机会去你们学校替你削他!”
没多久她就用了手机,写信说:“以后别写信了,太土了,想我就给我打电话。”我攥着手里可怜巴巴的传呼机,恨这小丫头太嚣张太得意忘形,想跟她绝交。
而我们这些乱七八糟的信,很不幸地被我爸妈发现了。爸妈开始对我上纲上线,认为我升入高中之后成绩不好完全是因为交了坏朋友的缘故。我妈从信里记下阁阁的手机号码,直接给她打电话说让她离我远点儿,别耽误我学习。等我再有机会给阁阁打电话的时候,她那个号码已经不用了。
我给阁阁写了很多信,向她说对不起,也替我妈向她说对不起,她一直没给我回信。后来有一天她突然来学校找我,我们在学校的食堂吃了顿三块钱的盒饭,她说:“真难吃,吃这玩意儿怎么能考上大学呢?!你爸妈把你锁在这儿真够狠心的。”
午休时间操场上没人,我俩坐在双杠上聊天儿,阁阁说:“你妈说得没错,咱们不是一路人。你好好读书吧,少跟我这种人打交道。”我听得难受,又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她无所谓地说:“其实我们已经算是很好的朋友啦。以前除了大威和他身边的小弟,我没什么朋友。没想到转个学,还认识了你。每次收到你的信,他们就笑,说我有个作家朋友。”
我笨嘴拙舌地说:“你也好好念书吧,把中专读完,找个工作。总这么玩儿也不是个办法。”
“现在不玩儿什么时候玩儿呢?”她晃着两条瘦长的腿,使劲儿仰了仰脖子看着天说,“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嘛,辛苦奔命是一辈子,稀里糊涂也是一辈子,想那么多干嘛,走一步算一步。别人觉得我轻贱,我觉得自己是公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