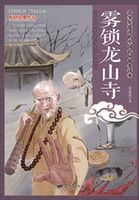进入这个家,我才知道杜圆圆为什么想我搬来同住,她确实寂寞。方方上小学了,住在箫市最昂贵的寄宿学校,一月才回家一次。何开来虽然呆在家中,但他以著书为由,成功逃离了家庭,他只是在吃饭时出现一会儿,平时基本上是见不着人的。她若想说话,也只有跟小保姆去说,而她又不愿跟小保姆多说话,觉着说多了有失主人的身份。杜圆圆在家中的乐趣主要是拿着一个算盘算账,算她今天又赚了多少钱。
后来,我还知道他们这对夫妻不只分床睡觉,并且是不做爱的。他们总共只做过两次爱,一次是在刚认识那天,一次是在新婚之夜。这种事,杜圆圆说多少,我听多少,我也不便多问。对此,杜圆圆也认了,她找何开来,好像找的不是一个男人,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她要嫁给知识分子。她对何开来写书有种发自内心的敬畏感,何开来坐在书房内,她轻易是不敢进去的,因此,何开来在家里的地位比我想像的要强许多。
其实,何开来在书房内根本不在写作,他究竟都干了些什么?我不甚清楚,大概不是跟小狗玩就是跟文如其在网上打牌,或者就是什么也没干。我这样说,估计并没有冤枉他。那天,我上书房想用一下电脑,何开来不在,电脑是开着的,我打完字,看见文件夹里的《中国人史纲》,顺手就打开看了看,里面只有一行字:
中国人的历史是从虚构开始的。盘古说:我开;女娲说:我补;共工说:我撞;神农说:我尝;精卫说:我填;夸父说:我追;后羿说:我射;嫦娥说:没射着!
我正在暗笑,何开来写书,呵,写了那么久,就这么一行字。这时,何开来进来了,我听见他在背后气急败坏说,你在干吗?
我回头发觉他异常生气,气得连眼珠也跑走了,眼睛里全是眼白,我说,哥,你这样子好难看,你这么生气干吗?
何开来说,你干吗看我的东西?
我说,哦,你就因为这个生气?我看看你的书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情书。
何开来说,哼。
我说,呵,你的《中国人史纲》写得很好,可惜就是太短了些。
何开来说,少给我贫嘴,我问你,是不是杜圆圆派你来查我电脑的。
我说,杜圆圆派我?她干吗要派我查你电脑,你电脑里有秘密?
何开来说,好了,好了,你快出去,懒得跟你说。
但何开来还是把我当作杜圆圆的特务,大概是防我告密,晚上杜圆圆一回来,他就表情悲壮地宣布他不想写书了。那段对话,想起来我还想笑。
杜圆圆说,为什么不想写了?
何开来说,这种书,我发现已经有人写得很好,不用再写了。
杜圆圆说,是不是有人抢在你前面,把你要写的东西都写了?
何开来说,是。
杜圆圆失望说,谁这么缺德,那你不是白忙了。
何开来说,是。
杜圆圆安慰说,不写也好。你写书,整天一个人呆在书房里也没意思,你不写书,以后就可以多陪陪我们了。
既然何开来不想当历史学家了,那就得多尽点做丈夫的义务。这个晚上,何开来的表现相当好,一直温情脉脉,他们大概又做了一次爱。
这回做爱,似乎对她后来的生活影响非常大,就像注射了一剂兴奋剂,杜圆圆身体内部的某些东西被调动起来了。此后几日,她一有空就跟我唠叨她的身体,她说,她本来可是个美女,脸蛋,身材都是很好的。怕我不信,她又拿出十年前的照片让我看,十年前照片上的杜圆圆,长得确实不难看。这让我感到可怕,一个人在时间中怎么就变得这么面目全非呢。杜圆圆说,她的身体是在上一轮婚姻中毁坏的,丈夫有了外遇,她很痛苦,但又没有办法,后来她发现吃东西可以缓解痛苦,她就不停地吃东西,凡是可以吃的东西,她都吃了一遍。几个月下来,再到镜子前一照,吓得自己都不敢认了。现在,她有了何开来,她要对何开来好,可她胖成这样,实在有点对不起他,她减过一次肥,因为太忙,没能坚持住,她决定再次减肥。
杜圆圆减肥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她是运动、节食、药物、器械一齐上,简直就是对自己身体发动的一场战争。她一天只喝水和吃少量的水果、蔬菜,某某牌减肥胶囊早、晚各服一次,据说可以烧掉体内多余的脂肪。白天照常上班,在三家蛋糕房间跑来跑去,既是工作,又可减肥。晚上七点,去附近的瘦身俱乐部接受专家减肥,让工作人员把她绑在器械上折磨一小时,其实,那些器械跟以前的刑具也没什么差别。八点以后,她叫上我一起散步一小时,九点半左右回家,在滴了香薰油的浴缸内泡半小时,这个秘方是一位老中医传授给她的,大约可算最有情调的一种瘦身法了,但不知道效果怎样。
杜圆圆动员何开来也一起减肥,杜圆圆说,你也太胖了,你跟我一起减肥吧。
何开来不屑说,减肥是你们女人的事,我们男人胖就胖点,无所谓。
杜圆圆说,减肥真挺好的,我开始减肥以来,精神就特别好。
何开来说,那是你。
杜圆圆说,你别那么懒,你看看你自己,你再不减肥,就超过我啦。
何开来被逼着,果然看了看自己,但他看自己的眼神很有意思,好像他看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一具与他无关的别人的身体。何开来说,随他去吧,反正我没兴趣减肥。
杜圆圆说,哼,你这死样,等我减成一个苗条少女,我就不要你了。
何开来看看她,不得不笑了,说,你真有理想。
杜圆圆减肥,确实还是颇有成效的。她特意买了一杆电子秤,早上起床称一次,晚上睡前称两次,大概再没有比看见秤盘上的数目字更令她兴奋的事情了,哇!又瘦了几两几两啦。杜圆圆蹲在秤上,摇着硕大的屁股,也不管何开来怎么不愿意,她一定跑进书房,将他拖下来,专门再称一次给他看,邀功说,你看,我又瘦了几两几两啦。何开来当然不看,只是随口乱应,哦,又瘦了几两几两。杜圆圆说,有没有比昨天更漂亮些。何开来说,更漂亮些。杜圆圆瞥一眼何开来,好像不太相信他这么廉价的应和,又走到镜子前,独自再确认一番,最后的结论应该是确实更漂亮些。杜圆圆这才放心地准备睡觉。
这段时间,我想,她应该是幸福的,但照例,幸福总不会长久,总有不幸福的事情突然光临。一天晚上,杜圆圆泡过香薰油浴,刚想称称体重,身上就痒起来了,先是背上一点痒,杜圆圆试图自己解决,将手扭到背部,勉强搔了几下,不料越搔越痒,只好趴在沙发上求我们帮忙,没想着,帮她搔痒随后就成了我们的固定节目。白天她是不痒的,她的痒总在泡完香薰油浴后的几分钟内准时发作,开始是我和保姆轮流帮她搔,搔痒的地点从客厅的沙发搬到了她自己卧室的床上,她把上身的衣服脱光,她觉着隔着衣服搔不过瘾。面对杜圆圆广阔的后背,老实说,我有些头疼,而且刚泡过香薰油浴的后背,十分油腻、燥热,就像一片热气腾腾的沼泽地,我的手指在上面运动,很快就感到酸疼。杜圆圆也从不叫停,她的嘴巴捂在枕头上,一直哼哼唧唧的,好像不舒服,又好像很舒服,慢慢地她就打起呼噜来了。
帮人搔痒实在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我觉着这件事应该由何开来来干。杜圆圆是他老婆,他老婆背痒,自然应该由他来搔,况且这么亲近的行为,让别人代劳也不合适。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杜圆圆,还特别强调让何开来来搔,可以增进夫妻感情。杜圆圆心领神会地看看我,说,对,对。以后就由他来干。
何开来帮她搔了两个晚上的背,第三个晚上就躲到酒吧里喝酒去了。不知为什么,杜圆圆也不好意思再叫我们帮她搔,她上街买了一把竹制的挠挠痒,自己搔。但自己搔痒,她又委曲、生气,当然,不是生我和保姆的气,是生何开来的气。杜圆圆觉着我为你减肥,你连痒也不帮我搔,也太那个了。杜圆圆就有点怨妇的样子,大概是那种痒感使她不能自持,她不能一个人在卧室里给自己搔痒,她故意跑进书房,站在何开来背后搔痒,并且嘴里念念着:痒,痒,痒死了。这种表演对别人或许有用,但对何开来没用,何开来只是看着她搔痒。
何开来说,你应该停止减肥了。
杜圆圆说,为什么?
何开来说,我觉得你的背痒和减肥有关。
杜圆圆说,和减肥有关?
何开来说,你不信?
杜圆圆说,那我还不是为了你。
何开来说,为我?
杜圆圆说,当然,我减肥,减瘦了让你喜欢啊。
何开来说,不必了,如果为我,就不必了。
杜圆圆说,你不想我变漂亮点?
何开来说,就那样了,再怎么减,也就那样。
这话大概很让杜圆圆受伤,一气之下,她真的就放弃了减肥。除了一项香薰油浴,瘦身俱乐部不去了,减肥胶囊也停服了,还猛吃各种东西,好像要把前段时间不敢吃的东西,统统吃回来。她的体重在迅速回升,她还每天给自己称重,奇怪的是,她对每天都在增加的肉,不仅不怕,反而很是幸灾乐祸,哈,我又重了几两几两啦。然后把重了几两几两再报一遍给何开来听,好像她身上每增加的一两肉,都是对他的惩罚。
杜圆圆也太不了解何开来了,她想以作贱自己的身体来惩罚他,这是不可能的,我敢肯定,何开来从来就不在乎她的身体,况且,他还说过胖是大俗大雅呢。
不过,何开来还是对的,她的背痒确实和减肥有关,停止了减肥,果然就不痒了。但停止减肥,好像又使她丧失了生活目标,杜圆圆变得有点无聊。
一个晚上,客厅里来了一只苍蝇,杜圆圆拎了苍蝇拍子,结果苍蝇让保姆用手拍死了,杜圆圆很不满意,索性开亮客厅所有的灯,打开纱窗,故意吸引苍蝇进来。这是富人区,苍蝇不多,但也有若干只应邀而来,在客厅里嗡嗡乱飞着。杜圆圆关了门窗,挥着苍蝇拍,兴奋得似乎在准备打一场世界大战。可她在苍蝇面前,又显得很蠢,连一只苍蝇也难以对付。她跟着苍蝇乱跑,跑动起来,全身的肉也在身上乱跑,待她好不容易抖着拍子准备下手时,苍蝇又早隐身了。有时,苍蝇还有意逗她玩似的,嗡的一声刚好撞到了她脸上,撞得她只是乱舞拍子,随时要摔倒的样子。我和保姆见她这么狠狈,不得不笑出声来。我们说,要不要帮忙?杜圆圆挥挥拍子说,不要,我在锻炼身体呢,我不能马上打死它们。她额上的汗都出来了,她确实是在锻炼身体。但她还是打死了一只,她居然不嫌脏,提着打烂了的苍蝇尸体,来我们跟前炫耀,好像她打死的不是一只苍蝇,而是一只老虎。
如果她就这样每天打苍蝇,也罢了,糟糕的是,她把剩余的精力转移到了我身上,她开始来关心我的婚事,就像母亲生前的唠叨,她也要我抓紧找个男人,但她又觉着像我这么封闭的人,自己是找不到男人的,她有义务帮我好好找个男人。一说起我的婚事,她似乎又重新找到了一个兴奋点,她的手、脚以及脸上的皮肉都在动,那样子,我怎么说呢?反正是帮的人比被帮的人急切,不太像是我要抓紧嫁人,而是她要抓紧嫁人。我说,我住你家,你是不是嫌烦了,想早点赶我走。杜圆圆狠狠拍我一巴掌,说,你这没良心的,我是想你早点嫁人,难道你一辈子不嫁人?我才不让你走呢,等找到男人,你就在这儿结婚,我们还住一起。
杜圆圆准备为我找的男人,要像何开来那样,首先必须是一个知识分子。幸好她不认识几个知识分子,她也只能嘴上急切而已。
九月的一个周末,杜圆圆神色诡异地告诉我说,走,我们出去玩。
我说,去哪儿?
杜圆圆说,鹿岛。
我说,鹿岛,干吗去鹿岛?
就去鹿岛。你、我、何开来,还有,杜圆圆刻意停顿了一下,笑眯眯说,还有文如其,我们去度假。
我没去过鹿岛,但我知道鹿岛在东海上,那儿有海水、沙滩、怪石,还有无数的贝类。从箫市码头乘快艇大约一小时的路程,不久,我们就在快艇上了,快艇贴着水面,好像在飞,我是头一次乘这么快的船,很有些刺激。船到鹿岛时,我格外高兴,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这么高兴过。
旅馆就在沙滩后面,从房间里趿着拖鞋就到了沙滩。那天天气也不错,午后的阳光落在沙滩和海面上,有些耀眼。虽然是九月了,而海水还很温暖,有种亲人的感觉,我感到大海在强烈地吸引我,很快我就泡在了海水里。
我游了一圈后,杜圆圆、何开来、文如其才从沙滩后面出来,杜圆圆走路摇摇摆摆的,大老远的就叫,何燕来,何燕来。我应了一声,并且招了招手,表示我所在的位置。不多一会儿,杜圆圆游到了我身边,因为体积大,比重又轻,她一动不动轻易就浮在了水面上,我拿手使劲摁了摁,都摁不下去。
捣乱。杜圆圆说。
我说,呵呵呵。
杜圆圆说,我看你今天心情很好。
我说,是的。
杜圆圆仔细地瞄了瞄我,好像在确认我的心情确实很好,又移动脑袋神秘地睃巡了一遍四周,我们周围除了蓝色的海水,其实什么也没有。何开来和文如其在二百米外的地方,更远的地方零零散散还有几个别的人。
杜圆圆确信没人可以听见我们的谈话,才说,今天我的心情也很好。
我说,好啊。
杜圆圆说,我还有个秘密。
我等着她说,但她又不说了,而且还害起羞来,我说,说呀。
杜圆圆眯了眼说,我跟你哥就是在这儿认识的。
我说,好啊,原来你是来重温旧梦,怪不得你要来鹿岛。
杜圆圆说,今天我们不是来重温旧梦,我们是专门为你来的。
我说,为我来?
杜圆圆说,是啊。
我说,为什么是为我来?
杜圆圆说,不懂了吧,为你介绍对象呀。
我说,对象呢?
杜圆圆比了比那边的文如其,不是在那儿。
文如其?他就是你给我介绍的对象?我突然就大笑起来。
杜圆圆制止说,别笑,别笑,他们都看你笑了。
我把脸埋进水里,再抬起来,才止住笑,我说,嫂子,你没吃错药?
杜圆圆说,死丫头,你不满意?我看文如其,人很好,很适合你,这可是我和你哥商量好的,我管你,他管文如其。
我说,文如其,我们早认识,用得着你们来介绍?
杜圆圆说,用得着,我们不介绍,你们没这根筋。
我说,好吧,反正我今天高兴,你随便介绍什么对象,我都要了。
杜圆圆说,正经点,鹿岛是个有缘之地,我相信你们会成的。
我还真没想过,他们是为我介绍对象来鹿岛的。而这个对象居然就是文如其,我和文如其,本来可以很随便,但经他们这么一闹,好像就不该那么随便了。现在,他不只是我认识的一个男人,而是杜圆圆和何开来为我介绍的对象。我心里在不停地发笑,可奇怪得很,我和文如其果然就有距离了。后来,坐在沙滩上,我们四人自动分成了两小堆,何开来和文如其一堆,我和杜圆圆一堆,中间至少隔着二米的距离。他们在穷聊天,我和杜圆圆在互相干瞪眼,那样子像是两个有企图的女人在窥视两个男人的世界。
他们在谈世界末日。
文如其说,我又想起世界末日了。
何开来说,这样躺着蛮好,还是什么都别想吧。
文如其说,应该想想,现在离明年8月18日,一年不到了,进入倒计时了,在末日到来之前,你想干点什么?
何开来说,我什么都不想干,就这样躺着。
文如其说,我也什么都不想干,但就这样躺着,我恐怕不行,我还得喝点酒。
何开来说,其实,末日挺有意思的,能够成为末代人类也是不容易的,但诺查丹玛斯的末日不够有意思,我们唐朝李淳风的《推背图》里的末日才有意思。
文如其说,《推背图》是怎么说的?
何开来说,禽兽皆著衣,人皆裸体奔驰于天下。
文如其说,哈哈,那么现在就是末日了。
何开来说,离末日还差一点,我们还穿着裤衩。
他们笑了几声,突然就没话了,何开来闭了眼睛在晒太阳,文如其大概还想说话,但何开来没话,他也只得闭嘴。他坐了起来,翘着下巴,煞有介事地注视着天空,好像他脑袋里面有很重要的事情,需要跟上天沟通一下。何开来想必也把我介绍给他了,估计他也在想这个事吧。我觉着好笑,莫名地又有些紧张,我想离他远些,就一个人躲进了海里。
文如其大概也很为难,不约我一次,在何开来面前也说不过去。夜里,在我快要睡觉的时候,他来敲门了,站在门口一本正经说,外面很好,我们出去走走。我想,我们都是在完成任务,我也就很配合地跟着走了。
海滩的夜色,确实很好。像上帝刚造完人后做的一个梦,平静,充盈,满足。风是柔软的、凉爽的,月亮悬在不远处大海的上面,将一道道细小的波浪照白,海滩上空旷无人,时间似乎退回到了很久以前,我站在水中,等待着波浪过来,“哗”的一声碎在我的脚下。
人置身于这样的空间之中,大概很容易动情。
何燕来。文如其在我身边叫了一声。
我说,嗯。
文如其停了停,说,我不知道他们叫我来鹿岛,是为我介绍对象来的。
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开玩笑,不用当真。
文如其说,不,我想过了,我发现我确实喜欢你,只是我们原来太熟了,太熟了容易忽略,而且,而且也有障碍,要不是他们点破,我还真不知道怎样开始……
我惊惶地抬头望他,他站在月光的正面,月光照着他的瘦脸,看上去非常认真。忽然,他伸过一只手来,把我的一只手抓在了他的手中,并且试探性地捏了捏,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表示不妥,过了一会儿,倒是他感到不妥了,起码他不知道该拿我的手怎么办,他严肃地看了看我,慢慢就放手了。
我是否也有点喜欢他?
第二天一早,我上海滩散步,文如其已经立在海滩边缘,面朝大海,似乎在发呆。我正考虑是否该跟他打个招呼,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看见我了,随即朝我走了过来。
我正想找你。文如其急急忙忙说。
哦。我说。
但他突然哽住了,好像有什么重要的话堵在喉咙里面,吐不出来,很痛苦的样子。
我说,怎么了?
文如其喉咙滚动几下,又咳了一声,说,我一夜没睡。
我说,哦。
文如其说,我想了一夜,你是个好姑娘,我真的喜欢,但是,我想,我不合适,我,我,还有你哥,我们不过是废物。我会害了你的。
我说,哦。
文如其说,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吧。
我说,本来就什么都没发生。
文如其说,可是,昨晚我拉了你的手。
我说,没事,不就拉了一下手。
文如其感激地看看我,转身走了,没走几步,就开始奔跑起来,好像他不快跑,我会追上去抓他似的。我掉了个头,刚好看见太阳从大海的深处升起,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竟流了下来,大概是阳光刺眼吧。
虽然什么也没发生,我还是有点被抛弃的感觉。不过,这事对文如其的影响可能更大,鹿岛回来后,他再也不敢来杜圆圆家,弄得何开来想见他,也只好到外面去,很不方便。当然,最生气的人还是杜圆圆,好像文如其拒绝的人不是我,而是她。很久以后,想起文如其,她还愤愤不平,哼,文如其,什么东西?也许,她也不是真的生气,她只是觉着有义务帮我骂骂而已,因为此后,我就完全谢绝了谁帮我介绍对象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