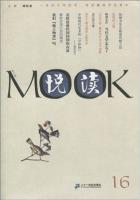在我只能搭着小凳爬上那把沉大的旧式雕花靠椅,立在座面上,才将这个大而重的柜子门揭开,又学着老人的样,很吃力地用一根黄褐色的、光溜溜的竹竿,撑住柜门,出现在眼中的东西,已叫我惊喜而不得不僵在那里,想这大柜子,是如此之大,藏猫猫是决不会有人找得到的,可里面却装着足够吃一辈子的好吃的香香,难怪这里总有不断的花生、冰糖、红苕丝、芝麻饼、豌豆、胡豆好多好多数不清的收藏一次次,一次次拿出来,神秘得好似一个“神柜”,要什么就会有什么:一只手工编织的粗麻袋,长长似兔耳的结拴紧花生;土罐粗糙的圆体上一圈圈线纹,红色方纸封住醉香的醪糟;油亮亮的木升子棱廓模糊,盛着金灿灿的黄豆;细蔑竹兜褐色沉暗,盖起的是方糖、寸筋糖、红糖和水果糖;白底蓝花细瓷瓦罐,尖尖的顶口里肯定是菜籽油;扁篾收口的大箩箩是桐子油浸过,年久已没有亮光,里头有白米、干面、麦粒、鸡蛋……我想起老人的慎告:注意门滑下来,砸伤人。
想起老人的话的神奇、想起老人的慎告终会灵验,我赶快小心又小心地将撑门的小竹竿取下,让柜门盖紧,一个土铁黑门扣扣起,再上古铜味长锁,“咔嚓”被反锚住。
一把大的长形铜锁,把楠木大柜锁住。只有让那枚长长的钥身插进去“咔嚓”才能打开。
黑漆斑驳的楠木大柜,稳稳实实地立在卧室的墙下,已有些发灰的白土墙上,挂着一串玉米、高粱、莱种及马、恩、列、斯、毛的粗制画像。一个物质文明、一个精神文明都在墙上和楠木大柜上了。我的祖母是从她的先辈手中传过来的,她的妈妈又从先辈那里接手的,传于何时,出于谁人之手,这个楠木大柜是无人知晓的。
楠木,是非常稀有的乔木,主要生长在南方的山区。如今,人们是见不着楠木这样的树木了。有谁舍得将它留给今天呢?过去,有钱人家是不惜本钱买这种木来打家具,作为一种固有资产来世代相传的。因此,很少有把楠木用来雕镂后做成家具的,那镂后的木屑太可惜天物。
在我们山区,谁家有件楠木家具,几乎是一提便知:呃,你说那处东西,石柘木石柘的白房子就有一个楠木柜子。上了些岁数的人,他们除了自己的亲戚还记得之外,要问他们,此地有过多少楠木树,他们如数家中逝去的亡灵一般地讲给你听:某年某月某地方有棵参天的楠木被不争气的儿孙分家伐砍“五马分尸”了,只留下一个“楠木坳”的地名。在这些老人记忆中,直到四十九年以后,他们记得还存在的一棵楠木树,也在石柘木石柘的石房子朝口门外,曾经历了入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劫后余生的楠木树。
我曾亲眼见到过这棵楠木树。
这棵当时幸存的楠木树,还不大,长在白房子高高的白墙外的南竹山旁,在它的下面有口井,人们因此把此井叫作:竹山旁的楠木井。楠木树的树身是直直的,约有鱼二碗般粗,其树壳是蓝幽幽的,细腻如人的皮肤,枝柯不张不散,仅从树干长出细小的微枝,叶是细碎、深蓝,叶面色深,水光柔亮华丽,叶背色浅有柔柔的绒毛,树却透出一股轻弱的香气,极好闻。特别是它下面的井水,是庄稼人暑天小憩时最爱喝的,这水沾了楠树的体气,回味也带着楠树的珍贵香韵。
那时,我太小了,还不懂得珍惜,往往趁大人不在的时候,用稚气的小手,把楠木大柜还残存的斑斑黑漆,一小块一小块地抠下,只觉得甚是好玩;有时还把白色的粉笔和红色的粉笔,毫不在乎地涂鸦在楠木大柜的四周,以取悦或满足一种幻想的放纵;而每当大人将楠木大柜叮当扣上、锁住的时刻,总把它神神秘秘地放在心里,老也揣不透被锁的究竟是些什么。看见楠木大柜,我的眼前就灵灵地出现白房子前的那棵楠木树的亭亭玉影,如一个清纯的女子,在等待着未知是好是歹的命运,是谁将它伐倒,留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