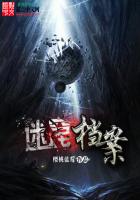转天一早,太阳刚冒个头,许飞带着他仅有的财物,一个古旧的旅游包,出现在北门大街的十字路口。
昨晚一夜未睡,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灰黄的街灯下,把他对杜小莫的点点滴滴一一从内心深处挖了出来,人结婚了,结婚了,结婚了,一切都成了过去,让这一切都像这五年的牢狱一样过去吧。
不管许飞是不是真的就这样轻松的放下了这一切,总之第二天一早当高杰和王刚出现在他面前时,许飞又恢复了像昨天刚出来时的那个状态。
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停在许飞对面,车里的两人看着正左右张望的许飞,王刚坐在后排,打着手式问高杰,“他想通了吗?”
高杰嘴一撇,“放心,他会想通的,到是我想不通了,你说,三子,你说,这一大早跑火葬场,不嫌晦气呀”
王刚弯腰离座笑着拍了高杰一下,随手用力按了几下喇叭。
许飞闻声望了来,只见高杰正坐在对面面包车里朝他招手。
半小时后,三人在市火葬场门口停了下来,许飞拉开车门钻了出来。
“你们去,我,我找地方停车”高杰找着借口不想进去。
多年前高杰就怕见到和死人有关的一切东西,在没有搬家之前,在他们家楼下转角处有家殡葬用品店,高杰每次晚上回来都宁愿多走一里多路绕开,因为在他上高中的时候,他亲身经历过一次让他至今想起都觉得毛骨悚然的事。
那天晚上,高杰下晚自习,由于快到高考,学习任务重,所以等高杰到家楼下时已经夜里十一点多了,这个时候的北门不比市区,幽长的马路上,一辆车都没有,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发着微弱的光,将一切都蒙上一抹惨淡的灰暗,其中有一盏大概是接触不良,灯光时亮时灭,路边的绿化带如同一个个朦胧的人影在那路灯下时影时现,高杰独自一人,哼着时下流行的歌曲,心无旁顾的走在这条幽暗的马路上。
再往前转个弯就是他们家那幢楼,如同往常一样,转角处那家殡葬用品店还在照常营业,店里亮着灯,以示里面有人,店内空间很小,顶多两三个平,里面三面墙上都有一层层的货架,整齐的排放着各式骨灰盒,上面压着黑色的布幔,店门口码放着一个个待售的花圈,花白花白的,在夜色中给人一种厌烦而又不敢近前的感觉,门口的墙上挂着一个像框,那是一幅黑白素描人物上半身肖像,画中是一个老者,看起来慈眉善目,不过要是在晚上,凭借着店里那点微弱的灯光,随便扫上一眼,总感觉那画中的老者沉暗无光的眼神正在盯着你,阴森森的,让你不得不加快脚步。
高杰走在店门前,下意识的不去看店里的一切,低头快步向前走。
突然,就在高杰刚刚从店里的灯光下走过时,一个身着一身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子从店门口立着的花圈后站了起来,高杰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心头一阵狂跳,街灯昏暗,他看不清小女孩的脸,这都快半夜了,怎么会有一小姑娘在这,没听说开这家殡葬店家里有个小女孩。
高杰僵了一会,强作镇静,正打算不管不问移步要离开的时候,那小女孩却朝他移了过来,高杰屏息着,一点脚步声也没听见,他慢慢地转动着眼睛去看小女孩的脸,天呀,他差点叫了出来,只见小女孩惨白的脸上血迹斑斑,那小小的鼻梁边上一团血肉模糊的物体在左右晃动,呀,天哪,她的眼珠正挂着呢。
高杰没命似的往家跑,他不敢回头,他总觉得那个小女孩就在他身后,只要他一回头就能看到那张挂着眼珠子的脸。
第二天,下午放学,高杰刚下公交车,准备换乘另一班车的时候,却看到在公交站牌边的人行道上围了一圈人,还有人在拼命的喊着快打120,他好奇心起,挤了进去,可就是这一眼,让他终生后悔,那围观的人群中,一辆小轿车前轮压在了绿化带上,后轮底下一个六七岁的的小女孩正在抽搐着,那雪白的连衣裙沾着鲜红的血格外刺眼,高杰头一下就大了,回想昨天晚上的事,在这一圈人中他还是感觉到从头到脚都是冰凉的,那天回家,高杰大病一场,之后再也没有在晚上走那转角处的殡葬用品店,也就是打那之后但凡和死人有关的东西在高杰这都是禁品,绝对不看不碰,在马路上遇到车祸也不看一眼,这么多年来都成了他的心病。
高杰将车停在离火葬场一百多米外的地方,下了车,对着许飞连连挥手,示意你们去,他就在那等。
许飞笑了笑,和王刚转身朝火葬场大门走去,他知道高杰那点事,摇摇头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三子,你知道王刚为什么不敢进这里面吗?”
王刚摇摇头。
许飞边走边道,“十年前,他被吓怕了,也是,倒霉催的,什么怪事都让他赶上了,我和他说了多少次,那店门口的小女孩不是什么鬼怪,就是她妈妈晚上出门办点事,回来晚了点,那女孩出门去找,走到那附近的时候摔了一跤,额头摔破了,哪有什么眼珠子挂在脸上,那纯粹是高杰那小子被吓蒙了,自己把自己给吓着了,后来那殡葬店的老板听到声音出来把她送回了家,还有那在公交车站牌边的那个小女孩,压根就不是同一个人,只不过穿的衣服差不多,后来被送到医院,万幸,救了过来,这高杰愣是不信,我说带他亲眼去看看那两个女孩,他死活就是不去,这都落下病根了,还好面子,不让我别把这事告诉别人,十年都过去,没治了,人小姑娘都变大姑娘了,想看都没得看了”
王刚听了一乐,回头看了高杰一眼,对他伸出个小拇指,一脸的兴灾乐祸。
走过大门,直接来到院内,看门的老头连问都不问,大概也没有什么人闲得没事做大清早跑到这地方来。
院内停着一辆灵车,看来今天这火葬场的生意惨淡,只有一拨人正排队走进追悼厅,当然这里的生意越少越好,这些人个个表情沉重,不少人脸上还留着泪痕,想必他们的一位亲友正在里面作遗体告别。
许飞从没来过这地方,站在院内四下看了看,望着左右两边那一堆的门,在这地方他可不想走错了门,于是扯了扯王刚,转身朝传达室的老头走去。
“你好,大爷”许飞很客气。
也许是老头在这太久了,见惯了生死离别,对活人也渐渐变得麻木,他放下手里的报纸,打眼瞅了瞅许飞,没说话。
许飞也不在意,什么样的环境出什么样的人,“大爷,请问取骨灰应该走哪个门?”
老头还是没说话,随手指了指院内左边那一排大开的门。
许飞顺眼一望,那可两扇门,到底哪个呀?于是他又想开口,却发现那老头屁股一扭,转过身继续看着他的报纸。
王刚是个火脾气,这什么人哪,手一抬便想走过去揪住那老头的衣服,再挥挥他泰森式的拳头,吓唬一番,许飞忙拉住他,“算了算了,走走,过去找找”
两人来到那两扇门前,也是,就算是厕所那也得标个男女区别,这么庄重的地方你咋也不写个标识。
许飞和王刚在门口等了一会,想等出来个人问问,但十分钟过去了,一个人也没见到,算了,一间间找吧。
许飞对王刚一努嘴,指指第一扇门,随便了,先看看这个。
两人一前一后,门半掩着,许飞轻轻推开,‘吱吱’作响,屋内光线不是很好,有些昏暗,在靠里墙边放着几辆类似于医院里的活动病床,里墙上有两扇紧闭着的小铁门,二人走了进去,立时被一股浓烈的焦糊味给呛得直皱眉。
“有人吗?”许飞喊了一声,屋内没人回答,只有一连串嗡嗡声,似是大火燃烧的声音。
王刚指了指里墙的铁门,二人谁也没进过这地方,天知道这些屋子是做什么,好在是比起高杰,他俩的胆子要大些。
许飞四周看了看,这屋子里了那几张铁架床再无一物,于是他走向了里墙的小铁门,伸手轻轻地推开了。
扑面而来的热浪让两人忍不住一偏头,里面有两个带着口罩的中年男人,浑身脏兮兮的,正将一根铁棍从面前的一个小洞里伸进去,时不时来回拉几下,许飞掩着鼻子想问那两人,可当他刚把头探过去的时候,不经意间往那洞口里扫了一眼,也就一眼,头猛然间大了,从那冒着火苗的小洞中,在那中年男人手中铁杆前方,在浓烈的火焰中,一个人,浑身着火的人,他的上半身正随着铁杆的进出而起起卧卧,胳膊和腿还不时的一阵阵颤动,许飞再也忍不住了,他呀的一声叫了出来。
“谁,谁呀,你们怎么进来了”那中年男人一回头,这种地方就算是死者的家属也不是随便能进来的,当然了,一般也没人想进来。
许飞没有回答,拉起王刚就往外跑,他的胃里一阵阵翻腾,快步冲到门口,连连干呕。
王刚没看到里面的情形,指指里面,意思是在问,这里面什么东西?
许飞想吐吐不出来,连连摆着手,“别提了,烧尸首呢”
这时一个和里面人一般穿戴的男人正从另一扇门里走出来。
“你们干什么呢?这里面不能随便进”
许飞大喜,忙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递给那人,半个字不带停顿地将他的来因说了出来,免得还像在门口问那老头似的只得了半个答案。
“是这样,江南监狱一个月前送了一名姓赵的来这火化,他的骨灰应该还存在这吧,我是来取的,这,这是江南监狱开的证明”
那人看了看证明书,想了想,点点头,“对,是有这回事,老赵头,有姓无名,没有背景,好记,早干什么去了,放这都一个月了,跟我来吧”
那人走进边上的门,两边屋子大小差不多,只不过内墙上是一排排如抽屉般的小格子,那人手指在那些小格子前划拉着。
“那,在这”说着便走过去随手拉开,从里面拎出一个灰色的布口袋,举向许飞。
许飞看了看王刚,伸手接了过来,“就在这里面?不是应该……”许飞比划着,咋得应该也有个骨灰盒吧,没听说还能用口袋装的。
“哦,你是说骨灰盒吧,有呀,回头看”那人一指许飞身后,“那,最下面这层是普通的,五百,中间这层上点档次,两千,最上面那层,那就讲究了,一万起价,最高五万,你选一个吧”
许飞摸了口袋,只有昨天出来时监狱给的这几年他在里面做工的两千多元钱,想想老赵头是他在里面唯一的亲人,许飞一指中间那层,“两千的来一个”
许飞小心的将布口袋解开,里面是一堆碎骨头渣子,王刚托着骨灰盒蹲在地上接着。
“师父,大飞来接您了”许飞轻轻的抖动着袋口,生怕洒落一粒,回想起老赵头生前的模样,许飞一阵心酸,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到了,也只能化作这一捧灰尘,连是不是他这人都分不清了。
在边上的工作人员,拍了拍许飞的肩膀,“哎,一会出门,上对面那二楼交钱,办手续,知道吗”
抱着老赵头的骨灰,许飞站在马路上,轻轻拍了拍盒面,望着远方微笑着说,“师父,您生前有姓不敢有名,别担心,大飞答应您的事一定办到,过几天,我就送您回家,入土为安”
高杰远远见许飞走来,忙将后车门拉开,闪到一旁,望着许飞手里抱着的东西,连连摆手,“走,走那边,离我远点,看到这东西我就晕,盖好,千万别告诉我你抱的是什么东西,你想去哪?”
“城南七十五里,南分路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