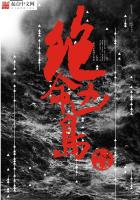我高三的寒假只身一人从南京出发到四川的爷爷家过年,想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秦风,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爷爷。
当时我正陪爷爷在封家园里听大戏,这是家里的传统。因为奶奶是大年初一的生辰,所以每年过年爷爷家里都会搭戏台,现在奶奶早走了许多年,听说她死后让爷爷把骨灰都洒了,但封家园里的戏一直唱到了现在,年年如此从未间断。
那次唱的是汤显祖的《牡丹亭》,我到的时候正好碰上台上浓妆艳抹的杜丽娘在唱那句“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
爷爷在台下的太师椅上假寐,听说他和奶奶第一次相遇,听到的就是这篇《牡丹亭》,当年金陵城内传唱的那句“秦淮十里醉千场,不及莺歌一声响。”说的就是我奶奶。
毕竟落魄公子哥和戏院名伶之间的爱情,无论是放在哪个年代都是段风流佳话,我爷爷年轻气盛的时候得罪了不知哪一路的人,奶奶为了救他,被逼服了毒,九死一生的捡回条命,但那名震金陵的嗓子确是废了。
后来爷爷重兴家业,在南京打出了片天下,奶奶却不愿意待在那纸醉金迷的伤心故地,在我父亲还小的时候,便举家迁到了四川。再后来我父亲因为求学而重返南京,这便都是后话了。
“你奶奶当年可比他们都漂亮,唱的也比他们都要好。”
爷爷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我忙去搀他,这次回来他好像比去年苍老了许多,大概人老去的速度是会与日俱增的吧。
“您年轻的时候也比这些小生俊啊。”我笑着说,但其实我没怎么见过爷爷年轻时的模样,他不爱照相,听说常年都面若冰霜,是在娶了奶奶之后才缓和了许多。
爷爷撇开我的手,自己缓缓站起来,我才意识到园子里还有其它道上的人。
“你也就这张嘴甜,油嘴滑舌。”
“还不是您老给我糖吃。”
众人哄笑,我却被爷爷手里的折扇狠敲了一下,痛的龇牙咧嘴。
“都这么大了,还是这幅样子,秦风在你这么大的时候都在外面帮我带人了。”
我很少听爷爷说道上的事,偶尔提起也只是说当年在南京那会儿,但毕竟年代太久远了,那些事除了给我留下过一种向往以外,并没有什么用处,现在提到的秦风大概是新秀吧。
“阎王谬赞了,少阎王会读书,肯定比我们这些混混强。”
然后我就在众人之中第一次见到了秦风,他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但气势却不是我所能够比较的。深冬腊月的他只穿了件黑色的短袖,一条银色的牛仔裤,精神得犹如旭日,在一院子人里头显得格外扎眼。
爷爷听了秦风的话,笑逐颜开,“就他读的那些混账书,能按斤称不?”
秦风听后也笑了,恍惚间我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但随即又否认了,我平常生活里要是见过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搞忘。
大概是从第一眼开始,我就觉得和这样的人做朋友是件很酷的事情,秦风符合我打小对爷爷那些故事里的所有向往,在我的脑子里,爷爷年轻时就应该是秦风现在的模样,痞气逼人的同时也英气逼人。
“看什么,现在知道什么叫人比人气死人了吧。”爷爷见我有些出神,呵斥道。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爷爷也正恨铁不成钢的看着我,只因当着众人在,才没有发作。待他重新坐到椅子上,我也才小心翼翼的跟着坐了下去。台上的戏还没停,那柳梦梅还在生龙活虎的唱着,台下的爷爷却像又睡着了一般。
那戏众人听到晚饭时才散去,霎时间方才还热热闹闹的园子,走得只剩下我和爷爷还有秦风了。我有些纳闷,往年都是只有我和爷爷两个人,今年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留秦风下来。
“往年秦风过年都是在山西那边帮我坐场子,今年他回来了,我就让他也住到封家园里了,”爷爷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平日里你不在,这院子里就我一老头子住着,怪冷清的。”
“阎王,听起来我是该早些时候回来的。”
秦风和爷爷一路说说笑笑,他们提到的那些事,我一无所知,只能一言不发在旁边跟着走。终于等到他们聊完,我们也走到了饭厅,管事的布完菜之后,爷爷和秦风也意识到我在一旁安静了太久。
“来,你每次回来都跟从难民营出来一样,瘦得跟猴儿似的。”爷爷说着将宫保鸡丁往我这里推了推,“你可别学着那些人去稀里糊涂的减肥,咱们封家的不愁找不着对象。”
我听了爷爷的话,有些尴尬的看了秦风一眼,发现他正似笑非笑的在埋头喝汤。
“别人见了我都说我胖了好几圈,就您还硬说我在瘦。”
爷爷却异常固执的争辩道:“你和你那挨千刀的死爹一个样,都遗传了你奶奶骨头小的好处,怎么吃都不胖。”
我听了爷爷的话差点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看吧,您都说了,我这体质就这样,还是让我为国家省点粮食吧。”
连秦风听了我这番歪理都忍不住笑着看了我一眼,爷爷在一旁也是哭笑不得。
“少阎王的理,估计也只有同那花佛爷才说的清了。”
我不知道秦风说的花佛爷是谁,但听起来似乎不像是本名,谁没事管自己叫佛爷啊。见爷爷的反应他应该是认识的,听了秦风的话正笑得合不拢嘴。我有些生闷气,看他们的样子想来说我和那花佛爷像,可不是件多好的事。
“等你过些年上了道,我就带你去拜访拜访他。”爷爷见我有些不大高兴,劝慰道。
我赌气似的说,我才不会去见那个姓花的,也不会被爷爷带上道,我心里也确实是这样想的,对那些东西向往归向往,你要让我舞刀弄枪的真的去感受一下,怕那滋味也不好受。
“小阎王,花佛爷不姓花,那是道上的兄弟们给他起的绰号,久而久之大家就都这么叫了。”秦风给我解释道,“他本身是个散客,只要给钱,什么都能做到。早四十年前,你就是想要***里头那群老头子的命,据说他都能给你弄来。但他神出鬼没的,想和他搭线做买卖,得全靠运气。”
我听着越发觉得秦风说的这个人像是武侠小说里头的世外高人,但实际上我也清楚,秦风这番话里头多少有些夸张。
“你爷爷我都是很偶然的机会才见到的他,勉强和他有过联系,几年前他应约来过一次CD。”爷爷见我不信,又补充道。
爷爷话音刚落,我就听见窗外下起了雨,来势很急,天霎时就暗了下去。
“那他现在还能做你们那些生意?一个老头子,单枪匹马的能干什么。”还是个半截身子都埋土里的人了,还能掀起多大风浪来?
“花佛爷这个名号在道上传开,确实是传了好几十年了,但上次他来CD,光凭那身手,怎么看都不像是个七老八十的人。只是可惜他常年戴着人皮面具,究竟面具底下是个什么模样,也没人说得清。”
“说的可真悬,那花佛爷可都快要被你们给吹成神了。”
爷爷听了我的话顿了顿,开口道:“那次他走后,我派了好几路人去跟踪他,因为那时候的我同你一样,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存在。”
外面突然炸起一声惊雷,房里的灯猛闪了几下,模糊中我隐约听见了爷爷的后半句话。
“果然他不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