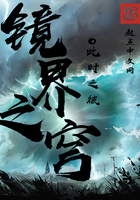“呀···”
罂粟不自觉的轻呼出声,这哪还是一个人,只见她整个脸上的皮像被硬生生的撕去了一般,露出阴森的白骨,上下嘴唇被强行缝在了一起,血肉模糊间隐隐露出的双眼紧闭,没有一丝光亮。
尽管一切都像极了那老妇,但罂粟知道,这不是她。
拔出软剑,罂粟轻轻的切断她唇上粗厚的麻线,一挣脱了束缚,嘴里的血都争先恐后的往外冒,露出里面被血染红的牙齿。
“幻影,是你么?”
罂粟的声音带着轻颤,她的视线渐渐的模糊。
“幻影,是你么?”
“幻影,是你么?”
······
罂粟一遍遍的呼喊,直到那血红的瞳孔微微的眯开一条缝。
“幻影,是你么?我是罂粟!”
“罂···罂粟,你···来了!”
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几个字却像用劲了全身的力气一般。
这还是那个跳着笑着嚷嚷叫唤的幻影吗?
只两天,她们只分开了两天,她怎会就成了这样?
“罂···罂粟,帮,帮我!”
她依旧呢喃着,有晶莹的液体从那血红血红的瞳孔中流下。
“我会救你出去,什么都别说了,什么都别说了!”罂粟的声音有些梗咽,若不是她自己的自以为是和判断错误,幻影又怎么会成这样?自己究竟做了什么?
“别,别···”
幻影挣扎着伸出伤痕累累的手,拉住了罂粟的衣袖,她的声音低弱但急切,声声都扣在了罂粟的心上。
“罂···罂粟,帮,帮我,我···我有话···要说!”
有话要说,但是却要拿她的命来换吗?
罂粟低头看着虚弱的幻影,心下一紧,犹豫了半响,终于内力一动,手上顿现两根银针,她慢慢的将它们射进了幻影的头顶。
“幻影,你说吧,我听着!”
罂粟将头低下,凑近幻影的嘴,心中酸涩难当。
“罂粟,对不起,我没有遵照约定,我把我们的计划禀告了少主,我,我没办法对他隐瞒,他是那样温润的人啊···”
幻影的思维慢慢的恢复,手脚也渐渐有了些力气,她抓紧了罂粟的手,说话的速度很快,连带着受伤的声带,音质有些模糊!
“罂粟,但我总归没有辜负你所托,那老妇,我已经将她送出去了,但你,一定要在寅时之前去乱葬岗将她拉出,并服以龟息毒的解药,不然,她会永远都醒不过来了!还有,还有···宫中的事你不要再去调查了,他们,她们是我们斗不过的!”
“罂粟!”不等罂粟回答,幻影渐渐的急切起来,“别怪我,我以为我可以给她易容,却不想她已经是母体,已经是母体了呀!”
母体?罂粟自然能听得懂,在易容界里,母体是最大的牺牲,就像现在的幻影一样,将自己的面皮献出来,而自己本身除了已经被毁容外这辈子都不能再被易容。
“呵呵···”幻影说着说着就笑了起来,“我以为那只是傻瓜才会做的事,却不想我也做了,罂粟,罂粟···”幻影用仅存的力气使劲的抓住罂粟的手,尽她最大的努力将最后也是最想说的话说了出来:“你告诉他,告诉他我总算完成任务了,这辈子,我无怨无悔···”
“他是谁?”
其实应该猜到,但罂粟还是问出了口。
“呵呵,是啊,他是谁,神那般的人哈,呵呵···”像被什么呛到一样,她不住的咳嗽,嘴间有不停涌出的血液,慢慢的将罂粟的手也染成了通红。
“幻影,对不起!”
罂粟慢慢的开口,在幻影的耳边,她知道她已经尽力了,但朦胧间看见她原本还血红的瞳孔正逐渐的暗淡下去,渐渐的没了光泽。
而她的唇却还在不住的呢喃着一个名字:
“无尘,无尘,无尘···”
声音愈来愈若,愈来愈若,直至再也听不见。
罂粟怔怔的放开手中的人,那单薄的身躯失去了支撑轰然倒塌下去,无声无息,只溅起了几滴鲜红的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