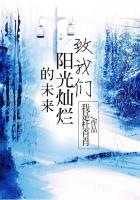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耕过田,我只是偶尔在田埂上捡捡稻穗,但那些用汗水浇灌出来的庄稼离我很近。镰刀割过稻秆的声音,打稻机滑过田埂的痕迹,现在已经很难听到和看到了,人们甚至逐渐忘记什么时节播种,什么时节插秧,什么时节灌溉,什么时节收割;忘记了水泵的零火线怎么连接,闸刀怎么安放;忘记了独轮车的结构,平稳的行驶,忘记了许多。
因为这些很辛苦,辛苦了半生却还一无所获,而被物质充斥的社会的发展,那几亩并不富饶的土地早已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大家宁愿舍弃那亲切的热土也要去到那陌生的城市里飘飘荡荡。
于是小村里只剩下老弱病残的人们,就连小孩也随着父母进了城市。他们学了城里的话,不再讲自己的话,用了城里的工具,有了城里的思维。这些或许都是好事,我只是担心那些城市化的步伐可能让本来应该播种的农田筑起一幢幢高楼大厦,一片片土地耸起一座座高压电塔。
我站在高岗上,高压电缆上流过的电像大雨般劈里啪啦。这个季节原本应该是稻谷从打稻机中流出的劈里啪啦声,但只有寥寥无几的几个身影在忙碌着,剩下的就是杂草的茫茫一片。我走到那几个身影旁边,跟他们聊着:还忙什么呢?农业都要工业化了,高新的技术都代替了人力,还忙什么呢?他们看着我笑着,说我是痴子,我也跟着笑着,像痴子一般笑着。
我拾起一根稻穗,我想得太多,这些根本不是我可以考虑的,我只需要想想一些简单的俗事就好。是的,他们虽然在忙,但他们相互配合着,团结着,欢笑着,这让我真的想起了一件叫我极为心伤的事。那是母亲的艰苦,是一个女人的艰苦,也是庄稼人的艰苦。
我实在太小了,以至于我的记忆还不那么明朗。父亲在远方,母亲的风湿都是从那时落下的。
农民着实什么也没有,除了那几亩贫瘠的土地,几亩贫瘠的土地便是他们的一切,因此我们家的几亩地也萦绕着母亲的艰辛。
田里的水又干了,那时还没有水渠,农民们需要背着那种铁质的大水泵,有马达的一侧放在池塘里,另一侧对着农田,然后拉出一条皮线,用竹竿把电线接到电线杆上的零线和火线来接通电流。虽然听起来不复杂,但有些困难不是只字片语能够体会的。
这种水泵极为沉重,需要人力车拉着,但农村的路窄小的很,颠簸的很,人力车便会经常陷入泥沟。况且田间的路人力车也是进不去的,人们只有拖着沉重的水泵,喘着粗气往来着。
田间有一种吸血怪物,它们会在人们不经意间从脚下钻进肉里,在那粗糙的皮下一耸一耸的游动着,我曾经见过,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总是让人不寒而栗。
天已经快黑了,我静静坐在田边的埂上,手上握着一根还没生出谷子的稻穗,不停的摇晃着,因为那密密麻麻的蚊子几乎要将你蚕食。
母亲的肩膀早已厚厚隆起了密密的水泡,她正看着一个地方,我也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我似乎嗅到一股香气,似乎看到有人在向我们招手,但其实我终究什么也没看到,因为我几乎还没稻杆长,我只是看到母亲有一丝失落,心酸。
母亲的田离祖父的家很近,是正对着的。我或许是千真万确的闻到了香味,他们习惯的把桌子搬到外面来吃,他们说着,笑着,他们只要夹一下菜就可以看到我们,但是他们终究是看不到我们的,因为他们不幸的患了一种斜眼的病,这是多么的不幸——不幸极了。
母亲不愿再看他们,而转向看着我,那种凄凉我至今也没法体会。
丰收的季节最使人们兴奋,可母亲恰恰相反,有些担心,因为别人田里都是三五成群的忙碌人,而母亲的田里却形单影只。
我坐在独轮车上嚼着母亲给我削好的地瓜,我喜欢地瓜在我牙齿间咬碎的声音,我想用这个声音去掩盖别人田里的欢笑声。
那不是别人,那是我的祖父和我的叔父们,他们就在隔壁,他们挑着箩筐,举着担子,他们瞧着是多么的高兴。母亲再一次望着他们,但他们的病大概可怜的病入膏肓了吧!
我的地瓜嚼完了,我开始等候那些渺小的但成群结队的蚊子嚼我。
母亲显得十分疲惫,母亲望着天空没有过分的奢求,只祈盼不会下雨,因为母亲一个人那单薄的肩膀是搬不完田里所有的谷子的,即便那并不很多。天边闪闪着几点星光,让母亲舒了口气,至少今晚不会落雨。
母亲吃力的推动着独轮车,车架发出的吱呀声回荡缕缕,像是诉说着什么。我悄悄回头望了望那个方向,他们在整理刚运回去的稻谷,笑得那么欢乐、那么喜庆,而母亲的背影却让汗水印的异常孤落……
临书仓促,不尽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