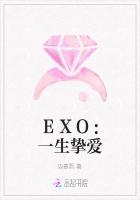毛泽东不相信搞建设比打仗还难,认为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大兵团作战”,就能够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就可以像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胜利一样,实现经济建设的“大跃进”。因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的不决定于这种或那种条件,而决定于人,决定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不是鼓足干劲、是不是力争上游、是不是事事多快好省。群众说得好:‘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了的”。“赶上英国,赶上世界一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起决定作用的,也不是时间,而是人……是人的决心、人的干劲”。于是,群众性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普遍展开。虽然毛泽东也有要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赶超发达国家的认识,但他把赶超的重点主要放在了钢产量上。片面强调钢产量的赶超,导致了“大跃进”运动中全民炼钢、“以钢为纲”的不正常现象,并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衡。
应该说,赶超发达国家,从政治意义上及现实意义上来看,都是非常必要的。确立这样的奋斗目标,对于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但是,赶超发达国家是一种发展战略,它必须有严格的科学分析和论证,使其符合经济建设自身的规律,如果超出了经济建设自身的规律,就容易产生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情绪。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真正决定力量,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也只有在认识和尊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而且还要受到社会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制约。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过高地估计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结果陷入了主观与客观相背离的困境。
强有力的新中国中央政权本为后发展国家进行发展的后发优势,最终因过度集权和专断而变成后发劣势,阻挠了现代化的理性政府的形成。
2.意识形态的强化导致中国与世界现代化内在联系的阻隔
我们知道,二战后,美苏两国的争夺表现出了剧烈的意识形态之争,时任美国海军部长的福莱斯特说:“我们正致力于保持一个资本主义——民主方式得以继续下去的世界,而俄国人如果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话,就要以这个制度的垮台,为他们的利益所在。”于是,在两大阵营格局的基础上,各国的外交政策和行为深受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以至于“意识形态”成了两种社会制度的代名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地深深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
首先,意识形态的趋同,使新中国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一经进一步尖锐化,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全地球都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何况中国是在同一个深入国土的帝国主义奋斗,没有苏联帮助,就休想最后胜利。”可以看出,这时的毛泽东就已经有了“一边倒”的思想。1947年9月,日丹诺夫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提出了世界已分裂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的理论;12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放弃了中共基于“中间地带”理论的三分世界法,而使用“帝国主义阵营”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来划分世界力量的格局,并把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看成苏联领导的反帝斗争的重要方面,将中国革命力量看成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共不仅接受了苏共的“两个阵营”理论,而且明确了中国是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即苏联)一边的。
1949年3月,毛泽东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的及美国的工人吸引了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也能胜利……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同年6月4日,刘少奇又指出,在两个阵营中间,实行“中立”是不可能的,那只不过是一种骗人的鬼话。而毛泽东在其《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地阐述了“一边倒”的思想。他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的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可见,在“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一部分”的前提下,联合各国无产阶级特别是苏联,这已是顺理成章的事情。1956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讲话中谈及此举的意义时,就说道:“我们提出‘一边倒’,是意味着在政治上必须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团结起来,同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边,不能一脚跨在社会主义方面,一脚又跨在西方资本主义方面。所以,‘一边倒’就表明,我们在政治上同资产阶级国家断然分开,打消一切西方国家的幻想。”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一边倒”已经不是什么选择,而是必然结果。
其次,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又使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从“一边倒”转向“两条线”战略。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对马列主义的一些理论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原则问题以及当代世界形势的若干重大问题,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对于这些分歧,毛泽东始终主张通过内部讨论来解决,而不应影响两国正常关系。但赫鲁晓夫从追求同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的外交战略出发,一心想把中国纳入他的战略体系,并为此不断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致使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认为苏共已经变为修正主义政党,苏联已经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中苏关系日趋紧张。
如果说新中国选择亲苏反美的外交战略,意识形态起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同样,意识形态也主导了美国的对外政策。正如亨利·基辛格曾指出的,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历来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矛盾:一方面,没有一个国家“在日常外交活动中比美国更务实”;而另一方面,又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罗伯特·达尔也认为,“美利坚是一个高度注重意识形态的民族,只是作为个人,他们通常不注意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一致程度令人吃惊”。这两个人的话表明了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的影响,就像亨廷顿所说,意识形态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基础性资源。自从1946年揭开了东西方“冷战”的序幕,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抛出了对苏联和共产主义进行“遏制”的“杜鲁门主义”。他宣称,世界已分为两个敌对阵营,美国政府“决心承担无限制的责任”,来援助“自由世界”,并对“集权主义国家”发动一场全球性的、意识形态的“圣战”。于是,反共主义的意识形态支配了对华外交,先是将中国视为苏联共产主义在亚洲的附庸和仆从,后将中国归类为扩张式的极权共产主义国家,遏制“中国式极权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首要目标。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一边倒”战略的客观条件已不复存在。但是,尽管中苏分裂一直是历届美国政府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却并没有使其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相反变本加厉,致使两国间的对立不断加深。而中国则由于美国执行了“联合封锁”和“遏制中国”的极端政策,特别是经历了朝鲜战争和两次台海危机,视美国为最大的敌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理所当然地占据了中国对外战略的首要地位。面对中苏、中美关系的这种现状,1960年底、1961年初,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反帝、反修的“两条战线”和“两条统一战线”的思想,对外战略从“一边倒”转向“两条线”,既反苏又反美。
众所周知,邓小平在总结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也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孤立状态下实现现代化。战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作为主权国加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之中,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其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样说明后发展国家只要顺应世界潮流,参与世界经济事务,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自主性发展道路,其现代化一样可以获得成功。但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由于意识形态的强化,中国先是失却了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后又割断了与社会主义苏联的联系,从而也导致了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内在联系的阻隔。
3.政治化代替科学化,现代化偏离轨道
意识形态的强化不仅导致了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内在联系的阻隔,而且进一步推动了全社会的政治化。1957年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夏天,那就是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这场在当时被认为是“一场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最终导致政治化代替了现代化,现代化因而偏离了应有的轨道。
在强烈的意识形态观念主导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充满了现代化发展的各个领域。在此,我们以科学技术发展领域的政治化为例说明,即可见一斑了。
当时的判断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企图篡夺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让科学技术离开社会主义轨道”,认为“他们提出了一整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他们攻击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叫嚷‘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们提倡‘为科学而科学’,否定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神圣任务”。因此,提倡科学领域的政治挂帅、提倡党的领导,成了当时科学发展的方向问题。当时认为“自然科学和技术虽然没有阶级性,但在为谁服务和归谁所有这一点上却有着强烈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里,所谓‘为人类服务’只是骗人的鬼话;自然科学和技术不能脱离政治,而要服从政治;政治是统帅和灵魂,任何时候都是政治领导技术”。“科学工作、科学团体是不可能超阶级的,不是党去领导,就是资产阶级去领导,不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挂帅,就是资本主义的政治挂帅。”时人从历史和理论等多方面论证了,政治从来就是领导技术的,认为政治是经济的表现,它代表着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技术既然是代表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它就必然反过来领导它所服务的主人。与此同时,技术专家——技术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它只是附属于一定阶级的一个阶层,它本身的力量微不足道,它的作用是要在和阶级结合的时候,才能显示出来,因此,所谓的“工程师专政”只能是一种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幻想而已。从此,科学界弥漫着浓厚的政治氛围。
在这场科学政治化运动中,就科学技术工作者个人而言,政治方向问题表现在红与专的关系上。在科学技术的发展道路上,科学工作者不能一心只想着个人的兴趣和发展前途,否则就被指责为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科技界普遍开展了红专辩论,那种“只专不红”、“先专后红”的所谓“资产阶级道路”受到了批判,许多科学工作者都因此甚至被迫选定了“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道路。通过整风和反右运动,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机构和科学团体不能没有政治挂帅,成为“共识”。许多科学机构和科学团体都在反右派运动中,在政府挂帅下召开了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的斗争大会。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后,又都召开了向党交心的红专跃进大会,推动大家向党交心,向“红透专深”的目标迈进。
这是一场思想跃进的运动,这场思想跃进也是一场“兴无灭资”的思想革命运动;而这场思想跃进的革命,是在破个人主义,立社会主义,破保守迷信思想,立共产主义的风格中形成的。思想跃进成了科学跃进的前提和基础,也成了科学政治化的思想保证。中国的科学发展完全走到了政治化道路上来了,走到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上来了。从此,科学工作者都决心做坚定的“左派”、做红色的专家,必须“左”、必须“红”,这被认为是作为科学工作者以及科学发展的首要条件。这样,中国科学界全面地向政治化迈进:要政治挂帅、要破除迷信、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要“红透专深”。
科学技术发展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这一切本来都没错,也都是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坚持的道路。但是,一旦将这一切看成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政治斗争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道路就开始走入歧途。科学政治化过程从此完成。
科学政治化无疑正是现代化发展走上政治化的一个缩影。现代化发展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变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现代化彻底走向歧途,偏离了正确轨道。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机遇再一次被延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