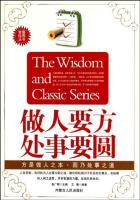一位学者这么说:“那些激进的人士,出身于文学却不谈文学,但是又以文学思维来处理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证实了这一点。以作家及具有作家习气的人士为人格代表,期望完美政治的文人政治思维,在其论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上面所表现的激情,确实能够获得感染人的力量。但其后果却未如他们的意。导致这种悖谬的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他们混淆了单纯的道义逻辑与复杂的政治逻辑、文学的描述语言与政治的分析语言、期于完满的个人美德与期于健全的公共道德的界限。因为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那些常使人写出优美著作的事物,却能导致庞大的革命。”
而可怕就在于,古有士子科举,今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英,自以为才高八斗、气贯长虹就能经天纬地,一遍一遍,忽悠无穷动……
这个世界很多人活在自我设计的圈套里,陈子昂是才高八斗,是一代文宗,是初唐四杰,只是,武则天虽然喜欢、怜惜,但只能旁观。因为政治逻辑与文学思维是两回事,多年拼杀于权力场里的武则天,早已升级修罗界——如果尼姑庵里,她自恃魅力无敌幻想李治能飞蛾扑火,那现在就不用坐在这里做高高在上的皇帝,早下世投胎去了;如果后宫之内,她指望王皇后顾念旧恩,倚为靠山,那现在早被后妃们当垫脚砖用了;如果做太后之时,她幻想亲情孝义,早被权臣孽子扔在一边凉快去了……这一路拼杀,不现实,就得死。
权力场不是道德秀,谁不知道明君圣君该怎么做,谁不希望搔姿弄首做仁德之主?但是,做得到吗?说是停止告密,阻止酷吏统治,那这些眼儿鼻子恨不得吃了你的朝臣们怎么对付?一个女人家身处包围中,就不许养几条疯狗来自我保护?不惜民力开隧道攻打羌族,是威吓周边也是为了打通南路,天下大事,即使如你陈子昂所言能“w hy”(原因)了,可是“how”(具体该怎么做)?
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一篇激情洋溢文才并茂的道德说教和仁政乌托邦,如果皇帝是《侠客行》里的白自在,陈子昂估计能如愿以偿当宰相。可他面对的,是一路拼杀出来的女皇武则天,女人式的不现实幻想早在做才人时期就已沉寂,做尼姑之后更是消弭殆尽。后宫之战、朝廷之争、亲子之伤,哪一场不需要血淋淋的现实理性精神的支撑?
不现实,就得死,你吹到天上去又有什么用?问政几次之后,武则天就知不合适,这是个文学青年,跟复杂黑暗的政治不搭边,但是其才可悯,其心可怜,因此几次召见,听听遥想里的乌托邦,意淫一下共产主义式的大同世界,如此而已。
女性幻觉思维对付职场,文人文学逻辑对待国事,都是一样的精神可嘉、滑稽可笑。当下既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忽悠受害女名单,古代也可以列一个长长的文人失败史:陶渊明、杜甫、柳宗元、刘禹锡、苏东坡……太多太多了,真实世界里,理想与现实,永远一墙之隔却天人永隔,文化过多则容易迷失于理想而消化不良。有人这么玩笑,打工仔会比学者,更务实。
骆宾王,已矣。
人才“女人”
陈子昂的理想,另外一个人帮他实现了,一个女人——上官婉儿。这个女人的祖父,正是当年做了李治与武则天夫妻博弈牺牲品的上官仪,得罪武则天后被杀,孙女婉儿与母亲郑氏被配入后宫掖庭。一开始,是身份卑贱的罪臣贱籍,在后宫成长到14岁的时候,因才华被武则天赏识,消除贱籍,命掌管宫中诏命。她的一生:才女、文人、宰相、仇敌、李唐、武氏、宫斗、政变,是个抛物线式的怪圈。
本来跟这位女皇是仇深似海,后宫14年里,母亲郑氏时时陪在身边,即使入宫之时年幼无知,满门血案怎能不记。这许多年以来,很难想象在这位天赋奇才的少女心里,有多少自卑的压抑与仇恨,有多少挣脱命运牢笼的不甘与愤懑。
而这许许多多的幻想与仇怨,在见到那个人的时刻,变成了种种错愕的心机。据说武则天当场命题,让其依题着文,她文不加点,一气呵成,而且文采飞扬,让人叹服——这么多年的等待,她怎么肯?
年少轻狂,仇深似海,却屈意媚主,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也许本来是一场处心积虑的复仇谋杀,而正史里隐隐绰绰记载,奉命掌管诏书不久,忤旨当死,但是武则天怜惜其才,并没有杀她,只是黥其面尔。短短几个字背后,又掩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变故?
她是个文人,后来劝谏中宗设置文学馆也罢,搞文学活动文学沙龙也罢,都在表明这是一文学青年、文学女青年,有才气,有骨气,有恨气,却被留在仇敌的身边。我们可以想象,见面之时的偶露峥嵘,必是拼死报家仇的小孩心性,不久以后的那次忤旨,则是一次复仇失败的借口,一个总比谋反更可宽赦的借口。
因为武则天不想杀她。
她的家族已经被自己灭掉,无依无靠,不过母女相依为命,很难再跟任何政治集团相牵连,并且女孩如此年轻,为奴多年,居然学得满腹经纶,生命激荡,恩怨分明,不正是自强不息的武才人再版吗?
天下茫茫,知音难求,大位之上,才知原来“寡人”——周围人怕她敬她恭维她;亲族们早已老鼠见猫,不会跟她说几句真心话;男宠冯小宝识字不多,也不过是让人开怀的玩具;大臣们是外廷人,朝廷利益复杂难测,没必要为拉个家常话就去引起党争若干。而这个能表露自己真心的倔强女孩,却突然让她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安全感与轻松感。
常年穿梭在男人的世界里,无论是治理天下、制定政策、颁布诏令,每次望向自己的眼睛里含着什么,武则天很清楚;宰相那么多,朝臣那么多,几十个几百个,他们在想什么,武则天也很清楚。有时候,自己那灵机一动的乍现,有时候,那女性直觉里的创新,有时候,那神来之笔的动作,有时候,那谋定后动的决断,都能在那些惊讶而不知所措甚至带有鄙视的眼睛里,找到无法沟通的明证。
可是婉儿不同,她们是一类人,虽然武则天在修罗界,婉儿还在人间混,但是底质材料基本一致,她们都是,站在中间,看世界。
武则天,太寂寞,她太需要一个帮手来理解和协调一个女人的武周天下。
婉儿正是最合适的那个“人才”,同时,多年的相依为命,主仆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奇异的羁绊。一如《宫女谈往录》里那位伺候慈禧的“荣丫头”,在18岁被老太后指婚太监后,一直守着这份承诺,即使太监丈夫在她30岁时已病死,依然矢志不另嫁而终老……
我们看婉儿的后半生,武则天去世时,她已经年近40,嫁给中宗李显做昭容,专掌起草诏令。奔走于韦后、武三思、太平公主与相王李旦等权贵势力之间,依靠韦后、武三思贬杀了张柬之、桓彦范、敬晖、袁恕己等逼迫武则天退位的功臣。因为诏书里经常推崇武氏而排抑皇家,惹怒太子李重俊。景龙元年(707)七月,太子发动政变,发左御林军及千骑三百余人,一路扑杀武三思与其亲党十余人,又统兵三百余,搜杀上官婉儿。婉儿急中生智,跑到中宗和韦后处挑唆:“观太子之意,是先杀婉儿,然后再依次捕弑皇后和陛下。”中宗情急之下带着韦后、婉儿和安乐公主登上玄武门躲避,并令右羽林逼退太子军,于是太子兵败。
不久,婉儿怂恿中宗设立修文馆,召天下才子赋诗唱和,大臣所作之诗,皇帝让婉儿来进行评定,名列第一者,常赏赐金爵……后来允许她在宫外置所,于是跟武家所属的大臣崔湜私通,积蓄男宠,丑名四逸。
中宗死后,韦后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太平公主与侄子李隆基联合发动政变,诛杀韦后及其党羽,婉儿在军乱中亦被杀。玄宗李隆基登位之后,追念其才,下令收集诗文而辑成20卷。宰相张说作序:“古者有女史记功书过,复有女尚书决事言阀,昭容两朝兼美,一日万机,顾问不遗,应接如意,虽汉称班媛,晋誉左媪,文章之道不殊,辅佐之功则异。”
她的一生,太多人注重其才(诗文成集),太多人注重其貌(如额头毁容而雕成梅花事件),太多人注重其淫荡(私通大臣),太多人注重其地位(女皇秘书的宰相地位)。或许不经意间,也有人注意到那人性的缝隙,说她不过是一小小女子,在后宫与政治险恶斗争里求生而已。但是,是否有人想过,在那私通大臣、举办文学沙龙、积蓄男宠、抑李扬武的背后,哪一条,哪一个,不倒映着武则天的影子?
本是李家人,与武家血海深仇,只是年月太久了,跟那个天龙之表的女人走得太久,太久了。一生里,太多夜深人静处,跟男人们的处政方式与思维天下,斗智斗勇,那个女人的艰难、那个女人的焦虑、那个女人的锋利与那个女人的自卑,她走得太近,看得太清,懂得太多。几十年,一生,太久。
她忘记了自己本是上官家的婉儿,她只记得,自己是武则天的仆人、秘书、助手和同伴,这一辈子的使命,就是贯彻那个女人的旨意,让那个女人的天下,千秋万代……神龙政变之后,女皇驾崩之时,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女人的时代已经逝去,只有她,还活在梦里,活在武则天的影子里,不觉得,也不想觉得。
还记得吗,韦后想要女主天下的那些祥瑞,不正是女皇曾经用过的权谋?
还记得吗,那些诗歌比赛,那些文学沙龙,不正是女皇晚年欢乐的艺术圣地?
还记得吗,那些男宠,不正是女皇曾经拥有过的谄媚与安慰?
还记得吗……
婉儿的一生,有些梦,太久。
人才“大臣”
在武则天的眼里,婉儿恐怕是最如意的臣下,她懂她,并且崇拜,既没有陈子昂们的“我是天下奇才,你得供着我”的文人得瑟,又没有谄媚权臣的满腹狡诈,一心一意,一生一世,武则天,真的很喜欢。但治理天下显然不能只有婉儿,偌大的一个帝国,还需要另外一种人。
大臣。
《反经》上说大臣的含义是“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而能做到这些的,却是不可能剔除正统观念的那些人——那些贵族和正直士子。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转折期,是魏晋南北朝的贵族统治转入官僚的分裂期,科举刚刚产生但并不普遍也不占核心,朝政由贵族把持的机会相对更多。而在教育体系里,家教、家风、家学传统依然占有优势,这些优势在换代时期是不会轻易退却的。一个贵族出身的子弟也许会纨绔不堪,烂泥扶不上墙,但是更也许,在精英教育与高等文化熏陶下,在政治觉悟与韬略之计的传承下,比那些小门小户的寒族士子,更为出类拔萃。
可惜的是,武则天治国需要的,正是这种人。
退一万步说,就是她杀光了所有贵族,那些刚刚上来的庶族地主们也无法帮她运转起整个帝国,因为他们如果是“正直之士”就很难根除传统理念。门户之见、性别之偏,所有的转轨都需要一段时间,而历史只给机会没给时间,太短,太少,太仓促。她没办法,这些人不能不用,但是,也正是这些人在传承了优秀资源的同时更传承了正统理念——他们在告诉她,自己是一个来路不正的主子,那么“how”?
永昌元年(689)八月的一天,炎炎烈日炙烤着神都洛阳的街道,一名黄衣使者一边急马奔驰,一边焦急地高喊:“太后有旨,刀下留人!”听到这句话,人人皆有喜色,传至刑场,更是一片欢呼,不仅犯人手舞足蹈,叩谢天恩,连刽子手也提刀念佛。而只有一人十分冷静,只见他身穿白色囚衣而一尘不染,神色淡定,微微而笑,仿佛是出行重大而高贵的祭祀礼仪而非上刑场砍头,待到旁人给他解下刑枷,顺手弹了弹身上的灰尘,才徐徐跪倒谢恩……
他叫魏元忠,庶族出身,军事入仕,高宗李治时期曾经就吐蕃问题上过书,扬州平叛时又为武则天立下奇功。圣历二年(699)任相后,多次被武则天任命为大总管,对付吐蕃和突厥等外患。史评成绩:“元忠在军,惟持重自守,竟无所克获,然亦未尝败失。”就这么一人,《旧唐书》说他“坐弃市流窜者三”,《御史台记》中说他前后“坐弃市流窜者四”,政治仕途风起云涌,柳暗花明一村又一村。
长寿元年(692),被来俊臣诬告,判死刑,负责推案的是他的部下酷吏侯思止。因为魏元忠坚决不认罪,侯思止一气之下把魏元忠头朝下吊了起来。魏元忠依然不屈服,说:“你要我的头现在就可以割走,何必要我承认谋反。”后来因为狄仁杰的智慧,此祸得免。五年之后,再次启用。有次宴会,武则天笑问:“你怎么老被人诬告?”魏元忠回答:“臣是一只鹿,罗织之徒要用这只鹿熬肉汤,我又怎么能避免呢?”
武则天真的不知吗?
狄仁杰,一代名臣,贵族之后,科举入仕,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等地方官,因为政绩突出,受到女皇赏识,天授二年(691)入相,被任命为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不久,被武承嗣勾结来俊臣诬告下狱,为了求活,当来俊臣推按是否谋反时,狄仁杰立刻承认“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因为有一条法令说:“一问即承反者例得减死。”来俊臣没想到狄仁杰这么乖巧,于是放松了警惕,没有用刑而只是将其收监,待日行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