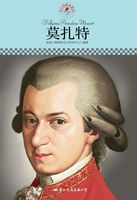每个星期听一次昆曲,周末我们一定去看戏,听昆曲,假如有特别好的戏,就不听昆曲,就去看戏。那时候叫汇演,各地的好戏都到北京来演出,戏曲界我有很多朋友,有很好的戏票早给我准备了,所以星期六晚上去看戏,不仅我和我老伴,我妈妈也喜欢看戏,一块去。有时候看戏看到十二点以后才回来,这也是很愉快的事情。
那时候北京几个重要的昆曲演员常到我们家来,南京、杭州的重要演员也到我们家来,我们都跟他们做朋友。张允和写了好些关于昆曲的文章,人家很喜欢看,台湾对昆曲热心的人很多,也把她的文章拿到台湾发表。
俞平伯跟我们家交情好得很。我们家有很多俞平伯写的东西,老伴去世以后,我现在不挂这些东西了,我孙女带走了,她也很会玩。俞平伯很有学问,家学渊源,三代都很有学问。
俞平伯的风度真是没有话说,这是中国传统的仁人君子,高尚学者的风度,待人好极了。他对《红楼梦》的观点跟共产主义当然是谈不上的。所以批判俞平伯是没有用的,看起来是笑话,古代的文学为共产主义服务,怎么可能呢?
俞平伯在曲会里常常讲他的研究成果,像大学里上课一样,非常深入,那真是有水平!
曲会里有几个家庭妇女,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这都是薪金阶级,维持家庭都没有问题的。后来薪金阶级没有了,变成工人阶级。夫妇两人不得不工作,不然养不起家庭。在我们的时代,高级知识分子妇女不一定做工作,因为那时候家庭经济由丈夫负责,家里的太太都是学问很好的。那时,中、英、美都是这样的。
张允和在曲会里没有收入,不仅没有收入,我们还贴钱。北京市文化局每个月贴给这个曲会二百五十块钱做零用,其他的由各方捐钱。这种民间机构从明清就有了,士大夫在一起雅集。这个昆曲民间机构等于京剧的票房,都是士大夫有钱、有闲、高尚的娱乐。曲会在现在王府井商务印书馆的地方,里面还有小的演出剧场,中央很多有名的人都来看。周总理常常来看戏。康生也来,康生很懂昆曲的。
沈从文也来过,但不是很多,沈从文对昆曲的兴趣没有我们大。他搞另外一套,忙得不得了。张兆和也懂昆曲,来得不多。
我对昆曲的爱好从中学开始,我们校长童伯章对昆曲很有研究。童伯章在中学就教我们昆曲的文学,昆曲的音乐,我已经有印象。我始终对昆曲不是那么喜欢,我喜欢西洋音乐,我年轻时也学小提琴。听西洋音乐是张允和跟了我走,听昆曲是我跟了她走。我觉得中国音乐、西洋音乐都有好的地方。
二十五宁夏五七干校
“文化大革命”来了。忽然报上登出来,要反对教授,反对工程师,反响很大,国际反响也很大。几天后,口气改了,不讲反对教授和工程师,叫反对“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的当然可以反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头一个星期的口号跟第二个星期很不一样,头一个星期的口号出来,反响太坏,第二个星期口号就改了,内容没有改。
“文改会”是一个小机构,比部小,直属国务院的,开头轰轰烈烈的运动,我们等于是处于保护的状态。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开头大家都不了解。开头没有江青,后来江青变成“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人物。开头没有“四人帮”,后来才有“四人帮”。
“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力之大,恐怕毛泽东自己也没有估计到。人变得没有理智,没有法律,许多机构都停下来了。全国破坏的价值无法计算,“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一直到最后看了内部材料,我大吃一惊。
在“文革”中,张家当中影响最大的是大弟弟。大弟弟在贵州大学,贵州比较边远,更野蛮一点,所以大弟弟劳动过度,在“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就死了。
“文化大革命”把我们越来越贬低,开始说我们是“反动学术权威”,后来坏的帽子越来越多,到后来是“现行反革命”,到最后整个机构下放宁夏平罗五七干校。一九六九年冬天去,一九七二年春天回来。
岳飞说“踏破贺兰山阙”,就在平罗。因为中国的山多是东西向的,那地方的山是南北向,平罗是一个缺口。风吹过来,八级是很普通的,很苦的地方。我们去了才知道,有二十几个站,一个站有五千个劳改犯。我们去的五七干校是由两个站改造给我们的。实际上我们是优待的劳改犯,是周总理特别关照,可以拉电线,有电灯,给我们打一口井,我们运气好,打的水可以洗澡。在干校,可以通信,可是慢得不得了,一封信要大半个月才能收到。五七干校实际是劳改营,我们这种人是社会不需的人,是“社会的渣滓”。一到那里,大家要宣誓:永远不回去了!后来林彪死了,就把我们都送回来了。这是按照苏联的办法,苏联也把老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地主赶到北极圈以外。
我们去劳动改造,不许带书。在那里种稻子,缺少水,怎么种稻子呢?本地人劳苦得不得了,愚昧得不得了,什么都不知道,真可怜!一望二十里路,没有人烟,可是条件很好,有铁路,有运河,交通方便。天然条件很好,没有利用。
在宁夏时,我和林汉达——他原来是教育部副部长——两个人年纪比较大,第一年要下田,第二年叫我们去看高粱地,看看有没有人来偷,我们在山冈上望去,至少可以看一二十里路,没有人的。每天早上去看高粱,太阳下山前回来,比较轻松,我们就聊天。林汉达是研究语文用语,他主张词汇要口语化,把人家不容易懂的,改为容易懂的。我们谈到寡妇和遗孀的分别:穷人死了,老婆叫寡妇;有钱人、名人死了,老婆叫遗孀。林汉达后来生病死了。
我去看白菜,要服从造反派的领导,宁夏没有白菜,都是卡车运来的。白菜非常好,容易烂,要赶快交给厨房吃。好的都不吃,吃的都是坏的。我发现一个白菜原理:坏的才吃,好的不吃;不坏不吃,坏完吃完。从头到尾吃的都是坏白菜。
我们见到大雁下大便,这是一个有趣味的事情。古书上说,鸿雁传书。北京、南京的天空原来都有大雁飞来飞去,后来大烟囱冒烟,大雁害怕,就不飞了。现在大雁在中国西部宁夏一带,从西伯利亚飞到印度洋。大雁飞来的时候,天空中几天几夜,数也数不清。林彪死了,通知我们明天清早五点钟要开会,每人带一个小凳子,坐在空地上面,开会没有大会堂的。我一看天气好,到中午一定很热,开会都是大半天,我就戴了一个大草帽。九十点钟的时候,大雁来了,不得了,铺天盖地,到了头上,大雁纪律性好得不得了,领头大雁一声怪叫,大雁们下大便。我戴了大帽子,身上只有一点点大便,许多人身上都是大便,洗都不好洗。那天戴帽子的人不多,因为清早有一点点云,所以很多人都没有戴帽子。他们说,这种情况大概一万年才遇到一次。这是一生当中非常有趣的遭遇。
到五七干校有一个好处,我原来有失眠症,到了干校体力劳动,不用脑子,失眠症好了。回来以后,失眠症没有了,坏事情变成好事情。
“文化大革命”时,张允和是家庭妇女,不是重要对象,所以受的冲击不是挺大。我也是很受优待,我们几个同事回来以后被打得一塌糊涂,我没有被打。造反派告诉我,我查你是不是里通外国,结果你没有里通外国,所以没有打你。张允和带小孙女住在北京的亲戚朋友家里,家里不能住。东西都搞光了,她受不了,这种地方都表现出她比较娇嫩。
周小平和儿媳妇都是中国科学院的,下放湖北潜江,这些都是苦地方,是关劳改犯的地方。张允和和孙女在北京,儿子在潜江,我在宁夏,一家人在三个地方。连养孩子的钱都没有,我的老伴在亲戚那儿借钱过日子。
抄家是一家家都要抄的。到我们家来抄家,还算文明,拿去了几本书,没有什么损失。可是后来我们都不住在家里,造反派就把我们家的门打开,东西都搞光了,其他的东西都不稀奇,大量的照片搞光了,我们小时候的照片原来都有,现在全没有了。等到我们回来,我们的房里都住着不认识的人,回来再安排给我们住的地方。
我从干校回来,很有趣味,把高级知识分子都集合到国务院训话,说:你们这些人都是“社会的渣滓”,没有用处的。我们是人道主义,所以给你们吃一口饭,都回去吧,不要乱说乱动。没有工作,都回家了。
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工资扣掉了大部分,我最少的时候只有三十五块钱一个月,付房租都不够,就借钱来过日子。回来以后,很优待,扣的钱还给我们,用这个钱把债还掉。
沈从文一家是文学系统,他自杀是觉得恐慌。“文化大革命”时好多文学家自杀了,像老舍。后来沈从文到了故宫当解说员,不算文学家。
二十六“专家专家,专门在家”
一九七二年从宁夏回来,有几年什么事情也没有,我就安安静静做研究工作,那几年研究的成果最多。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的书为什么多呢?因为这段时间把以前没有弄好的研究,都弄好了。文字改革在世界上已经变成一门科学,中国人又不知道,我可以接触到一些外国的东西,稍为知道。
我们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新加坡是一九六五年成立。新加坡也是有意思,不是自己要求独立,想参加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不要它,把它赶出来的。李光耀大哭,说:“我们又小又穷,要成立一个国家,怎么办?”这个事情在中国完全新闻封锁,我们都不知道。我是八十年代在美国张充和家里,看到一点旧杂志才知道的。为什么要把新加坡赶出来,道理很简单:一、新加坡大部分都是华人,如果参加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华人就可能超过百分之五十,马来人就不愿意;二、新加坡的华人共产主义思想弥漫,李光耀原来就是老共产党。马来西亚讨厌中国人,把他们赶出来,新加坡只好独立。这跟台湾刚刚相反,台湾要独立。天下的事情都是古里古怪。
新加坡独立以后,要研究怎么建国,向美国专家、英国专家、日本专家请教。派一个调查团到中国来调查了三个月,新加坡能不能跟中国大陆走共产主义道路。调查的结果是新加坡不能走这条道路。
可是新加坡研究政策要跟哪个国家走,语文政策基本上跟中国走。新加坡的语文政策搞得很好,全国通用的语言是英语,华人要用华语,马来人要用马来语,印度人要用印度语,三大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华人的语言讲方言还是讲国语呢?可是不能用“国语”两个字,因为新加坡的国语是马来语,也不能用“普通话”,这三个字在新加坡不好理解,就用“华语”,这在华人里面都能接受的。华语的标准完全按照大陆,这是他们聪明的地方,文字也用简化字,拼音也跟着大陆用拼音。新加坡什么都跟台湾,就是拼音、普通话、简化字跟大陆。台湾很不高兴。我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台湾人质问新加坡人:“你们是‘事大主义’。”就是跟着大国走,新加坡人说:“我们不是‘事大主义’,我们是为了研究、教学方便。”
新加坡第一个用简化字、拼音方案,之后影响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开头是穷得不得了,什么都没有,可是走国际道路,什么东西都采纳国际专家的意见,结果十年工夫就变成一个好的榜样。我去了两次,第一次是新加坡华语协会邀请的,第二次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邀请的。第一次主要让我讲中国的拼音方案、简化字、文改政策;第二次是讲东亚国际语文问题,主要是英文地位。新加坡现在变成东南亚的明星,东南亚的语文中心、医疗中心、金融中心、航空中心在新加坡。原来大家讨厌的地方,不要它了,结果后来大家都喜欢它。马来西亚要吞掉它,可是它现在不要再参加马来西亚。到今天,新加坡的国际机场比我们北京的国际机场要好多了。
香港跟新加坡相反,跟着台湾走,到今天还是不大用拼音。台湾在我们没有提出简化方案时,蒋介石就提倡简化字,两次公开提倡。蒋介石在南京时就提倡简化字,南京是最早公布简化字方案的,可是公布出来,人家反对很厉害,第二年就取消了。蒋介石到了台湾又提倡,孙科也提倡,后来共产党搞了,他们就反对了,是这么一个变化。我认为简化问题不是党派的事情,文字改革问题不要跟政治搞在一起。现在台湾搞一个通用拼音,我看通用拼音很难搞下去。我是希望说服台湾,语言文字用科学方法来解决,跟政治脱钩。我对台湾人讲,“文改”不是共产党搞的,“文改”在清朝末年就搞了,国民党对“文改”很热心的,北洋政府也很热心的。
一九七六年,实际上我还没有恢复工作。毛泽东死了,邓小平上台,政策是改了,可是许多坏事还存在,一时改不了。一九七七年开始改,一直改到一九八四年稍为像一点样子,比较上轨道要到一九八七年。开头也没有恢复办公,把社会搞得一塌糊涂要转过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差不多十年工夫,拨乱反正,大概到一九八七年以后,才上轨道,这些是很慢的。我名义上是恢复了,但是没有上班,在家里面做研究工作。我的生活很简单,研究的内容不简单,表面上安安静静。所以,造反派批评我们:“专家专家,专门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