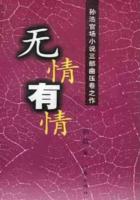一九八八年以后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把我的研究工作一点一点搞一个段落;第二个阶段就是随便看东西,写杂文。我是做学术工作的,不搞文学,为什么不搞文学?不是我不喜欢,而是我的精力有限。在学术上,对语言文字学方面可以说是一个空白,我就占领这个空白,可以做许多事情。为什么说是空白呢?语言文字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学问,一向传统很深,要把旧的书看一遍,也要看好多年,大学里一向把音韵学、训诂学作为重点的课程。清华大学解放前有名的大学问家都叫国学大师,王国维等人都是研究从前的东西,成果很大。可是有一个传统很糟糕,就是研究中国,研究古代,不研究中国以外的东西,不研究现代。没有外国,那范围就很小了,世界那么大,一个国家再大也只是一个国家。研究古代而不研究现代,现代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而且有实用的,研究古代当然很有价值,但是跟实用相差很多。王国维的创造了不起,可是有哪几条实用的?
我到了“文改会”,工作需要,我就在空白区里做了许多工作,很容易见效。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把“文改运动”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我在北京大学开汉字改革概论课,就是把原来人家没有系统的知识变得系统化,言之有据,把有系统的知识变成一门学问。第二件事情,我提倡现代汉字学,现代汉字许多问题很少有人研究,大学生到中文系都是研究古代,可是现在有用处的东西不研究不行。
胡适之了不起的,他到中国公学当校长,找沈从文去教白话文学,为什么呢?胡适之说:“我们提倡白话文很久,大学里面连课程都没有。笑话!”大学里谈到的文学都是古代的,没有现代的。中国提倡白话文以后,许多人认为小说上成就最大的是沈从文,诗上成就最大的是徐志摩。不能从政治角度来批评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当然可以否定他们。可是文学史不是那么看的。
同样地,在语言学、文字学方面,赵元任搞了现代,是了不起的,可是他搞的现代主要是方言,跟现代有实用的问题真正挂钩的很少。我就在这方面下功夫,一做这工作就立刻遇到许多问题,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把这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第二是现代汉字学,这是成功的。第三是比较文字学,还没有成功,清华大学有一个研究小组,可是要成为一个课程,现在还没有条件。讲起来道理很简单,历史系只有中国历史,没有外国历史,行不行呢?只有古代史,没有现代史,行不行呢?为什么语言学、文字学老是古代的,老是中国的,没有现代的,没有外国的?这样来讲,很容易了解,可是到今天要改还是不容易,现在多少大学有现代汉字学我还不知道。他们说,至少有十几个大学,当中跟我有密切联系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文字改革的意义很重要。中国的传统与外国传统相似,有文字之“神”,“神”是高傲的。古代人认为,文字是上帝给的,是不能改变的。这个观念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外国与中国一样,文字、语言都是随着时代在变的。譬如今天在语言方面,有了电脑,很多新的名词也随之而来。中国最早的一次大的文字改变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书同文”,当时七国使用不同的文字,统一以后文字不同带来很多不便,办公、行政、教育都不方便,因此秦始皇要统一文字。可见,早在秦始皇时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就开始了。后来,历代都在改变,汉朝改变也很大,秦始皇用小篆作为主要的文字,到了汉朝就开始用隶书,再后来又变成楷书。虽然古代传说文字是由上帝给的,不能改变的,但实际上文字是不断在改变的。
到了清朝末年,受到西洋的影响,感到中国的文字太困难,对文化的普及提高不方便。后来随着与外国往来的频繁,就发现中国的文字与国外的往来不方便。所以,从清朝末年,就产生了“文字改革运动”,写的方面就是“语文现代化运动”。语文现代化,就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要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这些工作中,我觉得近年来做得很好。解放后,在五十年代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现代年轻人都学了。这个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处很大。首先,使得中国的小孩子、文盲能够利用这个工具认字,走进中国的文化宝库;其次,方便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汉语拼音一方面是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看似是个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如,我们中国人的名片上印着拼音,这样不懂“方块字”的外国人也可以认得,可以叫出。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到今天,都处于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之中,现代化改革,一方面是语言文字的改变。
九十年代以来,教育部领导的普及普通话工作做得很好。设想,一个大的国家,广东人讲粤语,上海人讲上海话,香港人到北京旅游还要找翻译,国人在本国找翻译岂不是笑料?其实外国原来也如此,我三十年代到日本东京读书,原来以为我学的东京日语,可以走遍日本,但是发现连不远的京都的语言就完全不一样。可是日本能够推广日语,日本人称之为“国语”,以东京话为基准,到了现在日本人之间讲话没有一点障碍了。西洋国家的共同语言普及大概三百年之前就实现了,日本大概一百多年之间实现了,我们中国还正在实现之中。前两年,有人在北京做抽样调查,北京人能讲普通话的大概占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的不一定能讲,所以我们是在逐步改进。一个国家要做到现代化,需要达到很多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讲话大家都懂,如果讲话都不懂,怎么能算现代化国家?我们这一指标虽然还没有达到,但是逐步在接近之中。我个人的感觉,九十年代我们的语言现代化工作发展得较快,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文字改革或者说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不能没有,人不能不讲话,人不能不认字啊!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普通话要制定一个标准,要做教育工作,我们的文字特别困难,我们要使它变得方便一点,太困难的地方要改掉一点。当然,基本上要依照原来的,不能改动太多,逐步的改动是可能的。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八十五岁以后,我看一些专业以外的书,主要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化学,另外一方面是历史学。为什么看文化学呢?这是偶然的,《光明日报》开一个栏目,要振兴中华文化,要找一百个人写文章,差不多每个星期一次,我开头不感兴趣,后来人家说请你写,就给他们写吧。我说:“他们有些人的写法我不同意的。”他说:“没有关系的,他讲他的,你讲你的。”好,我就给他们写,写了一篇,他们觉得感兴趣,这样就把研究文化学作为一个玩意儿,不作规规矩矩的研究,就看了很多中国和外国的文化学的书,都是零零星星,后来上海编了一本《周有光文化论稿》。对文化学我是外行,他们觉得我的看法还是跟人家不一样,有参考价值,这是业余的。我现在写的文章,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有的在内地,有的在香港。因为年纪大了,没有事情,别人来看我,说怕耽误我的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不值钱,我现在是“无业游民”。
《百岁新稿》是我九十岁到一百岁之间写的,其中,有的文章是我看了很多书后写的,有的文章是杂志邀请我写的。老来读书,我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难。苏联是新中国的原型,中国改革开放,略作修正,未脱窠臼。
人家一看《苏联历史札记》,说:“这篇文章我们不敢登。”我说:“为什么不敢登呢?这都是公开的苏联的材料嘛。”他们说:“你把它结合起来就变成集束炸弹。”苏联垮台是世界历史大事,我也很关注这个事情,就经常看一些相关的中外文书籍。看了至少有十六七种,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一次跟朋友聊苏联的事情,有朋友邀请我写一篇关于苏联的文章,介绍苏联的情况。苏联一共几十年的历史,所以介绍苏联的书籍都是长篇大论,他希望我这篇文章不超过一万字。我就把几十年的历史压缩,把最基本的东西写出来,没有添加评论。《苏联历史札记》里完全讲的是事实,比如,我把苏联的几个领导人“排排队”,讲讲他们执政和下台的情况。苏联领导人不是死了下台就是政变下台,这就说明苏联有问题了。国家的领导人终身制是不行的。老了,没有精力,并且任职时间一长就有种种问题。因为政变下台,这个制度也是封建社会皇帝的做法。当然,我没有评论,我是写出来让别人去评论。在书中,我就写了几句叙述性的话,看的人自然明白。我用诸如此类的写法,在很短的文章里,实际上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
《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也是别人邀请我用很短的文章进行探讨。为什么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却超过了两千年历史的国家?为什么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却超过了英国?许多人问,拉丁美洲的开放比美国早一百年,那为什么拉丁美洲到今天还远远不及美国?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需要研究。我不是简单地提出答案,我是提供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从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发展得“快而好”。有一个美国教授,看到了我这篇文章发出感慨:“我一辈子在美国都没有了解美国,我看了你的文章才了解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