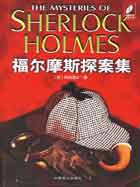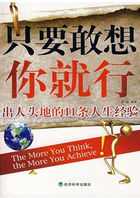何黑子引着叶福清走进了旺兴村,一眼就看到了那棵老榆树。这棵榆树足有五百年树龄,树身苍黑,树冠庞大,走近大树下的碾盘,叶福清围着老榆树转了一圈儿,叶福清想,登高这个畜生卖了府绸铺子,要是去赌去嫖,当老人的心里还好受些。可是,他跑到旺兴来办什么学校,教一群泥腿子识字,又杀猪又唱戏,这不是存心要把老子气死吗?叶福清用力捶打着胸脯,恨不得变成老虎,把登高活活地吞了。
叶福清问过了,登高办学校的地方,原来是旺兴吴财主的老宅,窝风向阳,坐北朝南,风水不坏,门左是一条涓涓清溪,右边则是一道隐约可见的山冈。左青龙,右白虎,这种宅子日后只怕要出达官贵人哩。却不想,吴财主百密一疏,竟然与卢大头瓜葛上了,好好一座宅子,成了匪财。原想那卢大头也不敢来住,偏偏卢大头中意登高,这座宅子便成了登高败家的家什儿。叶福清本不想来,可是何黑子一天几次汇报旺兴的动静:大少爷在旺兴请戏班子了,大少爷在旺兴杀猪了,大少爷在旺兴自个儿贴钱给泥腿子办学校了,和尚到旺兴了,小姐和丫环也去了……叶福清越听越气,邪火几乎要掀开天灵盖。他实在忍不住了,叫上何黑子,连车也不套,直奔旺兴。
叶福清一脚踢开了登高学校的大门,把门里扫地的和尚吓了一跳。知秋也从一间偏屋里走出来,愣怔地望着他。登高一脸笑意,从正屋中出来,可能是想说什么,见到他这个当爹的,也僵住笑,连个招呼都忘了打。桂花见到叶福清,身子一抖,连笑也不会笑了。叶福清决定就从桂花下手,先给这个下人来个下马威。
叶福清说,桂花,你不在家里侍候太太,到这儿来干什么?桂花说,是……小姐……叶福清一板脸,呵斥道,小姐就能由着性子来吗?小姐胡闹,你一个下人也跟着胡闹?叶福清的威严一向都在语气当中,几句话,把桂花的理智都打飞了。桂花红着脸,傻站着,再也答不上话来。
知秋看不过眼,横在桂花面前说,爹,你有气就骂我吧,这和桂花无关。叶福清还在责骂桂花,该死的奴才,你在这里玩的挺热闹啊,又是唱戏又是杀猪,看回家我怎么收拾你!不打断你的腿,我这个老爷就白当了。知秋说,爹,要打你就打我吧,买猪和唱戏,都是我的主意。叶福清高高地扬起手,恼怒地吼道,你就不该打吗?登高上前一步,挡在知秋面前说,爹,知秋没错,你要打,就打我。叶福清这才正眼瞪着登高说,我哪里敢打你?登高说,你是我爹,当然敢打我。叶福清哈哈大笑几声,阴阳怪气地说,登高,你弄错了,我哪里是你爹,分明你是我爹。你何止是我爹,你是我们叶家的活祖宗。登高吓了一跳,他定定地看了看父亲,确信父亲没疯之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惭愧地说,爹,儿子不孝,你想打就下力打吧。
叶福清后退几步,忽然打了自己几个耳光,他仰着头,对着苍天大吼,老天爷呀,我叶福清哪辈子作了孽,叶家的祖业真的要败在我手上了!天哪,你睁睁眼吧。叶福清胸口一热,身子一拱,一口鲜血喷出嘴边。知秋尖叫一声,扑上去抱住叶福清。知秋哭道,爹,你别吓我呀,你别吓我呀,爹,你怎么啦?桂花也上前扶着叶福清的胳膊,急得泪水在眼中直转。
登高慌忙打发和尚到石桥去请郎中。等郎中的工夫,登高就守在父亲的身边,神色焦急。知秋抽空把登高拉到一旁,低声问,大哥,这学校还办吗?爹这样,是不是该缓缓?登高先是低头沉思,接下来又高高地扬起头,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可以看出,登高的心里像倒进了一盆炭火,灼得他坐卧不安。良久,登高低沉地说,妹子,学校无论如何不能停,要办下去,一定要办到底。知秋忧心地说,可是,爹这样,我们怎么忍心……登高说,知秋,家国难两全,忠孝也难两全。为了革命事业,我只能这么选择了。爹有一天一定会宽恕我的。知秋摇了摇头,泪水汩汩地流下来。知秋带着哭腔说,恐怕难哩。
晌午时,郎中来了。把了脉,看了舌苔,开了方子。登高让人到石桥去抓了药,知秋亲自带着桂花把药熬上。就在这时,门外一阵喧嚷,登高未及出门,见卢大头一身青衣,已经进了门。登高赶紧把卢大头让进堂屋,卢大头闻到药味儿,便问,叶少爷,什么人病了?登高说,家父略感风寒,不碍事的。卢大头一怔,说令尊在吗?我去看看。
在正房堂屋,卢大头见到了叶福清。卢大头施礼说,叶前辈,晚生有礼了。叶福清虽然心痛难忍,但来了生人,还是硬撑着,挤出一丝笑容来,说,恕老夫有病在身,不能还礼,壮士请坐。
卢大头暗叹叶福清有眼力,他只看一眼,就知道这人是文人还是武夫。这眼力没有几十年的修炼,是不可能有的。只凭这一点,卢大头就对叶福清另眼相看。卢大头说,老前辈,服药了没有?叶福清长叹一声,没有回答。卢大头诚恳地说,我和令郎是生死之交,有用得我卢某人的地方,请前辈尽管开口。叶福清有气无力地说,叶某谢了。卢大头拱手说,前辈,晚生告退。叶福清扬了一下手,说,恕不能送。
卢大头走到门口,叶福清忽然叫住了他。叶福清说,壮士,你刚才说你贵姓?是姓卢吗?卢大头转过身来,望着叶福清说,正是。叶福清惊异地看着卢大头,半晌才说,莫非你是……卢大头矜持地一笑说,正是在下。叶福清不禁睁大眼睛盯着卢大头,用力吸了几口气,才说,卢壮士,我们叶家世代良善,从来未曾通匪,也担不起通匪的罪名,你大人大量,放开登高吧。卢壮士,你应该知道,若是事机不密,朝廷一定会追究责任,难道你还想让登高上山入伙吗?卢大头望着叶福清,郑重地点头说,老前辈放心,我就是上法场,也不会牵连大少爷,我虽为匪人,但义气二字,还是懂的。叶福清挣起身子,感激地说,老夫谢了。
卢大头走出正房堂屋,来到登高的住处。卢大头看看登高,半晌不语。登高给卢大头倒了茶水,问道,卢兄,你怎么来了?卢大头说,叶少爷,我想问问,青龙潭的人,能不能来识字?登高说,能,怎么不能?识字是好事,也算弃恶从善。卢大头拱手说,叶少爷,卢某欠你一个人情,来日方长,容当后报。登高一笑说,卢兄何必见外,为卢兄做事,是小弟的本分。卢大头一笑说,既如此,兄弟的人都在村外,让他们进来啦?登高说,快请。
卢大头从怀里掏出一个号炮,走到灶前用炭火点燃,一声震耳欲聋的爆响,传出数里开外。很快,一伙青壮年男人快步走进村子,都集中在学校的门外。卢大头出去点了人数,然后让他们在门外拜了老师。登高受了师礼,便把一干人让进院内。
吃过晌饭,和尚忽然进来对登高说,叶老爷要走,留也留不住。登高赶紧到正房堂屋,劝说父亲暂且留下。叶福清说,得了,我可消受不起,还是回去。登高说,爹,不管怎样,先稳定一下,你这身子还弱着呢。叶福清说,登高,爹想和你单独说几句话。
登高便让知秋等人出去,自己走到叶福清身边坐下来。叶福清拉住登高的手,未及开口,先落下泪来。登高替父亲擦掉眼泪,安慰说,爹,你别上火,有话慢慢说,都是儿子不孝,惹爹生气了。叶福清睁开泪眼,声音嘶哑地说,儿呀,你卖铺子,爹心疼,可是爹能想开。那些东西虽是祖产,但随时可以再置。有些东西,一旦丢了,便再也补不回来了,懂吗?登高说,爹,你指什么?叶福清一指登高的额头,没好气地说,脑袋!
登高明白父亲所指,本能地辩解说,爹,卢大头来找我,是想让他的弟兄也识些字,我想,这是大善之举,便同意了,爹,你放心,没事儿。叶福清一瞪眼骂道,糊涂,通匪本身就是大事儿,万一被告发,就是生死官司,你是留过洋的人,难道不知其中厉害?登高啊,爹老了,爹怕打官司,爹这把老骨头,还经得起折腾吗?爹求你念在我们父子一场,你发发慈悲,放过叶家一门老小吧。
那一瞬间,登高的心痛得几乎要裂开了。爹一生不求人,现在,却要求自个儿的儿子。登高相信自己的所为没错,可是,爹错了吗?一个为国,一个为家,都符合纲常天理。作为儿子,他不孝。作为国民,他要尽责任。登高几乎要给爹跪下了,可是,心中一直有一个声音冰冷地告诫他:叶登高,你不能软弱,不能退让。国家大事,永远都是第一位,家事了了,只能牺牲和让步。登高清了清嗓子,开口说,爹,你曾经教过我一首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天儿子算是用上了。爹,为了推翻腐败透顶的大清国,儿子已经豁上这条命了。爹,月大月小赶上了,你认吧。如果日后儿子牵连到叶家老小,今个儿儿子先在这里赔罪了。
登高后退半步,铿然跪地,不等叶福清做出反应,先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叶福清闭上眼,一行老泪夺眶而出。登高以为爹会破口大骂,可是,等了一阵子,叶福清一直没睁开眼睛,登高便把知秋送进来的一碗汤药端到父亲面前,说爹,起来喝药吧。叶福清伸出手,把那碗汤药拨到地上。叶福清说,不必了,从今儿起,爹绝食,不活了。登高也流泪了,他跪爬几步,抱住父亲的一只手,涕泪涟涟地说,爹,我替天下苍生谢你了。叶福清抬起眼睛,望望登高,又望望这间陌生的屋子,艰难地说,登高,送我回家吧。我不想死在外面。记得,我死了,不进咱叶家的祖坟,我没有脸面见咱叶家的列祖列宗。你是长子,切记,不可遗忘。登高点头,说爹你放心,儿子记下了。叶福清无力地闭上眼睛,再也不肯开口了。
登高赶紧安排和尚,在旺兴找了一辆车,然后把叶福清扶到车上。叶福清执拗地拒绝和尚护送他回新生,却拉住知秋不放。登高看看时间不早了,只好动员知秋说,妹子,要不,你就辛苦一下?知秋撅着嘴说,要是爹不让我出来,那怎么办?登高说,哥保证你一定能出来,行吗?知秋才好不情愿地跟车走了。车到村口了,知秋还在高喊,哥,别忘了你的保证啊。
登高看了看身边的和尚,强烈的日光照在和尚的脸上,和尚眯着眼,傻傻地望着知秋远去的背影。和尚的眼睛里流动着不舍的光芒,身子僵硬得快断裂开来。和尚的头皮几天没有刮过了,已经开始泛青。登高说,和尚,过晌把头剃一下吧,你现在都不像和尚了。和尚说,算了,不剃了,随它去吧。登高严肃地说,那不行,和尚,你现在是革命党人,要听从上级安排,让你剃你就要剃。和尚这个身份对革命工作十分有利,知道吗?和尚默默地点头,又出去忙碌起来。
这一晚的课,登高讲得十分精彩,听课的人都激动地望着登高,有几个女人干脆哭了起来。登高不但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科技差别,还着重剖析了中国国民的小农意识,讲到激愤之处,登高说,日本人把中国人叫成支那猪,我们能答应吗?不!我们不能答应。我们要发奋学习文化知识,争取早日让我们的国家兴旺发达。
学员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旺兴学校开课半个月,效果非凡,受到上级的充分肯定,上级不断派人来取经,但这也给登高制造了很大压力,仅接待一项就让登高入不敷出。有时候,远道的同仁还要住在旺兴,既增加了财物支出,也增大了暴露的危险。登高和省党部的栾劲书记长交涉过,栾劲同意暂时不再派人来旺兴。宋掌柜同时带来了可靠消息,大批可疑人员出现在旺兴的周边,对旺兴进行全面的监视。
有一天,一个叫花子甚至闯进学校,赖在教室里不肯离开。登高怎么看那人,身上都有一种邪气,让人望而生畏。接着,诸城县里的内应也传来消息,说陈太爷已经开始关注旺兴的农民学校,已向济南府写了奏折,说明了旺兴的情况。也许用不了多久,济南府就会转回一道批文,明令取缔旺兴农民学校。真到了那一步,事情就难办了。登高觉得,自己有必要到诸城去一次,都说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如果能和陈县令做好沟通,让他暂时对旺兴学校视若无睹,那无疑会为下一步的工作争取到宝贵的时间。登高马上做了一番布置,准备第二天一早就动身去诸城。
和尚连夜去青龙潭请来了卢大头,权做登高的贴身侍卫。卢大头拍拍自己的镖袋说,放心吧,叶少爷,有我老卢在,诸城县没人能动你一根毫毛。登高欣慰地说,那是自然。
天亮了,登高起身洗漱,在和尚的服侍下吃了早餐。卢大头一身短衣打扮,在门外等候。和尚关切地说,大哥,马替你备好了,你们小心为上,不要冒险,我们都等着你回来。登高说,不能骑马,那样目标太大,我们步行。放心吧,有陈冰如在,料想无事。
晨雾正浓,路边的槐树上淋漓着重重的水汽。登高和卢大头沿着旺兴山脚的一条小路,向新生那边走去。过了新生,就是石桥,再往南八十里,便是诸城县城。
登高和卢大头一前一后,沿着大路疾走。雾气好像化不开的包袱,把登高和卢大头紧紧裹住。卢大头十分谨慎,稍有风吹草动,便做出停止的手势,直到确信没有危险,才招呼登高继续前行。
两人走到程戈庄镇,正逢镇上大集。登高饶有兴趣地东张西望。卢大头紧跟其后,一刻也不敢马虎。登高不时和卖东西的百姓说几句闲话,偶尔也抓起一把花生米或者柿饼,细细地品尝。遇到穷人,登高也会掏出几个铜板,塞到人家手里。卢大头则留心着前后左右的公人,遇到衙役或者捕快,他就用身体护住登高。如此几次,卢大头对登高说,叶少爷,看来官府还没有注意到你头上。登高说,欲擒故纵也未可知,还是小心为妙。卢大头点点头,继续观察四周。
到了下晌,两人进了诸城县,到悦来茶馆坐下。茶馆掌柜派小二到县衙找来了陈冰如,三个人重新泡上茶,开始说话。
陈冰如一身新衣,脸上薄施铅华,神态自若地喝茶。她本来有话要说,但碍于卢大头,她一直沉默着。卢大头何等聪明,站起来,谦恭地说,叶少爷,我去看一个朋友,稍迟些回来,你们聊。登高嘱咐说,小心些,我在此专等。
卢大头便退出去了。
陈冰如从窗口看着卢大头走出悦来茶馆,便走到登高面前,认真地看了看他说,登高,瘦了,吃得不好吗?登高说,吃得好,睡得好,可能是忙了些,没事儿,瘦点儿好。陈冰如不说话,只是轻轻地握着登高的手说,你要注意身体,不要太操劳了。两人一时无话。登高心情是复杂的,他知道自己深爱着这位姑娘,可是,他顾虑着自己的身份,一直不敢过度示爱。爱不是占有,不能为了自己而牺牲对方的利益。如果爱需要一方奉献,他宁愿这一方是自己。
陈冰如又问,登高,遇到麻烦了?登高点点头。陈冰如说,有什么麻烦,说嘛,我能帮的,一定帮,我帮不上,我就找我爹,在诸城县,我爹可说是无所不能。登高说,没错。
登高并不急着说事儿,对于革命的意义,登高还没有系统地对陈冰如进行灌输。考虑到陈冰如的身份,登高不能不谨慎。革命是伟大的,但牺牲却是残酷的。那不是玩笑,而是血淋淋的人头落地。按大清律法,弄不好还要连坐,牵扯到家人的安危。
陈冰如也不说话。她知道,该说的话,登高会畅所欲言。她愿意陪着登高体验无言的美妙。天上的白云像刚轧出来的棉絮,白得晃眼,陈冰如沉默着,久久地向天际眺望,看累了,陈冰如便去看远山的轮廓和状元牌坊的黛色身影,有那么一阵子,她还望着对面的一棵大柳树出神,那上面一直落着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她的心被这群东西吵乱了,以至于预谋了许久的体己话儿,在登高面前一句也想不起来了。
陈冰如真的预备了好些话,都是那种掏心掏肺真心牵挂的心里话。她不止一次下定决心,见到登高,一定要说出来,她想让登高知道,她有多么想他,有多么爱他。可是,见了面,她张了几次嘴,却羞涩了。她想骂自己,想打自己,可她却不想让登高为她着急,万般无奈,只好忍着,她可不想让登高觉察她有任何异样。她心疼这个男人,她爱这个男人,只要有办法,她绝不让这个男人因为她分心。现在,这个男人肯定遇到了难处,就算是为他去死,她也不会皱眉。
登高似乎并不关心她的内心,边喝茶边问,冰如,你父亲还好吗?我有日子没见他了。陈冰如一笑,盯着登高的眼睛说,哟,知道关心我的家人了?有长进啊。登高说,爱屋及乌,人之常情啊。陈冰如说,谢你挂念,家父尚好。登高说,冰如,你能不能让我见见你父亲?陈冰如不以为然地说,你去见不就得了?又不是没见过。
登高当然见过诸城知县陈世林。印象中,那是一个颇有修养的人,思想也算开明。登高曾幻想着策反陈世林,让他也站到革命队伍中来。此事一旦成功,影响将是巨大的。这对大清官员来说,无疑是一枚平地惊雷。开了先例,效仿者势必层出不穷。
登高说,冰如,眼下革命党闹得沸沸扬扬,你怎么看这个问题?陈冰如给登高拿了几块甜点,试图避开这个话题,她说,革命党恐怕离我们很远吧?登高说,人说天下事事事关心,你怕也难脱干系啊。陈冰如说,如果你是,那我就跟你闹革命党呗。登高笑了,他给陈冰如添上茶,巧妙地转换了话题。登高说,什么时候能见到你父亲?我有事需要他指点。陈冰如说,三日内我会答复你的。
晚上,陈冰如到登高下榻的客店,请登高和卢大头吃饭。菜是酒楼里订来的,酒是诸城高粱烧,加上刚做好的酱肘子和烧鸡,也算丰盛。陈冰如先敬了卢大头一杯,再敬登高。陈冰如说,登高,我爹答应后天晚上,在家里见你,不知意下如何?登高说,好啊,我一定按时造访。
陈冰如看了看卢大头,再看看登高,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她在想,这两个人有意思啊,一个是留学东洋的高材生,一个却是杀人越货的土匪。是什么让他们走到一起来了呢?难道是登高向恶?或者说卢大头向善?说登高向恶,陈冰如不信。若说卢大头向善,陈冰如仍是不信。卢大头缘何有了向善之心?是登高的人格在起作用?这个念头甫一出现,陈冰如就摇头否定了。不,不可能。莫非说,这两个人之间会有什么交易?陈冰如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一个冷战。据陈冰如了解,父亲陈世林与卢大头素有仇怨,如果卢大头利用登高制造对父亲下手的机会,那是很有可能的。
想到父亲有可能惨死在惯匪卢大头之手,陈冰如的小拳头就攥紧了。酒过三巡,陈冰如再次给卢大头倒上酒,趁着卢大头兴致正高,陈冰如忽然问,卢寨主,你以后会弃恶从善吗?卢大头看了看登高,良久才说,土匪从善,是个难题。先前我一直没有信心,可谓顾虑重重。不过,自从认识了登高少爷,我就有信心了。我觉得人还有另外的活法,那就是忧国忧民,造福乡里。我想过了,不论遇到何种麻烦,恶要弃,善要从。我卢大头从今儿起,要跟着登高少爷做一个好人了。陈冰如不失时机地问,以前的仇家要是不依不饶怎么办?卢大头严肃地说,那倒不怕,我这边把仇恨泄了,别人断不至于找我的麻烦吧,毕竟我恶名在外,余威尚存嘛。陈冰如多少有些释然,又给卢大头倒上酒,说,卢寨主,饮完这一杯,小女子要告辞了。卢大头把酒喝了,说道,请便。
陈冰如早上醒来,便去了齐鲁学馆。今天,诸城学子王继宗开馆收徒,下重金礼请县令陈世林主持开馆仪式。还没走到齐鲁学馆门口,就听到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拐过榆树街中段的十字路口,陈冰如看到上百人围拢在齐鲁学馆门口,父亲陈世林正满面春风地为学馆剪彩。随着一条红绸被几位诸城名流剪成数段,齐鲁学馆立时大门洞开,几十名童生呼叫着,涌进学馆。
学馆正式开课授业。
陈冰如并不走过去,只是静静地等在旁边。稍顷,父亲在乔书吏的陪同下,乘一顶轻便轿子缓缓而来。陈冰如上前福了一福,轻声叫道,爹。
陈世林掀开轿帘,见是女儿,便招手让她上轿,让轿夫继续前行。一个衙役打着铜锣,在轿前开路,那种威严的锣声,提醒着诸城居民一体回避。
回到县衙,陈世林认真地看了看这个宝贝女儿。女儿十九岁了,已出落成诸城有名的美人。琴棋书画,填辞作赋,女工厨艺,无所不精。只是这丫头的个性了得,全然不是女子风范,处处不让须眉,让陈世林甚是头疼。劝也劝过,却没用,人家不听,还有一套接一套的理论反驳。女儿大了,爹经常说不上话,她娘又不得要领,便让这丫头越来越野性了。没有她不敢说的话,没有她不敢应承的事儿。诸城县几乎是她在当知县了。陈世林每思及此,都会揪心地焦虑。
陈世林首先发问说,冰如,有事找我呀?陈冰如说,爹,女儿前儿个不是说让你见一个人吗?陈世林略想一下,说,是的,你让我见新生的叶公子,怎么?又有变故?陈冰如说,爹,女儿想了想,你还是不见为妙,这个人,背景复杂呢。陈世林微微笑了,盯着女儿说,见也是你,不见也是你,到底让爹怎样啊?陈冰如便撒娇说,爹,让你不见,你就不见嘛,说那么多干吗呀?陈世林再一次笑了,眼睛转了转,便戏弄女儿说,闺女,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那可是留洋回来的大才子啊,爹都很喜欢呢。陈冰如红了脸,说爹,你怎么这么坏呀?我就是喜欢他,怎么啦?陈世林提高了声音说,我能怎么样?到了这一步,我就准备嫁闺女呗,唉,姑娘大了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仇啊。陈冰如撅起嘴说,爹,女儿什么时候和你有仇了?你见过比我更孝顺的女儿吗?陈世林一本正经地说,那倒没有。陈冰如这才转嗔为喜说,就是了。
陈冰如让父亲屏退了左右,自己便和父亲谈起了登高。陈冰如简略地介绍了一下登高的情况,便话题一转,和父亲谈起了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
革命一词,陈世林并非闻所未闻。他此前去过几次济南府,谒见过本省巡抚孙宝琦和本州知府黄曾源。他们屡屡跟他谈起革命,听他们的口气,看他们的表情,这革命分明要成大清国的克星了。听说北京的大人物,也有许多参与了革命,要跟朝廷作对呢。陈世林知道,一个朝代若是尽了气数,就会出现异象。当年的大明朝,到崇祯帝时,顺应天时地出现了李自成。等李自成把大明军队打得七零八落,多尔衮不失时机地率清军入关,几乎是白捡到了一片锦绣江山。眼下,宣统皇帝还小,皇室内部派系倾轧,财政凋敝,入不敷出,军队建制瘫痪,各省督抚拥兵自重,官吏大肆贪敛成性,行政体系已陷入混乱……长此以往,这大清国还能撑得下去吗?其实无须问,陈世林知道,病入膏肓的大清国已经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至于什么人接掌政权,他还没看出门道。不过,就算是改朝换代,于他这种蕞尔小吏也干系不大。弄得好,他可以继续当他的县太爷,弄不好,也不过是回家养老,想他这些年在诸城县知政,贪也贪过,搂也搂过,可修桥补路之类的善事也做过不少,当地民众断不至于把他也革命了吧?
其实,陈世林自从听说登高,就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个叶大少爷从日本归来,他会不会是革命党。这孙大炮近年来一直在日本活动,像登高这样的少年精英,难免不是孙大炮的拉拢对象。再说,越是精英,越有着清醒的头脑。登高未必就没看到大清政府的腐败与不可救药。革命就是这些精英们正在追赶的时尚。那么,自己该怎么和这个年轻人相处呢?一刀斩了当然不行,目前的形势,可谓神鬼难测,说不定几年以后,革命党人治理天下,那时,万一追究旧账,本官就得变成革命党的阶下囚。这几年,政府杀了数不清的革命党,保不济将来人家也会杀大清官员,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上台后,第一件事报仇,第二件事报恩。眼下,自己身居七品知县,得饶人处且饶人,无论如何,都得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啊。女儿对叶少爷如此关注,分明是动了春心,做父亲的,既要照顾女儿的脸面,还得为女儿设计安全和幸福生活道路。稍不留神,女儿就得吃亏,万一连坐,恐怕自己都得吃挂落。要和登高少爷谈谈?谈谈就谈谈吧。反正现在登高还没有公开宣称他就是革命党,这种时刻,喝酒、见面、来来往往都正常。
不过,对女儿的提问,陈世林也不准备搪塞,他还是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陈冰如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她拉着父亲追问说,爹,你到底怎么看待革命呀?你倒是说话呀?陈世林放下茶杯,世故地说,丫头,革命未必就是坏事,真成了气候,人家革命党就得坐天下。自古以来,成者王侯败则贼,没有反正可分。孰对孰错,老天也弄不明白。陈冰如着急地说,那我该怎么办呀?陈世林不紧不慢地说,凉拌!陈冰如眼睛一亮,盯着父亲的眼睛说,爹,你快说,如何凉拌?陈世林说,既然我们不能正确地判断形势,那就若隐若现,若即若离,观望嘛。保持可进可退的姿势,永远都会主动啊。陈冰如摇了摇头说,爹,这不好吧?爱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势利呢?陈世林轻斥道,你懂什么?这种事把握不好,是要灭九族的。你不要忘了,我们身后还有一个大清国,大清的律法残酷着呢。当年,翰林徐骏写错了一个字,就被雍正帝革职,接着有人告发,称徐骏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反诗,于是,好端端一条性命就丢了。文字狱尚且如此,何况乱党叛逆!
陈冰如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早在结识登高之初,她也猜想登高可能是革命党。那时候觉得好玩,就和登高保持着来往。没想到,男女之间是经不起交往的,一有接触,陈冰如那颗多情而敏感的心就怦然乱跳起来。她理智地告诉自个儿:别想他!可越是这样,越是想得厉害。到后来,她已经控制不住思念了,一想到登高就全身发软,就神情恍惚。没办法,她只好放任思绪,想个没完没了。想到最后,几天不见登高,茶不思饭不想,连父母问话也充耳不闻了。用娘的话说,这孩子,傻了!
今个儿把话说到这儿,陈冰如也没有顾忌了。她直截了当地问,爹,眼下登高有事,你帮不帮?陈世林说,对叶少爷的事,我不能轻易表态,至多就是默许。如此,对内对外,都有余地。陈冰如这一次没有摇头,而是乖巧地说,爹,革命党来头猛,大清国的剿杀势头也不会差。关键时刻,你还得帮他,不管怎么说,你闺女喜欢他,爹,爹,算闺女求你了。陈世林叹息一声,不无责备地说,唉,哪有你这样的闺女,护着男人,羞耻都不要了,好吧,谁让你是我闺女呢,我帮他就是。不过,到了爹帮不了的时候,你可不能怪爹。陈冰如沉着脸说,闺女知道。
这一头晌,陈冰如一直坐在卧房里发呆。风云际会,世事无常,她懂。可是,到了改朝换代的节骨眼儿上,她的见识便不够用了。茫然的事情,最难决策。这种事又不便声张,陈冰如只有闷在肚子里,任其煎熬了。
心里一乱,想的事情就多了。先想到登高有一天会有牢狱之灾,若是在诸城县,陈冰如保证让他受不着苦。惹急了,她会搬进牢里与登高同住。若是在济南府,她也有办法通融,这年头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也能叫磨推鬼。钱不是问题。这些年,她已经攒了一笔钱,换成龙洋,有上万之多。区区一条人命,五千足矣。再说,还有爹的老面子,再不济也值几千个龙洋。陈冰如越想越有底气,她想,就是拼上自个儿的性命,也要让登高活下去。
陈冰如忽然想到了一个重要问题,登高的农民学校在不在官府的取缔范围?如果官府不管,那自然没有问题。万一官府不许,那登高就成了万众瞩目的靶心,闹大了,恐怕爹也难做。陈冰如越想越急,她换上衣服,便奔向衙门大堂。秋风正急,吹落了中院的柳树叶子。陈冰如低头望着落叶,顿时心生惆怅。她觉得不吉利,本来是叶登高,却变成了叶落地。这是不是一个不祥的前兆?
陈冰如停住脚,叫来了丫环。她吩咐说,去,把所有的叶子都扫起来,倒掉。看着丫环急匆匆的身影,陈冰如又去看那棵柳树。这是当年父亲进衙门时栽下的,几年下来,已经有脸盆粗细了。本来是想寓无心插柳,现在却寓成了叶子落地。陈冰如想了想,便起身先到县尉衙门。陈冰如果断地对一个捕快说,带上斧子,去帮我砍树。
一顿饭的工夫,那棵柳树已经被砍倒拖走了。陈冰如望着崭新的树根茬儿想,现在,叶子再也不会落地了。
陈冰如心情愉快地走进父亲的公事房,父亲却不在,只有靠窗的榆木桌子上,端放着父亲的文房四宝。陈冰如在父亲的桌前坐下来,无意当中看到了父亲尚未写完的奏章。她俯下身子看了看,不料,这一看,顿时让她变了脸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