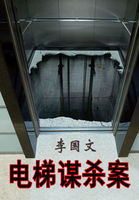几天后,马其明便让马全留了下来,帮助自己打理生意。马全为人聪明,举一反三,加上马其明有意培养他,不到两个月,就掌握了做生意的窍门。马其明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但不知为什么,却不肯放手让马全去管理商行名下的任何一间店铺。日子一长,马全有些不耐烦了,这一天终于找了机会对马其明说自己想去管理一家铺子的事。马其明意料之中地说:“你当掌柜?你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吗?”
马全使劲地点了点头,说:“侄儿这两个月来跟着二叔学到了不少东西,我相信一定可以的。”
马其明想了想说:“你想当哪家店铺的掌柜?”
马全早有准备,说:“就酒楼吧。”
马其明似乎有点吃惊,问道:“酒楼?”
“对,酒楼。”来源福商行名下十三间店铺,最挣钱的数米行,最不挣钱的就是酒楼。马全早已想过了,去米行显不出他的本事,如果能把酒楼的生意做起来,那就足以让二叔相信自己的能力了。马其明思忖了一会,点头说:“也好,那你就去试试吧。”
马全兴奋不已地上任了,实际上他早已经来过酒楼很多次了,对管理上的弊病已然心中有数。酒楼是两层建筑,装饰得很是漂亮,但是厨师却不上档次,只能做一些低档的菜,客人也只是一些比较穷的人,而且赊账很严重。针对这些缺点,马全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调整。他把原来的厨师辞退了,另外高薪聘请了徽菜高手,并将客人定在有钱人的身上,这样一来,菜式精美、花式繁多,而且又没有赊账现象,生意一定会红火起来。
果不其然,调整之后的酒楼生意日渐红火,最繁忙时上下两层满是客人。一个月下来后,马全一算账,利润比上个月翻了十倍有余,当下自得意满地拿着账本去给马其明看。没想到马其明看了后却不置可否地说:“从明天开始,你还是回来跟着我吧。酒楼由原来的掌柜打理。”
“什么?”马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已经做得这样好了,为什么不仅得不到称赞却连掌柜的位子也要撤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马其明摇摇头说:“你什么也没做错。好了,别说了,你去和掌柜的交接一下吧。”
马全开始很委屈,但很快就想明白了,二叔这是在考验他,也许是准备重用他了。这样一想,也就释然了,做起事来更加努力。
果然,几天后,马其明因为有事需要出次远门,他让马全暂时打理商行的一切事务。马全知道这是一次机会,他事必躬亲,兢兢业业地打理着商行里的所有大小事务。以前他看二叔这东家当得很悠闲,却没想到自己做起来却是如此繁琐。十三家店铺各行各业的都有,如果不一一了解,根本不可能知道其中的规矩。好在马全心细,花了很多天时间把各店铺的业务摸了个透,然后把十三家掌柜招在一起开了个会。会上马全对各掌柜管理方法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原来这也是一片好心,没想到却惹了大家极大的不高兴。
米行掌柜第一个跳起来,说:“我给东家打理米行时你只怕还没有出生,你有什么本事在我面前指手划脚的?”
“对,我们这些掌柜的跟着东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东家都从来不过问我们经营上的事,你算老几?”
马全的脸涨得通红,这些个掌柜之所以倚老卖老,还不是因为自己年轻,说话没有威望。当下只得草草地结束了会,心中却暗暗发誓,一定要做出成绩来让他们信服。
这天马全正在休息,下人来报湖州的李清山老板求见。马全曾跟着马其明会过李清山,此人是湖州的一个丝绸商家,为人甚是阴险狡诈。半个月前,来自波斯的一个商人带着一船波斯丝绸,远渡重洋来到扬州寻求买家。马其明去看过了货,这些货做工精美,图案繁多,充满了异域风情,马其明当场便付了定金,回去筹钱。没想到等到筹足了钱去提货时,波斯商人却直摇头,说已经有人买了。那买主正是李清山,谁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把已经收了定金的波斯商人给说服了。正因为这事马全对他的印象很差。
马全来到客厅,看到了李清山。奇怪,几天没见,他怎么像是生了一场大病一样,精神很是萎顿,不由得问道:“李老板这是怎么了?”李清山摸了摸自己的脸,苦笑着说:“我也不瞒你了,那笔波斯丝绸我上当了。”李清山长吁短叹地说出了原因。原来那日他送了一笔货到扬州来,收得货款后正要回去,却听说波斯商人在寻求买主,也赶去看了,他的想法和马其明相同,觉得这肯定是一笔挣钱的买卖,当下就要买下。波斯商人说已经有人付了定金,怎么也不肯。李清山得知马其明只是付了定金后,立即四处借债,将白花花的银两堆在了波斯商人面前。波斯商人虽然收了定金,但为怕夜长梦多,也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了。
李清山所借的银子大多是高利贷,拿到货后他立即在扬州本地开始推销。他想得很简单,这样的波斯货销售一定会很乐观,只怕几天就可以销售一空,到时不仅还上债,还带得一大笔银子回去。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那些丝绸竟然只是上面几层是好的,其他的都已经是发黄了,这显然是在海上遇到了风浪,海水浸湿了丝绸,而波斯人又将其捂着,结果就泛黄了。这样一来,虽然丝绸的花色让人喜爱,可是品质变了,买的人极少。李清山一面被堆积如山的货压得喘不过气来,一面又被高利贷追得四处逃躲,无奈之下,只得来请马其明相助。
马全听了他的话,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所谓天不欺人,讲的不正是这事吗!他说:“对不起,我的二叔不在,你需要我怎么帮你?”
李清山羞惭地说:“我想……我想请来源福收购了这批丝绸。”李清山也知道自己这要求太过无礼,声音越说越低。
马全吃惊地说:“我们拿这批次货来做什么?”
“我……我也是没办法了,请你看在同行的面子上帮帮我,日后如有机会,定当回报大恩大德!”
马全沉吟道:“可是现在我二叔不在这啊,这如何是好?你不如再去别家看看?”
李清山牙一咬,说:“这样吧,只要你把我的高利贷还了,再给我一些回家的盘缠,这批货就是你的了。”
马全笑了起来,他要的就是这句话。于是问了他所欠下的高利贷数额,便拿出银两交给了他。李清山拿着银两双手直颤抖,这笔生意他做得很惨,几乎把前半生的积累全数亏尽,他苦笑数声,捶胸顿足地走了。
这边李清山刚走,马其明也回家了。马全炫耀似地说起了此事,又说:“侄儿早已想好了,那些丝绸虽然有些发黄,卖不上大价钱,但可以作为我们积压货物的搭送物。也就是说,买一定数量的积压货物,就白送一段丝绸,而我们购买丝绸的本钱可以在积压货物中赚回来……”话没说完,突然看到马其明紧皱眉头,一脸不快的样子,忙收住了嘴,不知所措地看着他。
马其明没有说什么,转身就出了门。过了一会儿,马其明竟然拉着李清山回来了,然后拿出一沓银票来递给李清山。李清山困惑不解地问道:“马老板,收购丝绸的钱我已经收过了,你这是……”马其明说:“那时因我不在,我侄儿不懂事,那批丝绸何止值那些钱。这些银票你收着,算是补上不够之处。”
李清山捧着银票,哆嗦着嘴唇说不出话来,突然“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痛哭道:“马老板,我……”
马其明忙将他扶起,说:“人生在世,谁没有个三灾四难的。都是同行,不必言谢!”
马全在一旁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一幕,他实在不知道二叔心里是怎么想的。等到马其明将李清山送走之后,马全还在苦苦地思索着。马其明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坐下,说:“我知道你有什么疑问,现在也到了解谜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想问的就说吧。”
马全说:“说实话,我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有的事,明明是赔本的买卖还要去做。先说酒楼的事吧,我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换了我,而且,我走之后,酒楼又回到了原状,这不是明摆着不想赚钱吗?”
马其明笑了起来,说:“这事啊,很简单。你知道酒楼的厨子是什么人吗?他是徽菜大师的嫡传弟子,什么样的菜做不来?可是我不让他做那种精美的菜,因为富人家可以上酒楼吃,为什么穷人不可以?穷人同样亲朋好友,也有需要上酒楼吃饭的时候。还有,你知道赊账的都是些什么人吗?他们都是些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穷人,如果我不赊账给他们,他们上哪去吃饭啊!当初开这个酒楼时我就没想着要挣钱,我的钱都是来自大家之手,我只是借着酒楼把钱返还给需要的人而已。”
“那些掌柜呢,他们的经营明显地有各种各样的弊病,我不相信你没看出来。”
“他们是我多年来相交的朋友,对他们的忠心我一向不怀疑。你说的那些弊病我当然看在眼里,可是人总有些个毛病的是不是,你管好了他这个毛病,说不定下一个毛病更厉害,只要不是不可原谅的错,错就让他错吧。”
马全又说:“那李清山的事呢?他可是个没有道德的人啊,你还要这么帮他!”
“说实话,对他我也是很反感的,他破坏了生意上的规矩。可是仔细一想,如果不是他,那么受害的人就是我们了。冲这一点,我们也要帮他。另外,他上门来求助,就说明他觉得咱们可信,加上他对货物的品质并没有隐瞒,也足以让我相信他的诚意。人在危难时帮他一把,会让他记住你一辈子。”
马全如醍醐贯顶,恍然大悟地说:“我明白了,要做生意,先得须学会做人!”
马其明哈哈大笑,拍掌赞道:“对!你做生意很精明,是个经商的天才。但是你要知道,做生意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做人。咱们徽州人为什么在各个地方经商都是如鱼得水,就因为我们会做人。”说着,马其明拿出几锭银子交给他说:“你已经明白了经商的道理,日后前程不可限量。但鹰如果一辈子呆在窝里,至死也不会学会飞。当年,我是用十两银子发的家,现在我给你一百两银子,天高任鸟飞,你到外面去闯一闯吧!”
马全扑倒在地,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他双手接过银子,说:“二叔,侄儿今后将永远牢记你的话,至死不忘!”
十几年后,马全成了巨富,这是后话了……
义商
德州绿香茶楼的老板王定生是徽州人,他苦心经营二十年,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主。按说他要什么有什么,应该是事事顺心了,可他的独子王成业却让他怎么也放不下心来。
这天晚上,王定生正在书房里查账,王成业醉醺醺地闯了进来。王定生生气地说:“你又喝醉了?不成器的东西!”王成业没有顶嘴,而是得意地说:“爹,我知道您一向瞧不起我,可我今天谈成了一笔大生意!”王定生没搭理他,继续看账本。王成业见状,一把夺过账本,说:“我没骗您,是真的。您瞧!”说着,他掏出一张纸来。王定生定睛一看,顿时愣住了,原来这是一份订购十万套棉衣棉裤的合约,订货人叫许宾。
王成业看到父亲吃惊的表情,得意地笑了笑:“十万套!这回知道我有出息了吧?”王定生拿着合约看了半天,条款清晰,赏罚分明,确实不像假的,但他还是狐疑地问道:“虽然我们是经营茶叶生意的,但也不会有买卖上门不做的道理。只是这个叫许宾的人为什么会找到你?又为什么会向你买这么多的棉衣呢?”
王成业不以为然地答道:“都是朋友介绍的。”原来,前几天王成业和朋友一起吃饭,酒喝多了就随口夸耀没有他王家不敢接的生意。一个朋友接嘴道:“城里最近来了一个叫许宾的外地人,他要订购十万套棉衣棉裤,可没人敢接这活,要不你去试试。”王成业正想在父亲面前表现一番,听了这话,立即去找许宾。许宾听说了王家在德州的实力,当下表示可以谈谈。“所以,我们今天就签了这个合约。看,我们可以把货分给德州所有的裁缝去做,然后统一收货。这单生意我们可以净赚五千两呢!”
王定生闭上眼睛想了想,说:“我想跟许宾见见面,你安排一下吧。”第二天上午,许宾如约来到了王家。只见他三十多岁,一脸沉稳。王定生开门见山地问许宾,为何将这么大一笔生意交给王成业,许宾哈哈大笑:“生意人嘛,谁有能力接就给谁做了。再说王家有这么大的家业,我不怕他跑了。”
“那能否告知在下,这些棉衣棉裤你准备销到哪里去呢?”
“这个恕在下不便告知,王老板既是生意人,应当懂得行里的规矩。”
王定生笑了笑,说:“既然如此,这笔生意我不能接。这一千两银子算是我们的违约赔偿金。”说着,王定生拿起茶杯,准备端茶送客。王成业送走许宾之后,怒气冲冲地跑过来质问父亲:“爹,您怎么能这样做?说好的事又反悔,您叫我以后怎么做人?”王定生恨铁不成钢地说:“你啊,鼠目寸光。你差点儿给我们全家惹来了灭顶之灾!”王成业奇怪地问:“您这话从何说起啊?”“动动你的脑子,十万套棉衣棉裤如果是直销,他该卖到哪一天?唯一的可能就是有人在他手上订了货,他有把握拿到货后全部出手。可哪里会有这么大的市场呢?这是其一;其二,你注意到他右手的虎口没有?他端茶杯时我看了,满是老茧,加上步伐如此稳健,显然是习武之人;其三,他的口音是天津的……”王成业突然惊呼一声:“难道他是义和团的人?”王定生点了点头,一言不发。
义和团本是白莲教失败后产生的分支,传到天津后,日渐壮大,屡屡犯乱,朝廷已经将其列为乱党,与其有瓜葛者一律处死。王成业说话的声音都哆嗦了:“那我们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