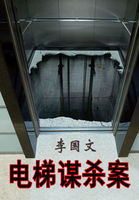一
阿海同时请了中医和西医为妻子治病,使依妹病情暂时得以缓解。虽然,在当地行医的同是福清哥,说的都是带渔溪腔调的福清话,但西医是留洋归来的,中医则是传统国学,因此他们各行其道,互不了解,更谈不上相结合了。西医施用的补液、酸碱平衡及退热的处理,使依妹一度神志清醒,脉象也明显好转,这使得医术高明、经验丰富的俞老中医疑惑不解,以为自己对依妹病危的判断是误诊。但西医陈医师心里十分明白,病菌在病人体内不断倍增,他所施用的补液疗法,是被动的,并不能杀灭病菌,只待病人身体用发热来抵抗。可是,热度过高,又伤了身体乃至致命,因此又不得不用退热药,这是当年西医的无奈与烦恼。其实,那时如果懂得中西医结合之道,在没有抗菌西药的情况下,让中医以清凉解药主攻,西医护持,依妹或许多一线生机。不幸,这只不过是颠倒历史的假设,不是事实。事实是依妹的病情每况愈下,俞、陈两医师背靠背,束手无策,难挽沉疴。
林继祖夫妇得悉依妹病重,常来看望。他们把家中现有的贵重药材如犀角等送来让俞医师选用,但都不见有效。他们如此关切义女(干女儿),使旁人特别是两位医师十分敬佩。其实,在继祖心里,沉积着驱不散的福宋形影。他每次见到依妹,都难免联想翩跹,不能自己。不过,他每次来看望都止步于楼下店堂,毕竟不是亲生女嘛,如何能进依妹的卧房特别是“月子房”。因此,他总是在楼下等待他的妻子,之后,不厌其详地向妻子询问依妹的病情。曾殿臣老先生比平时来得更勤,俞老医师每日来随访病情,他总先期来接待。因此,他对依妹的预后,十分清楚。此情此景,他不得不忠告阿海,已到了让继祖、依妹父女认亲的时候了。但阿海却一日拖过一日。在他的心里,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年纪轻轻的妻子将要离开这世间,渔溪山最好的中医加西医不都在尽力救治吗?
不幸,依妹的病情并不跟随阿海的愿望好转,反而在不断地恶化。但由于中西药的处理,使她几次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每次清醒都给阿海及美玉他们错觉,以为有救。依妹自己,像是在天上人间几度往返,清醒时,恐惧过后想的是阿海和儿子。她出现了今生无能照顾丈夫与儿子的预感,趁着姆妈与美玉在床边照顾的时候,眼看着美玉,嘴唇动了几下。美玉赶紧将耳朵贴近依妹嘴边,听见她轻声地说:“好姐姐,儿子给你,海哥也给你,他人好……”
美玉听着妹妹的遗嘱,承受不住这悲惨凄切的锥心言语,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
哭声惊动了楼下所有的人。
阿海箭也似的奔上楼,大声地叫着“妹!妹!妹!”,但依妹只能张开眼睛望着丈夫,说不出话来了。曾殿臣见情况不妙,叫正好在场的儿子进善,赶快到林府请继祖来与女儿见最后一面。他自己摇着肥胖的身躯,到街头去请陈医师来打“救命针”。
林继祖夫妇进门的时候,曾殿臣把继祖叫到门边,轻声地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随即陪他上楼。阿海见到他们,明白曾老用意,便立即大声地叫道:“妹呀!你日夜找的真正父亲来了,快叫声‘爸爸’哟!”
依妹再张开双眼,嘴唇轻微地动了一下,好像是发出了声音。
继祖将女儿的头抱在怀里痛哭,用手不断地揉着她的面颊与头发。
后来人们说,继祖用泪水为女儿梳洗送行,那是凄凉的传说,也是真情。人世间……
许多人感叹依妹不幸,青春年华就离夫别子,她甚至没有机会开口向亲娘叫一声再普通不过的“妈妈”,也没有机会听到儿子牙牙学语叫出的一声“妈妈”,就这么匆匆地走了,她未曾享受人生啊!但也有人不以为然,说依妹虽然身世清贫,总算是在外婆照料中长大,又有过阿海这样的好丈夫,也做了母亲,且在父亲的怀里安详地离去,无怨无恨,人生不过如此而已,还能有什么企求?在这苦难的乱世,长寿就是多受煎熬哟!曾殿臣就是如此劝阿海,请他节哀。
阿海虽然少年时就开始帮人料理丧事,但还是经不起这丧妻之痛。他的心魂,好像也跟着依妹走了,只是凝神地流泪,什么事也做不了。依妹的丧事是在曾老主持下,由她能干的叔父林孝祖料理,尽早入土为安。墓地选在连泉山,与秀才祖父的陵园相去不远。
在依妹盖棺的时刻,林继祖掏出一个白纸包,轻轻地放在女儿胸前,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曾殿臣看在眼里,心中猜测:那未必是金银财宝,最可能是依妹母亲留下的如今加上继祖自己的头发。老夫子想到依妹在世时没有爹娘可依靠,只是在死时获父母的一缕青丝相伴,不免仰天长叹,悲悯之心致老泪纵横,不能自制矣!
曾殿臣不让继祖送葬上山,白发送别黑发,太凄凉了啊!
依妹走了,阿海还得活下去。他还没有受尽人间的磨难,要继续承担这既非一家又是一家的生活重担,何况还有自己跟依妹留下的儿子,正嗷嗷待哺呢!阿海白天埋头打理店务,忙忙碌碌,倒也过得去。可是,夜阑人静时,儿子由美玉她们带着,他的思绪就像脱缰野马,奔腾不止。少年时,在窗口听私塾先生说:“父母恩深终有别,夫妻义重也分离。”自己对父母没有印象,并不体认什么“恩深终有别”之苦,如今,夫妻恩爱,这“义重也分离”之痛,却是如此难熬。他不明白,为何好好的一句“人生似鸟同林宿”的书语,却流传成“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世情如此淡漠,使他感叹不已。阿海从而想起,自己是与郁家贵吃一个母奶长大的,却阴差阳错,结成难解的冤家。眼下自己的儿子又与他的儿子同吃一母奶,这是天定的轮回么?想到这里,阿海感到彻骨地寒冷。不!绝不让儿辈将来成仇,何况必胜还是美玉的儿子呢。阿海暗暗地下了决心,把必胜视为己出,与自己的儿子同样对待。既然必胜已取王姓,那么,把儿子取名“必利”,这样,“胜、利”连义,都是我王家儿子,长大了就可不分亲疏了。
二
郁家贵与张四被张雅悟派出的寻找阿海的保丁们惊醒,急忙逃离山寨,翻过一座山林,见四面并无动静,才敢停下来。因为,无论是单枪匹马的阿海来报仇,还是罗县长带大队人马来清山,对他俩都是致命的威胁,因此不能不逃。但逃到哪儿去呢?阿头与“永福仔”(永泰县人)的交结,张四只是听闻,并不知晓其联络暗语,如果盲目闯入永泰县境去找他们,人地生疏,势必被黑白双方当“光饼夹肉”吃掉,找不到阿头又不敢出山,他俩只好靠手中的两把驳壳枪,在山区的小范围内乱闯。但大一点的村庄他俩拿不下,三两家偏僻的茅舍,容易拿下却没油水,能吃上一顿热的番薯粥就算收获。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况且,居无定所,没有一觉安睡。这样的日子郁家贵实在受不了,张四也同样受不了。受不了就难免想后退。退到哪里去呢?他们俩都想到了,各自回来的地方去,但那并不是寻死的意思,而且,各有各的心绪。郁家贵并不知道依妹已被他害死,只感到自己已落到妻离子散、无处栖身的境地,要报此霸妻占子之仇,非得冒险回到海上,重投“和平救国军”不可。他认为那儿乡亲多,换个支队即便从小喽罗做起,也比困死在山上有出息。张四早就感到,跟着这姓郁的吃苦,太莫名其妙了,应及早甩掉这个尾巴。他估计回家后顶多让老伯父打两记耳光,痛骂一顿而已,这也不是第一次,经历多了,说不定他老人家又要派我什么重要差事呢。
既然两个人心头都盘算过了,那么,谁先开口其结局都一样。张四卖出最后一道人情道:“山路我熟悉,我送老兄走,可避开渔溪街及林家村,从玻璃岭北麓过马路,经下槽、天宝陂,不必进城门就转上去牛田的大路。这乡间小路不会有保安队站岗,你可把驳壳枪带上,这年头就它最管用。”
郁家贵听了张四一席实在话,心里十分感动。因此,立即回应道:“如果我郁某此去有出息,能光明正大地报答老兄,必事先写封信,经‘兴福祥’杂货店请令伯张雅悟老先生转交给你。不然,也会请人把信送到五岭豆腐店,留阿头老姐处。请老兄今后随时留意我的消息。明也好,暗也好,我有恩报恩,有仇报仇!”郁家贵越说越激动。
按照张四指点的路线,郁家贵顺利地回到郁家村。老伯母见侄儿游荡回来,倒也很高兴。郁家贵父母此时都已去世,不过,长久以来他最亲近的就数这位骂他最多、也关照他最多的大伯母。他请伯母闭上眼睛,自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金镯子,总有二两重,套在伯母的右手腕上。老太婆睁眼一看,差点晕倒。在她镇静之后,嘴里不断地唠叨:“我福浅,福浅不堪这么重礼。我替你母亲收受。这是你母亲积的阴德。”听来好似向上苍祷告,不可因福得祸。
伯母给侄儿煮了一大碗蛋面,并看着侄儿边吃边说他行商赚钱的故事。老太婆心如明镜,这年头行商赚钱哪有这么容易,只不过今日金子在谁手里,就属谁的,多说有何意思!因此,未等侄儿把编造的故事说完,便问道:“有无阿海、依妹的消息?都说他们在渔溪开薯粉店,生意还很不错。”
“我也只是听说,没见到。做行商的东奔西……”
“渔溪是行商要道,你路过没去看他们?奶兄奶弟哟!”
郁家贵正忙着找借口,可是老太好像不想听解释,便接着说:“福宋,噢,依妹的母亲,回来过。”
“是从日本回来的?”
“是的。她在东家村见不到亲人,就来找我这老姑妈。”
“跟日本仔一道来?”
“不,跟她丈夫,高山镇人,往日我见过。”
郁家贵听着,一时脑子还转不过来:为何说依妹母亲的丈夫,而不说依妹的父亲。但老伯母继续说:“他们按我说的,到渔溪龙海薯粉店去看过,可是那儿店门开着,店里没人,街上也没人。”
“那他们一定是带日本仔去的,那时刻渔溪人逃光了!”郁家贵很肯定地说。
“不会吧,他们从我这里走,回来时说:在去的路上,在上迳桥头,迎面遇到从渔溪开过来的日本兵。因为他俩会说日本话,走在前头的那些不会说日本话的日本兵,不敢为难他俩。”
郁家贵明白,跟老太说话,千万不可伤害了她娘家的人。因此,他不再说什么,但心中充满收获感。他迷迷糊糊地感到,这情节将来有用。
郁家贵吃完蛋面,要去看看结拜兄弟们,打听一下海上的消息。但据大伯母说,他们那一帮子人,如今只有老大阿土仍在家种田,其余人她老人家都说不出去向。于是,他就到村西边上去看老大。
阿土“落仔坎”,成亲才四年多就有了三个孩子。尽管他两夫妻没日没夜地忙碌,孩子还是饿得哇哇叫。郁家贵刚进门,看到这番情景就想退出。但阿土还是拖住老弟,要他坐下,并随口说:“走的兄弟,回来过的只有‘大锣’,你这是第二个,还要走吗?”
老大提到老五郁大乐,郁家贵很感兴趣。因为他知道老五也“走海”去,只不知属哪个队伍。因此,便急切地问道:“他混得可好?”
“他自己说,天下最好的事,是到白犬岛当‘和平救国军’。道理他不便泄露,说等我去了就会告诉我。但你看看,我这景况怎走得了!”
郁家贵猜不出那白犬岛怎么个好法,但他知道,那儿也在郑德民管辖下,福清人多。阿土在送兄弟出门时,补充了一句:“他还说,找他很容易。报名郁大乐大队副,岛上无人不识。”
郁家贵按老大所说的,果然很容易就找到老五郁大乐。
郁大乐见老二郁家贵来投,十分高兴。一是因为毕竟是同村的结拜兄弟;二是日前那位姓何的共产党把队伍拉走,以至岛上缺员需要补充。
郁家贵客套地说:“今后请五弟大队副多多照顾!”
“什么‘雷’(鸟)队副!根本没有这个衔头,只不过大队长不识字,文书的事靠我,我怎么写,他就怎么盖印,因此大家都叫我‘大队副’,并不多吃一分钱粮!”
“那你总算得上大队长亲信!”郁家贵恭维了一句,正搔到大锣的痒处。
“这不算什么,还有更重要的呢!”郁大乐趁兴继续说道,“郑德民身边有个亲信,与我结拜。你知道郑司令是什么人?我看你猜也不敢猜,他是军统戴笠手下人,到海上来‘曲线救国’。”
对此,郁家贵多少也有所听闻,但仍然装作很惊讶。
老五大锣得意地继续说:“那何队长是什么人?嗨,更出奇了。他手下有个海口人,在他们队里像是当家的。那人什么事都找我帮忙,我与他真是一粒芝麻也分两半吃!他告诉我,他们是共产党!”老五停下来,看看家鬼是否被他吓出满头汗。郁家贵听到“共产党”三个字音,倒真的吓得面色变了。因为他差点被共产党游击队俘虏了呢!郁大乐继续说:“我能帮的都尽力帮他们,无非是粮草、弹药。我这里不稀奇,他们手头最缺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