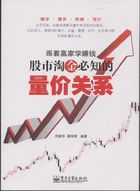阿海进了张家大门,连起码的招呼礼节也不顾,就在张老太的引导下,立即奔到依妹床边。夫妻俩超越了五千年的传统礼节,当着人前抱头痛哭。还是老太太及时提醒:依妹在坐月子,不可伤泪泉。这时,阿海才把依妹的头从怀里轻轻地放在枕头上,抱起她身边的胖儿子。二十二岁却饱经风霜的阿海,一股说不出的亲情暖流,涌上心头。他不在意自己满腮胡子,把脸贴住儿子,惊得儿子哇哇地哭。老太太赶快接过“蜡烛包”。阿海这时才想到,应向张老先生致谢。他出了房门,即见等在外头的张雅悟,便赶紧上前道:“落难时节,多蒙老先生收留与照顾,只怕晚辈今生无以回报!”阿海双手揖拳,很为激动。
但张老摆摆手道:“自己人不说客气话,照料自家儿媳,理所应当。”
张老一时忽略,未去想阿海并不知道自己要收他做义子这回事。因此,阿海听到“儿媳”两字,有些突兀。
张雅悟的儿子立即解谜道:“父亲派我赶到林府,要我传达两桩事:一是他老人家要与你结义为父子;二是我们会服侍好阿嫂月子,请你不可冒险进山。”
此情此景,此恩此义,阿海听着十分感动,未有片刻迟疑,立即行大礼:“父母亲大人在上,受不肖一拜!”
阿海用的是戏台及书摊上的语言。因为他自幼熟记的是这类书语,不加思考,即刻反应的就是这类书语,因此,它是发自肺腑的。张老夫妇即刻上前扶起阿海。
老太太说:“现在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坐月子怕风,又加依妹体弱,应好好静养,满月后出山不迟。”
阿海听了义母的话,觉得道理很明白,如不遵从,就是见外了。便应答道:“听从两老安排,请指点应采购些什么,我明日出山照办。”
义父立即阻止道:“山里情况不明,你不宜出村,阿头他们是不敢进村找麻烦的,来了也不怕。明日还是叫你弟去跑一趟,先到林府向你岳父母报个安,后到渔溪街买些补品。”
张老这先到林府报安的安排,是很聪明的。只要看一看礼数是否到家,就可测试林府与依妹的亲情是真是假。因为,此间考究人家坐月子,由娘家各方亲戚供应“每日一鸡”,供三十只鸡。对你林府来说这是小意思,但要动员三十家近邻远亲来送礼,那就要看你林府的亲戚是否把这女儿当一回事了。此外,张雅悟也想到,有了娘家的三十只鸡,要添购的其他食补品就不多了。
四
林继祖三兄弟得悉张雅悟花大力找回阿海,都十分感动。张雅悟儿子多余地说:“我们会照应好阿嫂的月子,我娘说,她会把你们的女儿当自己的一样看待,请放心。”此话一出,立即震动了林家三兄弟特别是继祖夫人。这两天林府的人都在担心阿海夫妇的安危,倒把应该给依妹备月子礼的事忘了。仓促间如何应付,那倒是需要时间商量一下。于是,继祖夫人一面着佣人备饭招待客人,一面与家人背后商议,之后,对张雅悟儿子说:“亲戚们山路不熟悉,陆续送来的礼鸡由我们收下。今日先请亲家叔带回三十只鸡,如不够用,尚有劳你再辛苦一次。”
林夫人明知张家哪有再来讨鸡的道理,但话总尽量说得悦耳,大家风范嘛。
山里人上街,除张有财这类好吃懒做的少数人外,往返路上都不让肩膀空着,连张雅悟儿子这样比较富裕人家的子弟,也不例外。因此,他个子虽小,但肩膀很硬。他今日挑了两个双层鸡笼,外挂两个布袋,一袋装着继祖当时带回来孝敬老父但未用完的炼乳、奶粉、麦片等罐头食品,另一袋塞满新旧的婴儿衣裳、尿布及小毛毯等等,总共超过百斤。因此他无法再到街上购物添重,径直回张家庄。
张雅悟听了儿子转述,再看看这一大担的月子礼,更加确信这产妇依妹是林继祖的女儿。林府千金哟!非比寻常百姓家的女子。他想到张家出面办满月酒的时候,林继祖将带领林府至少三十家亲戚进山,那三十多顶轿,加上夫人们贴身的丫头、佣人,必将组成长长的人阵穿过村庄,其声势好比元宵节游灯,那是多风光、多壮观!那么,张、林联姻就成为家喻户晓的事实了。张雅悟不禁感到庆幸,阿海儿子在这里降生,的确是我张家之福啊!
阿海回到了身边,依妹百无忧虑,静心坐月子好了。但她身体仍然那么软弱,饮食难进,每顿只能勉强喝些老太太特别为她熬的糯米粥,至于鸡、鸭、鱼、肉,那只能眼看着端进端出。她平时话就不多,甚至跟阿海一起,也没有太多话好说。她见的人不少,但见了并不聊天,肚子里的世事自然就少。外婆那里听来的“嫁给鸡跟鸡走,嫁给野猫满山跑”这类故事,说一次也就够了。因此,她跟阿海住在郁家村时,虽然是独门独户,本可不受拘束地说悄悄话,但她却没有什么可多说的。过去,她总是在那夫妻特别节目完成之后,靠在阿海的肩膀上,听丈夫“说古”。阿海肚子里的料子多,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但依妹未必都要听新鲜的,一个故事,即使重复860遍,她也听不厌,反正听着听着就睡着了。阿海只比她大四岁,可是她把他当做大四十岁的父亲,虽然,她并不知道父亲的怀抱有多么温暖。在“龙海之家”,美玉母女的卧房与他们夫妻俩只有一板之隔。当美玉隐隐约约地听到阿海哄依妹睡觉的故事后,第二天总是找碴发脾气。一次、两次、三次过后,依妹体会出什么来了,再也不敢叫丈夫说古催眠。但今夜在张家,房墙是花岗石建造的,即使鼾声如雷也传不到隔壁,做丈夫的就大胆说吧。但阿海突然惊觉,贴在胸脯上的依妹,全身发烫。此时已是深夜,夫妻俩都不愿打扰张家人。按依妹的说法,发热是常有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阿海心神不定,熬到天亮,立即找张老夫妇商量。
要找医生的话,阿海与张雅悟首先想到的无疑是俞老中医。但世局如此混乱,山路如此不太平,勉强去请,实很为难名医,还是先请邻村的医生来号脉吧。那医生诊断依妹得“月子风”,说他见得多了。他知道病人是镇上来的,因此加了一句话:“请谁看都一样。”可是,见得多了与治好的多了,本是两码事,做医生的含糊其辞,却使病家听了感到放心。戏法人人会变,山村里走江湖的更通此道,不然哪有病家上门?但依妹用药后毫无起色,每当过午至深夜,便热得滴汗不出,时睡时醒,醒时语言也显得含糊。三天了,吃的那么少却时有呕吐,吐的是酸水和苦汁。阿海非常着急,张老夫妇也十分地担忧。阿海想,与其去抬俞老医生勉强进山,不如把依妹母子抬回渔溪街,一切也就方便了。老夫人坚持说:坐月子不能受风。但张老倒是想:已经受风了,留下来责任太大,出了事对张家也不吉利。因此,他同意阿海的决定。
依妹是无法坐轿子的,即使不透风的大轿也不行。好在张家有一张“南洋帆布床”,把床脚一折,便是一副担架。找一位矮个子搭档抬布床,上山时阿海抬后头,下山时阿海抬前头,跟当时抬曾殿臣进山那样,轿子平稳,担架也可平稳。再叫一顶大轿,让张家儿媳抱着月内婴儿上轿。张雅悟却有意坐上竹轿显眼,并带一帮保丁开道,大小土匪不便也不敢来找麻烦。万事安排妥当,依妹上担架时,张雅悟儿子放了一串“百子炮”,为壮行,也为祝福。
此刻约莫是上午十时,太阳已照到了山村,从村道进入山径的时刻,也不至有寒意,但张老夫人事先还是用棉被把依妹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还给她头上扎了一块红布,这自然是最要紧的事。依妹凝神仰望,树梢间破碎的天空,忽明忽暗,闪闪烁烁。望着望着她似乎睡了,不过,她本来也不算很清醒,只是此刻她眼前出现了外婆,她老人家忽近忽远,似笑非笑,不知是喜是悲……
依妹十八岁了,她在外婆身边度过了十六七个春华秋月。她梦里从来只有个外婆,即便在阿海出洋,令她日夜思念的日子里,入梦的仍是近在眼前的外婆。她不知父母是什么意思,都到哪里去了?她相信外婆说的,等她长大了父母都会回来看她、疼她。但当她长到能挑起担子往镇上送海杂,送外婆做的绣花鞋、针线活,人们都说她一举一动像母亲的时候,还不见母亲回来,也不见父亲回来。她高兴的时候,趴在外婆怀里笑,但更多的时候是趴在外婆怀里哭!个个孩子都在哭哭笑笑中长大,穷孩子富孩子莫一例外,但依妹哭比笑多。她才过十五岁,世事懂得不比别的孩子多的时候,就听说有人要来抢亲。她知道“抢”总是可怕的事,于是听令外婆、姨婆,躲在家里,像躲海盗那样,战战兢兢不敢出门。后来又说抢亲不可怕了,可又抢不成。她十六岁生日才过不久,就吹吹打打地把她嫁给了阿海。啊!阿海,只有阿海,一夜工夫就驱散了她多少年的恐惧,并解开那多么深奥的神秘。人们必说:一夜夫妻百日恩嘛,人人都如此,那算什么稀罕!但依妹是不会同意这种说法。有了阿海,依妹不再羡慕别人有父母、兄弟、姐妹,有了阿海,依妹感到这人世间多么有趣,再也不埋怨父母把她带到世上。无论是隔洋思念,或者惊慌的逃难,凡事只要跟阿海连结在一起,是苦是乐她都吸收,也都能转化成营养滋补自己成长。
依妹多么热爱现世生活。酸甜苦辣都是味哟!
担架把迷迷糊糊的依妹抬进了“龙海之家”。陈美玉和她的母亲,一起奔到店前,抱着布床放声大哭,说不清是喜是悲,应当说是悲喜交集吧。因为她们并不知道依妹病有多重,以为只是落难中分娩,惊慌一场而已。
张家儿媳告诉美玉,依妹还没有开奶。美玉立刻把孩子抱上楼喂奶。真是有奶便是娘,这孩子一碰到奶头,就吮吮啄啄地吸起奶来。
阿海把依妹抱上二楼卧房,盖好被子之后,交给美玉母亲照顾,自己赶快去请医生。他先跑到俞家,但俞医生出诊不在。这时他想起助产士医馆一姐,她会接生必也会治产后病。可是医馆一姐说,她愿意来帮助做些必要的护理,但不会用药治病,应尽快去请陈医师,并说,陈虽是外科医师但产后发热的病症,应当也会治的。
陈医师按西医规矩,问了病情,量了体温、血压,检查了身体,下楼时才对阿海说:“接生时不干净,得了产褥热,病情很重了,已有酸中毒。”
陈医师说此话时,刚好曾殿臣闻讯赶到,听了感到莫名其妙。他读过医书,认为热症应分“虚热”和“实热”,哪有“酸热”?因此他责问阿海道:“坐月子,你怎可给她吃太多的醋?”
“两码事,两码事,一时跟你们说不清。我已替她打了退热针,还要挂两瓶‘葡萄糖盐水’,但那都是对症的、暂时的,希望她能渡过难关。”陈医师简要地解释道。
阿海相信医生就跟去取药。曾老却愈感糊涂:既然用药对了症,何以又是暂时的?这也怪陈医师书呆子不会走江湖,把话说得太彻底了。可是,这些话对已有根深蒂固的中医概念的人来说,对不上号,因此难懂。
曾老是热心人,他安顿好张亲家及其儿媳,就亲自跑到俞家,恰巧俞医生出诊归来,就及时请他到阿海家。
俞医生号脉后,感到脉象脆弱,病症沉重,危在旦夕,但还是开了处方。他下楼后跟曾老耳语:“耽误了,耽误了,很可惜!”
但曾老不死心,请求道:“立即去配药,立即服用。晚饭时刻,有劳老友再辛苦一趟!”
俞医生一是看在老友恳求的分上,一是知道曾某常在此饭店小酌,这“晚饭时刻”的意思也很浅白,用不着客套。
阿海拿了两瓶药水与陈医师一道上楼。医馆一姐帮着陈医师作静脉穿刺,看到药水顺畅地滴注着,便主动留下看护。约莫过了两个多小时,才滴完两瓶共一千毫升的葡萄糖盐水。此时,依妹的热度退了许多,神志也见恢复。
晚饭前,俞老中医来复诊号脉。他见依妹的脉象与气色都明显好转,甚感诧异。在俞医生看来,产妇气血亏损,发热属虚劳之症候,治则宜调补气血,用药不出“黄荬补血汤、补中益气汤”。但依妹病情如此危急,只一服汤剂即转危为安,那是江湖郎中说说而已,他自己不以为然。美玉母亲虽然炒了好菜,酤了好酒,但俞老食之无味。凭良心说,像俞老这样的正派医生,他希望每个病人都得以起死回生。可是他行医几十年,误诊是很失面子的事,但病危的话已说出口,就难收回了,不免心里矛盾,与老友对话也语无伦次。
那个年头,虽然英国人弗来明发明了青霉素,黄氨药也已问世,但连陪都重庆也难得到此类药物,何况边远沿海的福清县?渔溪镇的名医们用葡萄糖盐水加清凉解毒中药,能救回依妹吗?老天呐!依妹芳龄才过十八呢,不能让她多活几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