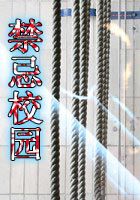自从柳葫芦把那一丈二红洋布、九个红鸡蛋和一缕红麻送到了柳大成家,不久,柳乔氏的病就不医而愈。柳葫芦对于“扑宅”一说半信半疑。柳葫芦心里虽然犯嘀咕,却也不敢跟旁人说。柳大成走时跟他再三交代,如果他说出去了,就把他送进号子里,柳大成手里有他的把柄。
老陈来搞整党,要对社里的党员挨个儿审查,重新登记造册,澄清真假党员,纯洁党的队伍。他要求群众揭发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问题。
社里的牲口病了,柳大成让柳葫芦去县里兽医站给牲口看病。这对柳葫芦来说,确实是个美差事,每天吃的是白面馍,还有补助。他知道柳大成是想糊住他的嘴。可是,老娘的银镯子丢在他手里,老娘现在还不知道,要是哪天想起来要戴,他咋说啊?他啥时候能给她老人家再打一副?想起这事儿,他心里就揪成个大疙瘩。柳大成记着他那档子事儿,他咋知道的?
从兽医站回来,柳葫芦就心神不宁。他也不敢跟我干娘说,憋在心里实在难受。他的那点破事儿实在算不了什么,可是柳大成说够判几年的。
葫芦回想着,柳大成咋会知道这事儿呢?他朦朦胧胧地回忆起来了,那天,他拿了钱出柳老歪家的大门时,看到一个人影,一闪过去了,当时他也没有在意。自柳大成说起这事儿,他确定那个人就是柳大成。对,时隔不久,柳老歪家就被撂了炸弹。估计那时,柳大成已经是地下党了。镇反时,柳大成已经是贫协主席,是他和武工队的罗政委一起审问的柳老歪。别看柳老歪平时耀武扬威,人五人六的,遇事稀屎得很,啥事儿都交代了。公判时,柳大成只说一些大家都知道的罪状,其他的事儿都装在他肚里。如果那时柳大成说出来,他会不会也得吃枪子?如此说来,柳大成还保护了他。
当时,他不知道那是啥东西。他想,顺便替人捎点货,使点脚钱,也不犯律条。再说了,黑天黑地神不知鬼不觉的,能会有啥事儿呢?锨儿他娘光知道吃了那块“刀头”,她咋就不算算账,就她给的那几文钱能买恁些肉?她要是算算账,他就会跟她如实说,要是那时说出来了,他心里也不会恁憋闷。如果眼下突然说这事儿,就好像他干了啥坏事儿瞒着她。唉,事儿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谁知柳大成还记着这档子事儿呢。
整党快结束了,要发展一批新党员,成立柳家集历史上第一届党支部。柳大成理所当然是支部书记。他将要从党小组长,被正式命名为党支部书记。柳大成早已不是“南乡柳”了,他成了柳家集真正的主人,还给自己起了个大名叫柳全成,他觉得“全”字辈儿比较适合自己,往“德”字辈儿上靠就有些过了。他就是想把自己糅进柳家集的“柳”姓中。他苦大仇深,世代赤贫,这些年又一直在组织,思想进步,水平也高,是老陈看中的人才,当然是柳家集支部书记不二的人选。老陈看不中他媳妇柳乔氏,柳乔氏骨子里有股子尖刻刁蛮,让人觉得酸凉。可是,媳妇是人家的,不能拆散人家的家庭,更不能因为媳妇影响干部使用,这世上大概没有什么完美无缺的事儿,老陈也很无奈。
老陈已经跟柳大成谈过话了,筹备召开党员大会,选举柳家集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开党员大会前,老陈左思右想,觉得少点啥。是啊,应该再加强党的力量,吸收新鲜血液。像我干娘这样的优秀分子还得吸收入党。这柳氏令可是个纯粹的共产党员的材料,思想好,又能干,跟党一心,入党条件好像比着她量身定做似的,她比真党员还党员。
可是,我干娘死活都不愿加入党组织。一丈二的红洋布,像一条毒蛇,把我干娘咬怕了。她说让她干啥都行,千万别跟公家的人挨边。老陈已经来她家好几趟了,她就是不给面见。听说柳葫芦回来了,老陈就让柳葫芦做她的思想工作。
柳葫芦一听,就跳了起来,坚决不同意她入党。老陈不死心,就耐心地做葫芦的工作,问他究竟怎么回事儿?于是,柳葫芦就忘了柳大成的交代,把柳大成搞封建迷信,要了他家一丈二红洋布的事儿说了出来。要了一丈二红洋布光破灾气还好,那年过年的时候,柳乔氏把那一丈二红洋布穿在了她身上,变成了一件贴身小棉袄。穿就穿了,还鬼摆(炫耀)了一条街,柳家集谁不知她添了一件大红小袄?那可是他娘的银镯子、嫁妆换的。锨儿他娘还没心没肺地夸柳乔氏穿上好看,有钱了她也做一件。
老陈正发愁整党没有找到什么问题呢,这下正好,逮了条大鱼,也算对区党委有了交代。那场事儿,他也在场啊,柳乔氏确实不像话。他也想借机杀杀柳乔氏的刁蛮劲儿。不过,舍了柳大成,他心里还是有些不忍。他想,革命就得有牺牲,党的队伍需要纯净,柳大成还需要继续经受革命的考验。
柳大成不但没有当上柳家集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而且还留党察看了一年。因此,柳家集历史上的第一任支书跟柳大成失之交臂,由钦定的柳大成变成了他的副手柳圈儿。柳圈儿是正宗的柳家集的柳姓,大概跟柳老歪还是一个祖宗,不过人家现在成分好啊,人很精明,还认几个字,跟柳大成也跑了几年,选他当支书谁也说不上啥。柳大成是个心性很高的人,明明是煮熟的鸭子,偏偏又飞了。他那个恼啊,回到家里把柳乔氏打了一顿。柳乔氏岂是个吃亏的主儿,跑到我干娘家里骂了一通。我干娘不知就里,自然咽不下这口气,就和柳乔氏接上火了。葫芦回家后,又把我干娘打了一顿,柳乔氏才算罢休。
自从柳大成被留党察看,柳葫芦心里就没了底气。可是嘴巴还是严实的,没有对我干娘透露只言片语。柳葫芦心里老是七上八下的,觉得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半夜常被噩梦惊醒。那时,我干娘又生了个女孩叫桂儿。她看葫芦老是一惊一乍的,以为撞了鬼,就私下里在他枕头底下放了桃木棍,点了黄表纸送鬼,可是还是不行。她知道这鬼在葫芦的心里,就可劲儿问葫芦究竟咋回事儿?是不是做了啥亏心事?是不是跟柳大成有关?柳葫芦实在撑不住了,就扇了自己的耳刮子,扇完就哭了,说他不是有意害柳大成,早知道这样就不说了。我干娘说:说就说了,事儿在那儿摆着的,咱又没有屈枉他。他能把咱咋的?柳葫芦话到嘴边,还是咽下了,他还是没把实情告诉我干娘。
那天,柳葫芦刚刚拉完犁子回家,看到区公安派出所的两个民警站在他家大门口,他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两个人问:你叫柳葫芦?
俺是。
你被逮捕了。
为啥啊?
为啥?你问谁啊?你伙同反革命柳老歪贩卖毒品,毒害人民,还不知罪?
柳葫芦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至此,他才知道,他捎的东西是大烟膏。他说:等锨儿他娘回来吧,俺跟她见个面,交代一下。
那两个人倒也通情达理,觉得他不会跑,就等我干娘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