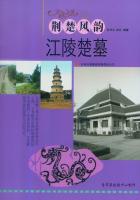国民性批判中的双重权力关系
国民性批判自古有之。
殷商征服夏人之后,将他们认为代表荒唐的笑话“杞人忧天”之类戴在杞人(夏王朝遗民)头上;周人征服殷商之后,将他们认为代表愚蠢、奸诈的“守株待兔”、“朝三暮四”等故事戴在宋人(殷商遗民)头上,以便从人格尊严和文化尊严上将他们进一步摧毁。
楚国是南蛮国家,中原的王侯公卿就将“刻舟求剑”、“画蛇添足”、“自相矛盾”、“叶公好龙”等等一系列荒诞故事戴在他们头上,嘲笑他们的弱智、愚昧,以此建立自己的正统感、优越感和高贵感。
这可以说就是国民性批判的萌芽。
秦汉以后历代士大夫张口就说“愚民”、“刁民”、“蛮民”,不辞辛劳地教化之、启蒙之,乃是这种文化战略和心态的发展。
国人常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与此相对应,国民性批判一般都是强者对弱者的卑贱化建构、歧视性描述与否定性评价。通过这种反复不断的负面言说,让弱者认清自己的弱者地位,更驯良地服务于强者即批判者的利益需求。
所以,所谓国民性批判,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所批判的内容是否真实,而在于必须通过这种言说建构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权力关系。被批判者如果企图通过改过自新、洗心革面摆脱那些被建构的劣根性,以便得到批判者的认可和赦免,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妄想。人类驯化牛的历史大约五千年,牛的克勤克俭、忠于职守已经完美得无可挑剔,可是牛永远摆脱不了那根皮鞭和那一声呵斥:孬种!这就是国民性批判的核心机密。
中国国民性批判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出现在近代被殖民、被掠夺的境遇中。西欧殖民掠夺者为西欧之外所有被掠夺、被殖民地区的居民建构了大致相同的负面形象,比如说美洲人没有灵魂,不是人;印第安人不热爱生活,不热爱劳动,喜欢集体自杀;非洲人智力低下,接近动物,很可能没有灵魂。说中国人欺骗、愚昧、奴性、邪恶、保守、迷信、没有理性,等等。说穿了就是一句话:中国人只适合像古希腊的奴隶和他们正在捕猎的非洲黑人一样为他们服役,服务于他们的利益。
西方殖民者用枪炮征服了中国,同时用这一套国民性批判话语,摧毁中国人的文化尊严,诱导中国人自觉地服务于他们的利益。欧洲国家对中国国民性的描述,是国家对国家、民族对民族的诬陷,是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整体性歧视。
中国的精英群体在漫长的失败与绝望中,全面接受了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否定性评价,而且进一步将殖民者概括的“国民性”概念发展为“国民劣根性”,并进一步将殖民者为全民族打造的这道精神枷锁完整地转嫁到了底层群体的脖子上,自己则像孙悟空的元神一样,悄悄地从这枷锁中溜走了。
由此,自古以来国民性批判中的权力关系,由一重增加到两重。西方国家为了建立和巩固他们对于中国的支配权,不断地对中国实行着整体性的国民性批判;中国的精英群体为了建立和巩固他们对于中国底层群体的支配权,不断地对中国底层群体实行着国民劣根性批判。
当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时贤决意为中国选择全盘西化的发展道路时,他们以西方殖民者的眼光、价值观和立场,对于他们与殖民者共同建构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诸般劣根性进行了狂轰滥炸式的大批判。随着批判话语的展开,批判的对象越来越具体,阶级构成越来越下移。
在梁启超笔下,国民性的缺陷主要是一种文化的缺陷,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共同拥有这些缺陷。严复主张开民智,也没有将矛头对准下层,相反,他更多地期待着上层社会迅速增强文化适应能力,在工商产业方面开创新局面。到了胡适这里,国民性问题已经有了阶层区分。他首先假设了精英人物没有这些缺陷,所以他呼吁中国应该集聚一万名这样的优秀人物,再来给有问题的中国社会及底层人群启蒙。
鲁迅是一百年来对于国民性批判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物。从命名权上来说,鲁迅也在这个领域掌握着权柄。胡适将国民性称作“罪恶”、“罪孽”,梁启超和鲁迅将国民性称作“劣根”。今天人们所谈论的“劣根性”,得益于鲁迅的强调。
梁启超在讨论中国国民性的“劣根”时,主要还是从历史、文化、地理、政治等角度,对中国国民性的生成和表现,进行了较为客观的研究和描述。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人文学术和殖民政治背景下,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性格的一次自觉体验和体认。其褒贬的色彩不是太浓,所以“劣根”在梁启超的言说中并不是中心词。
在鲁迅的国民性研究中,“劣根”一词却是核心概念。所以,后来“国民劣根性批判”几乎可以替代“国民性批判”,这种概念重点的转移,主要是以鲁迅的思想贡献为基础的。
鲁迅集中挖掘中国国民性中的负面因素,并用小说创作的方式,将这一切劣根性集中体现在一批小说人物身上。而他创作的人物中,最为生动的,激发了后代强烈的阐释激情的,都是地道的底层小人物。具体地说,鲁迅最后将中外人士进行国民劣根性批判时所揭示的一切劣根性,全都定格在阿Q、祥林嫂、闰土、七斤、华老栓等等这些最卑贱、最无助、最走投无路的底层人物身上。
鲁迅以国民劣根性批判为主题展开的一系列学术研究和小说创作,对于后鲁迅时代的知识分子理解国民劣根性、寻找进行国民劣根性批判的对象,具有十分明确的导向。
举例言之。
鲁迅所创造的承载着国民劣根性的人物形象中,最为着名的、阐释空间最大的、激发阐释激情最多的人物,无疑是阿Q。而大多数鲁迅研究者,都将阿Q看作农民群体的代表,将阿Q身上的劣根性,看作农民劣根性的集中体现。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在后鲁迅时代,国民劣根性批判的指向,越来越集中于底层人群。而鲁迅的小说创作,是这一历史趋势的奠定者。说得夸张一点,后鲁迅时代的文学创作,很大程度就是对阿Q批判的普泛的、细致的展开。
底层读书人可以通过批判阿Q的国民劣根性获得精英地位,精英读书人可以通过批判阿Q的国民劣根性巩固精英地位并强化精英的优越感。
国民劣根性批判问题,始终是一个权力问题——它是确定并巩固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权力关系的一种政治方式,虽然它以文化的名义表现出来。中国精英群体在殖民者面前,接受了失败的命运之后,将这种失败的责任归结为底层社会的愚昧、迷信、保守、邪恶,迅速地给自己规定了启蒙权、领导权。他们在殖民强权面前的失败感,迅速更换为面对阿Q、祥林嫂们进行启蒙的崇高感。他们以这种方式崛起为文化英雄和这个民族的新的领导群体。
为了维持文化英雄和领导阶级的地位,他们必须一直强化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也就是强化对于被领导阶级的卑贱化建构、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评价。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文化产品本来就是从殖民国家批发来的,所以他们与殖民国家的文化保持密切的精神联系,不断地通过强调殖民文化的正当性,来肯定自己批判的正当性。
从权力发展出人文学术及意识形态,又从人文学术和意识形态发展到权力,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过程。对于这个过程的理解,关系到我们对于国民性批判的历史文化意义的真切理解,甚至关系到我们对于当下中国政治选择和国际秩序的基本理解。
为了实现对这一切问题的深切理解,请允许我从一个家喻户晓的中国故事说起,这个故事就是刚刚提到的“自相矛盾”。
楚人卖矛者与“卖矛诱导”体系
中国古代典籍《韩非子》中一个名叫“自相矛盾”的故事,值得我们深长思之。一个商人拿起一根矛对顾客说,我这根矛呀,无坚不摧——可以穿透世界上所有的盾。
随后他又拿起一面盾对顾客说,我这面盾呀,坚不可摧,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洞穿它。
制作、销售矛的人,对于矛的知识很可能超过一般的购买者,所以,卖矛者关于矛的这句判断,在市场语境乃至于整个社会环境中,都很可能被认可为权威知识。
那个卖矛人为什么向顾客夸耀他的矛无坚不摧?他是有意追求关于矛的真理而得出的结论吗?他自己相信这条由他生产并传播的知识是真实的、正确的吗?都不是。
卖矛的人之所以这么说,唯一的动机是用这条知识引导顾客做出对他有利(而不是对顾客有利)的行为:买矛,唯一的目的是把顾客腰包的钱引导到他的腰包里。
也就是说,卖矛人之所以创造这条知识并要求顾客相信这条知识,不是为了追求真理,不是为了谋求顾客的利益。他创造这条知识,传播这条知识,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某些特殊的情景之中,他常常会绞尽脑汁地诱骗或者剥夺对方(顾客)的利益。
《韩非子》中这位卖矛者,看来是一位普通的小商贩,所以那位顾客敢于质问“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消解了无坚不摧的权威性。
但是,假如这位卖矛者不是一位普通商人,而是商汤王、周武王、楚庄王之类的人物,这位顾客还敢于这样挑战他的权威性吗?即使这位顾客斗胆提出质疑,商汤王、周武王、楚庄王之类的卖矛人还会“弗能应”吗?
很显然,如果商汤王、周武王、楚庄王之类的人物借助其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威来传播这条知识,这条知识很快就会传遍中原内外、大江南北,“楚矛”就会跟“吴钩”、“越剑”一样享誉天下,从而“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这个判断,就会作为一条权威知识,成为中国人文学术体系中不容置疑的构成因素。
就此而言,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卖矛人,包括文化人、知识人。只是每个人手里的矛各不相同。
商汤王、周武王、楚庄王宣称自己代表上苍统治万民,所以万民只要顺从天命、殷勤纳税,就可永葆福祉;犹太先知声称只有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其他种族如果不想灭亡就必须跟着他们信奉上帝,为此当然必须交上适当的份钱;亚里士多德论证奴隶天生适合服从和服役,奴隶主天生适合统治奴隶并享用奴隶创造的财富;杰弗逊强调每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是不可转让的,而印第安人却天生没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必须彻底灭绝之——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以上几条,都是我们人文学术体系中具有支柱般地位的核心知识,而那些人创造这些核心知识的时候,他们所怀揣的动机、所抱持的逻辑,跟那个卖矛人完全相同——诱导别人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近代以来成千上万以上帝的名义涌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就是这种卖矛人。
三百年前西方人卖上帝,今天西方人卖美国模式和普世价值。五百年殖民史上,西方人所出卖的价值,跟财富一直构成逆向运动。上帝流向东方的时候,东方的财富大规模流向西方;美国模式流向东方的时候,东方的财富大规模流向西方;普世价值流向东方的时候,东方的财富大规模流向西方。
征诸历史事实,商汤王、周武王、楚庄王、亚里士多德、杰弗逊、传教士都是成功的推销者,他们一生卖出了很多“矛”,不但在自己的时代得心应手,而且跨越时空,至今受到消费者(买矛者)的追捧。
那么,楚人卖矛者失败在哪里?商汤王、周武王、楚庄王、亚里士多德、杰弗逊成功在哪里?
“卖矛诱导”体系与小圈子利益
楚人卖矛者企图通过广告宣传在“自由市场”推销自己的矛,由于他的广告所传播的知识受到目标客户的质疑,他被置于尴尬境地,交易没有成功。
为了进一步探讨卖矛者交易失败的原因,本书愿意绕个弯子,也就是先放下这个话题,到遥远的时空隧道中,去揭示别人交易成功的奥秘。因为只有在成功交易的启示下,才能更好地解读卖矛人的失败交易。
交易的直接目的有两个,一是用自己的剩余产品直接交换别人的剩余产品,从而获得自己需要的消费品,在古老的实物贸易中大家都是以此为目的。值得格外强调的是,交易而来的消费品是由别人生产的即不是由自己生产的。二是以自己的剩余产品或者特意生产的商品获得财富,但这财富一般以具有特定信用背景的货币为存在形式。货币只有转化为消费品时才有价值,在特定货币的信用范围内,将货币转化为消费品时具有随心所欲的灵活性,能够交换任何由他人生产的财富,所以它广受欢迎,成为我们所熟悉的绝大多数交易行为的主要支付手段。
无论是消费品还是代表消费品的货币,都是财富,所以交易的目的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获得别人生产的财富。
在进行意在获得别人财富的交易行为时,所有人都千方百计降低自己的交易成本。对于降低交易成本的期待是没有止境的,直到零才算止境。
当一方交易成本降低为零的时候,交易性质就发生了变化,那种行为不应该再被称为交易。
所以,交易是人们获得别人财富的一种主动行为,但不是唯一行为。
以零成本获得别人财富的主动行为是什么?
一是抢劫,二是征收保护费。
原始时代,一个氏族仅与存在婚配关系和共同宗教仪式的邻近氏族保持友好关系,与所有其他氏族都是敌对关系。为了扞卫自己的采集区和狩猎区,他们就像今天的不同的狮子群体、猩猩群体一样,随时可能展开角逐和厮杀。在生产力发展到每个氏族都有剩余产品的时代,一个氏族随时都可能发动对其他氏族的抢劫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