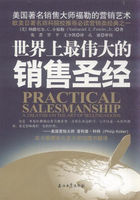1983年,我三十六岁,本命年。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灰暗、沮丧,那是一种很潮湿、闷热而又无处可逃的感觉,就如武汉的夏天一样。
从年初我就得病,胃痛,三番五次检查,就是查不出来什么毛病;医生说不排除癌症,我也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只是在想还能做些什么,比如写一份长长的遗嘱,于是就打腹稿,斟酌用句,想表达清楚自己的真实想法,但又怕给自己的亲人带来什么麻烦。
问题是:自己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并不清楚。总觉得应该说出来,其实一旦让说,也不过就那么几句话,而且这些话其实也早就说过了,只不过无人注意,也不会有人认真领会而已——当然就是领会了也不过如此。如果再说,当然仍不过如此,于是又很无奈,以致绝望。
自己变得更加多愁善感,总是默默流泪,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同情,但这又是一种弱者的同情,只不过想以自己的“同情”来抵御他人的“痛苦”而已。
这种“同情”其实很自私,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自怜,或者说是对自己的同情。
我说这些话,是因为这一年的下半年,全国性的“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运动就已经开展起来了;而我所在的华工,无疑在整个武汉地区,甚或全国范围里都属严重的;到底为了什么搞得如此严重?无非是因为黄克剑写了一些关于马克思的文章,讨论了异化、人道主义的问题,使用了据说是犯了原则性错误的一个说法:“林彪、‘四人帮搞的是假社会主义”(当时的“主流”说法应该说成是“林彪、‘四人帮反社会主义”)。
是“假”,还是“反”,或者说,用了一个“假”字,难道就开脱了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就污蔑了社会主义?
真是滑稽到了极点。
而“发现”并指出了这一点,在发言中慷慨陈词,罗列出一、二、三、四点要害,并真正显得义愤填膺的老师们,自己都在“文革”中吃了不少的苦,受了很大的罪。
我那时正在给在华工开办的哲学教师进修班授课,在哲学所内部也讲过几次个人近年的学习体会,还有每周到江汉区文化馆讲一次马哲(可得八元报酬),等等,自然也讲到了许多科学与哲学、情感与理智、宗教与信仰、历史与逻辑的关系问题,而且这种讲法本身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归入“唯心主义”范畴;但由于我是非党员,所以暂时可以置身事外。
单纯讲理论,并不知道要达到什么目的(为理论而理论); 或者,先有了某种现实的目的,然后再以理论的形式为自己的目的作出一番论证;那么我们现在到底是只讲理论,就学问而学问,还是先有了目的再作论证?这是必须反省的一个问题;而且,在为目的作论证时,必须意识到从某个前提出发,在达到合乎自己的目的的要求中,是有无数“沟壑”跨越不过去的,或者说是填充不满的。我们怎么可能一下子就从一个理论的“前提”逻辑地推出一个现实的“结果”呢?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就这样“合逻辑”地展开了。你会发现,不管讲理论的人怎么想,当理论的“热度”聚集到一定程度时,就孕育着某种爆发,就如海涅所说过的:“思想永远走在行动的前面,就像闪电永远走在雷鸣之前!”
同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切机制都原封未动,插头只是暂时拔离了插座;这与“帽子拿在手中”的道理一样,只要最高领导人想把插头插进插座,一切都会如前一样地运转起来。
这种必然性,到底是体现在理论自身,还是现实生活本身就具有这种“合逻辑”的必然性?
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而且知道问题就出在我只作理论思考上;而事实上,它并非一个理论问题。
10月13日的日记上第一次出现了“全党整风”的字样,我意识到一场新的思想运动即将开始;10月底,省委宣传工作会议召开,“清污”一词连同一些口号已经有些铺天盖地。
“Lea derscallf or wagingana ctivei deologica lstruggle, cleanupthepo llutionof bourgeo is inideo logicalan dculture”,这是我记在10月30日的日记本上的一段话,也许是从某张英文报纸上抄录下来的,总之感到问题重大。
于是,一些着名的诗人、作家纷纷讲话,谴责文艺界的“反现实主义倾向”。
11月7日,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深切感受到我们这里的一切也都在“静悄悄”中发生。
11月13日,院长不点名地批判了黄克剑,于是李其驹作为所长首先在支部会议上检讨;接着就是培训骨干,准备一次大规模的批判会议。所有这一切都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人与人之间在僵硬的笑容后面都潜藏着不可预知的你死我活。
1983:与叶秀山、邓晓芒在蒙古草原上的蒙古包里作客。
哲学所的全体会议是12月19日(星期一)召开的,在此之前,已经开了无数次会,在院工作组的直接指挥下,黄克剑在党内做了检讨,但事情并未结束,还要开全所的会议,对非党人士进行教育。那真是撕心裂肺的一天。我在事先就下工夫在《邓小平文选》中发现了邓小平也多次使用了“林彪、‘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这样的说法,但我们这里还在无休无止地批判着这句话。那一天,我声泪俱下地痛陈事情(也就是“异化”和“人道主义”这两个概念)的原委,翻出邓小平的话,引用马克思的话,怒斥学院、工作组以及所领导全力推动的这场莫名其妙的整人运动。
事情到此结束。事后,我才知道“上面”已经决定对此运动“刹车”;张平、李其驹两个人赴京探听真情,回来后再未有任何动作。
直到第二年的3月,我才知道中央有通知,说“清污”的事不要再提了;当初邓小平只是说了“不要搞精神污染”,并未说“要清除精神污染”。
又是一字之差!
圣诞节,宣良代表陈老师专程来看我,问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说,发生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当然,哭在现在,笑在以后。
那该是一种苦笑。
苦乐人生,苦笑人生,这一切,让中国人怎么可能不“恶搞”?
自那以后,我和黄克剑都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包括2007年年底在福州的相见。因为我们都知道,凡立誓忘却的事,一般来说总是忘而不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