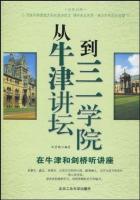综上所述,明清以来,福建省与琉球岛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因此,很早就有了划界问题。就中琉双方的史书记载而言,明代钓鱼岛应归福建福州管辖。清朝统一台湾之后,福建成立台湾府,钓鱼岛列屿此时应归台湾府管辖。此时的台湾府已经与冲绳隔海相望,双方有必要确定界限。康熙五十九年(1720),徐葆光出访琉球,在与琉球官员及学者的商榷中,确定了双方的分界。琉球方面得以正式占有台湾以东的许多小岛,但钓鱼岛列屿也正式划归中国的福建。日本吞并琉球之后,一度提出瓜分琉球的计划,未得中国政府接受,按其计划,钓鱼岛理当属于中国。而后,日本开始侵占周边岛屿,并窃占钓鱼岛。其时中国政府一直要求日本还琉球独立,没有和日本划界。台湾建省之后,福建与台湾之间未曾明确划界,但从划分原则而言,钓鱼岛应属台湾管辖。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割让台湾,不久,日本窃据钓鱼岛。因管理上的问题,日本最终将钓鱼岛划归台湾总督府管辖。1945年,日本战败,声明放弃台湾,台湾由中国政府接收,由于当时钓鱼岛归台湾管辖,所以,从法理而言,钓鱼岛已经自动回归中国。在台湾省建立以前,福建福州对钓鱼岛的管辖至少有500多年的历史,福建渔民常到钓鱼岛周边海域捕鱼,所以,钓鱼岛海域理应由中国内地与台湾共同管辖。
本文为提交2010年8月重庆纪念台湾光复与抗日战争胜利65年会议论文,后发表于《东南学术》2011年第2期。
(徐晓望,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学术与政治之间
——台湾的儒学现代发展反思
张文彪儒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曾经经历了一个稳定而普遍的发展时期。国民党当局将儒学中的一些伦理纲常作为巩固统治的思想武器,在“反共复国”纲领中杂糅进儒学思想中的伦常观念。儒学在一段时间里甚至被理解成提供意识形态选择的一种路径,同台湾当时官方哲学一起,成为台湾意识形态领域的两大思想支柱。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的儒学发展又经历了一个新的重建与复兴的机会。面对台湾社会在经历现代化以及后工业社会的大踏步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带有明确儒家文化特点的“台湾经验”,许多台湾学者在深入思考和把握传统儒家思想及战后新儒学关于儒家思想现代诠释之余,逐渐要求儒学精神进一步在台湾社会实践中发挥出其思想资源的优势。在这一过程中,儒学更多地致力于从古典儒学与现代西方各种思潮的反思中,完成从被动到自觉的思想转型。
一、传统儒学、新儒学与当代台湾社会
儒学自明代末期传入台湾以后,就一直对现实生活不曾间断地产生着文化层面的巨大影响作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台湾社会经历了由日本占领回归祖国不久,又因国民党战败盘踞台湾而导致与中国内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隔离状态。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特殊历史阶段,也并没有改变儒学与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基本上是透过两种途径:一方面是战后来自国民党当局所大力推展的反映一定统治意图的“官方儒学”,这种情形下的儒学是经过了高度选择性的诠释,主要是为支持统治的政治合法性而提供传统文化的基础。它基本上依靠当局政府的宣教渠道和明确的推广政策而得以保持自身的影响力,因此使儒学的传播具有一种严密的制度上的保证。另一方面是由没有任何官方色彩的知识分子所诠释的“民间儒学”,它完全致力于对儒家的观念体系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研究与探讨,而不把这种研究与探讨看成是传达权力阶层意志的一种特殊途径。这方面的儒学研究代表主要是台湾的新儒家,他们更多的是强调儒家的批判性。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民间儒学”在台湾社会的影响力远不如“官方儒学”。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的正相反对,至少儒学研究的这两个派系都希望从这个最传统的领域通过运用综合的诠释方法,走出全新的能够跨越经学、哲学、思想史的多元研究方向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过。
虽然“官方儒学”在台湾因为文化政策层面的缘故,一度占据着文化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其代价是由于担当着“国家政治目标”支持者的角色而不可避免地不断被工具化。尽管这种被工具化现象可能只是儒学思想在特定时空里存在和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然而也正是在这种被工具化过程中,传统儒学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观念的核心内容逐渐失去其主体性。与此同时,走融会中西思想之道路并自视为民族文化薪火传承的一线命脉的台湾新儒家,则始终自由地活跃于学术舞台之上。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作为现代新儒家第一代人物的熊十力、梁漱溟、贺麟等,他们一开始就坚持中国的未来应以先秦儒家精神为根基,进而接续宋明儒家心性义理之学,最终在吸收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基础上,谋求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地位。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人物,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张君劢等,在20世纪50年代初由大陆转移到台湾、香港等地后,也一直坚持认为儒家思想不仅是一个终极关怀的问题,而且仍然具有整合世界的意义。在他们看来,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背离,以及因为种种文化思潮的冲击影响而产生的分裂、对抗、非理性等等,都只具有主观上的意义,只是由于观念上的矛盾和混乱引起的。因此,牟宗三把自己哲学的最后取向归结为“圆教”与“圆善”,而实现这一观念的路径便是进行中西思想融会的学术工作。这种强调中西学术兼容的观点,被认为是当代台湾及海外其他新儒家区别于传统儒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如果说,这一时期的台湾新儒家学者仍然执着于在精神领域探寻或创立一种绝对圆满的思想体系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之后台湾儒学界的学术论争又有了另一种新的期许。他们开始更多地强调以深邃的、异见寻常的哲学洞见,去捕捉时代发展的内在精神与核心问题,从而将人的精神视野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一些学者开始普遍地用“思想资源”一语来表述儒家思想与现实精神生活的关系。这一点与他们的老师牟宗三、唐君毅等人的思想观点不同,在他们的老师看来,儒家所扮演的角色绝不只是“思想资源”,而是“精神世界”,因为前者是可分的、多元的,是可以经由主体的选择与发掘而表现不同的;后者则是整体的、统一的,直接与主体存在相呼应。
在这方面,台湾新一代的儒学学者不再幻想儒家的理论学说能够为现实社会的发展提供某种理想的蓝图。它更多的只能作为一种思想资源融入多元化的格局之中。也就是说,不得不正视传统儒学将注定消失于教育体制和知识学科化的现代学术体系之中的现实。这种被彻底置换了西方化学术坐标的状况,正毫无退让地限制着儒学话语的复记和观念碎片的拼接,从根本上改变了儒学的命运。这种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要求新一代儒学学者不得不具备更客观的视角,正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表现出更为鲜明的问题意识,更加着眼于思考人类在现当代社会所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而不再企求建立某种终极的判教系统和形上体系。
此外,与大陆许多文化学者一样,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台湾许多学者也把中国长期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儒家思想的政治化。这一观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似乎是一种发人深省的文化激进主义批判态度。但在中国社会经历数十年的现代发展之后,如果批判的眼光仍然停留在这一判断基础之上,就不能不说是一种过分简单和片面的思想了。况且从实际上分析,战后国民党虽然重视和维护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蒋介石本人亦在建立三民主义和儒学的联系方面不遗余力,甚至将三民主义看做是儒家道统的现代体现。但是,国民党意识形态中对儒家传统的认同,并不完全体现在国民党在台湾的各种政治设计中。事实上,儒家理想并没有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理想。在当时实际的文化政策中,我们倒不如将这种儒家化的倾向看做是台湾社会向西方政治体制接近时所提供的增强凝聚力的一种道德因素。同样的,即使是在国民党尽力强调三民主义与儒学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情况下,虽然在台湾儒学界亦培养了一些御用文人,但是,儒学在整体上所发生的转变依然不是很大的,包括一些著名的新儒家学者虽然从未与政治权势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违抗,但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不依附政治权势的特性。这也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这种客观上形成了儒学不断趋于边缘的格局下,比较消极地经常选择远避香港的置身事外的应对方式。
这么说并不等于把儒学与政治问题完全切割开来。儒学与政治社会、政治理想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命题,哪怕是到了现当代社会,儒家的“新外王学”或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仍然是台湾学术界讨论和反思当代新儒学思想建构之得失的一个焦点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一切都还是台湾学术界的玄思遐想,现实的政治社会发展一直没有进入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的视野。因此,新儒学哪怕在逻辑上与现代民主政治进行了观念性嫁接和融通,但在具体的政治和社会实践中,人们一直无法看到活生生的新儒家政治哲学的影子。新儒家政治哲学因此从根本上丧失了思想现实的内在理论能力,它还不可能为人们的政治思考提供一种直视现实的框架。这也是为什么在台湾社会民主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新儒家本来最具思想特色的政治哲学反而与现实生活渐行渐远的主要原因。
学术主张如此,个人对学术与现实政治之关系亦抱持远离的态度,这种远离或疏离的态度表现在现实政治伦理中的自我定位,即是与既得利益的统治及强势集团的淡然面对。牟宗三拒绝过蒋介石约谈的邀请。徐复观则是从现实政治中退身出来而始终与现实政治权势保持距离。他始终认为:“文化应和政治权力保持一个距离的立场”,徐复观:《徐复观杂文——看世局》,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第11页。而“决心与现实保持距离,以便能在文化思想上用点力量”。徐复观:《徐复观杂文——论中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第205页。正因为这样一种学术心态,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这些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学术著作很难用海峡两岸意识形态思想对之进行解读,他们与现实政治社会始终处于一种冷漠不契,甚或紧张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的思想成为大多数新儒家学者所共同坚持的自觉的文化与学术原则。台湾《鹅湖》杂志主编王邦雄曾经说过:当代新儒家在现实中只能采取“与官方保持距离”的立场,王邦雄:《国内哲学系所现况之检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卷第2期(1991年3月),第42页。这应该是对当代新儒家面对学术与政治关系态度的真实描述。正如台湾学者刘述先所说的:“当代新儒家是站在天下的、文化的、社会的、民间的、在野的立场,来省察、审视时代问题、担当文化患难的,他们的学问不出自政治权力系统下的意底牢结,此乃是新儒家的基本定位。此基本定位通过与现实政治的疏离感,而进一步表明他们与现实政治权势的基本关系,并使这种关系贞定下来,从而显示出界限分明而又可把握的真正的独立性。当代新儒家的这个基本定位与真正独立性,也决定了他们不凭借任何现实权势与任何外国力量来发展自己。”刘述先:《当代新儒家的自我定位与其政治学的现代展开》,《儒家思想与现代世界》,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第198~199页。
二、“内圣外王”与东亚社会发展之经验
“内圣与外王”的理念是最能揭示儒家的精神方向的,也是儒者借以安身立命和应付世事的根本法则。我们知道,传统儒学一直试图在其价值理想和现实政治之间建立起一种固定的联系。“外王”便是达到现实政治彼岸的具体体现,而当封建制度被摧毁之后,这一“外王”的现实途径被割裂了。但是,从理论上说,“内圣与外王”在儒学思想体系里的重要性却一直没有变化,人们不能离开“内圣外王”去研究儒家思想。在台湾儒学界尤其是新儒家学者看来,这一根本法则对于中华民族进一步摆脱近代以来所遭遇到的危机和困扰仍然具有不容置疑的功效。对于其中的具体思想,当代儒学提出了许多新的内容。比如关于“外王”,传统儒学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早已变得不能适应实践层面的需要。这一概念换上了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与科学,也就是“新外王”。虽然不断推进民主与科学,是中华民族现代化发展共同目标,但把此问题纳入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架构中加以阐析,却反映了台湾当代儒学学者在现代化问题上既不同于传统的守旧派,也区别于自由主义的西化派的特殊思考。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湾新儒家把这一思想理路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或称之为“返本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