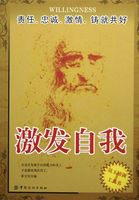不知过了多久,秦如晋睁开了眼睛。
首先,他看到了几朵金黄色的野菊花,在明亮的阳光下,冲着他灿烂地微笑。
然后,他又看见一张女性的,文静而娇好的面孔。那双明亮如秋水的眼睛在凝视着他,两片如玫瑰花瓣的唇边,挂着恬静的,喜悦的笑容。
他忽然感到了温暖,他已经有太久太久没有感到温暖了。一时间,他觉得自己依然在梦中。只不过,这场梦太美太好了,他有多久没有做过这样的好梦了!这几天,无论醒着还是睡着,他都在做噩梦,一场可怕的噩梦。他闭上了眼睛,想把梦继续做下去,如果梦让他如此温暖,他宁愿永远不再醒来。
可是,闭上了眼睛,他又陷入了一片黑暗。温暖就像长了翅膀的小鸟,一下子飞走了。他一哆嗦,连忙睁开了眼睛,于是,野菊花,阳光,少女的脸,微笑,又都出现了。那么,自己没有做梦?那么,自己是清醒的?他惊奇地向四周张望——上下铺的床,洁白的床单,洗脸架,毛巾,镜子,玩具狗熊……噢,这是女生宿舍啊!自己怎么会跑到女生宿舍来了?他吃惊极了,挣扎着,他要起来。
“别动,秦老师!”采薇慌忙喊道,“您还在出汗,着了凉,您会再感冒的!”
“再感冒?”秦如晋惊奇地说,“这么说,我已经感冒了?”
“我想,”采薇平静地说,“您已经退烧了。”
退烧?秦如晋努力思索,却根本想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发过烧。可是,他明显感到自己出了许多汗,而身体轻松了好多。那么,自己的确发过烧了!天,自己还干了些什么呢?他不知道,也想不起来了。今天早晨,在他的生命里就是一片荒原,仅有的一点点记忆,也如荒原中的风,在他头脑中倏然而过,让他无法捕捉。他怎么会到女生宿舍来了?他拼命在记忆里找寻。无奈,记忆中的这一段是个省略号,他无法从这不连贯的六个点中找寻到一些什么。可是,他不能躺在这儿了。来到女生宿舍本已荒唐,他怎么能再荒唐下去呢?他掀开被子,一跃而起,立刻,他感到一阵凉意,采薇忙递给他一块干燥的毛巾,他接过来,用它擦着身上的汗。
“拜托,”他凝视着身边这个高大而沉静的姑娘,在苦苦思索而不见成效后,他只好把疑问交给她了,“你能否告诉我,我怎么来到了这里?我……”他叹了口气,“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采薇望着面前这个人。这个几天前还在讲台上,面对一双双崇拜的眼睛潇洒地侃侃而谈的人,这个曾被学生称为“活阎王”,曾有着无比权威的人,谁能想到,现在,他会如此悲哀如此无助地看着她。她费力地咽了一口口水,斟酌地,一字一句地说:“您,您喝醉了,倒在了我们宿舍楼的旁边。我正好从那里经过,所以就把您……扶到了我的寝室里。”
“怎么,我喝醉了?”秦如晋不信任地问到。蓦的,他想起来了,他是喝了酒,一直喝到今天早上。然后,他想起了自己今天应该上班了,他这样的行政干部是必须“坐班”的。于是,他迷迷糊糊抓起了一件衣服,离开了家。恍惚中,他好象进了校门,好象对别人说了些什么,然后,然后……记忆的线又中断了。“那么,我真的喝醉了!”他自言自语。“天!”他把手指插进浓密的头发里,痛楚地,自责地说:“该死!我怎么可能喝醉?我怎么可以喝醉?”
采薇被震动了,被那强烈的痛楚与自责震动了。其实,这能怪他吗?再刚强的人,也会有自己的痛苦,也许,人越刚强,他的痛苦也就越大。等到这份痛苦大到他无法承受的时候,不麻醉自己,又能怎么办呢?他,实在不必如此自责。
“秦老师,”她想安慰他几句,“您不必这样,我们大家都知道您很难过,都理解您!”
“理解?”他猛地抬起了头,“理解什么?”
“理解您的心情,理解您的……”采薇犹豫了一下,她不想触动秦老师这根痛苦的,颤动的心弦,却一时间想不出可以替代的词语,终于脱口而出,“丧父之痛。”
“丧父之痛?”秦如晋无意识地重复着,蓦然,这几个字一下子唤醒了他灵魂深处更大的痛楚。“丧父之痛?”他又重复这几个字。突然,他把头埋进了手心里,他的手指又插进了头发中。他辗转地摇着他的头,仿佛在心头辗转地碾过一层层的记忆:苦的,酸的,辣的,涩的,咸的……他的头脑里嗡嗡然地响着各种声音,而在这种种声音的包围中,他觉得自己的心正一点点地破碎。“噢,丧父之痛,”他模糊地,惨切地说,“你不会理解,你能懂得什么!懂得什么!”
采薇有些慌了,她没有想到,自己脱口而出的这四个字,会引起秦老师那么强烈的反映。望着面前那在痛楚中挣扎的灵魂,她第一次感到,秦老师的痛苦,可能并不像所有人想象的那样简单。
“对不起,秦老师。”她歉然地说,“我,我说错了。”
秦如晋终于抬起了头,他刚刚捱过了那阵痛楚。“你没说错,”他说,“只是,你不能理解,你们大家都不能理解。没有人能理解,没有!”他瞥了一眼窗台上的课本,迅速转移了话题,“你,是中文系的?”
采薇点了点头。
“那么,”他的眼里忽然掠过一丝慌乱和恐惧,“系里都知道了?”
“不,没有人知道。我回来的时候,宿舍大门已经关上了。”
“既然这样,你又是怎么把大门打开的呢?”
采薇低下了头。“宿舍大门的钥匙是舍务老师上周给的,寝室钥匙是我私配的。”她不想隐瞒,她知道,现实是永远无法隐瞒的。
“你回寝室干什么?”
“我把课本拿错了。”
秦如晋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然后,他站起来,默默地走到窗前,凝视着那盆金黄色的野菊花,久久的,久久的不做声。采薇等待着他的处罚,可是,等来的,却只有他的沉默。
一阵急促的铃声打破了这份沉默。秦如晋猛地抬起了头。“什么铃声?”他吃惊地问。
“第一节的下课铃。”采薇回答,她的心在隐隐作痛。九十分钟就这么过去了,她终于失去了“当代文学”的考试资格。
“噢,这么长时间?那么,”秦如晋沉思着,“你第一节没课吗?”
“是的。”采薇回答得很干脆。她不想让秦老师知道,自己为了他,付出了多大代价。
“第二节呢?”
“有课,古代汉语。”
“那么,咱们走吧。”
采薇把寝室的物品简单整理了一下,把那个已经弄脏的床单泡在盆里,又匆匆换了一条新床单。然后把寝室的门,宿舍楼的门锁好。秦如晋一直在旁边看着,既没有伸手,也没有说话。可是,当采薇刚想向教室走去的时候,一直默不作声的他突然开口了:
“你说,你第一节没课,”他深深地,深深地凝视着采薇,目光一直望到她的心里,“那么,你又为什么甘愿冒着被抓住的危险,急匆匆地回宿舍取课本呢?”
采薇深吸了一口气。秦老师,您实在精明!“我……”她赶紧为自己找第二个借口,“我,我向周老师请了病假。”
“算了,不要编下去了,”秦如晋挥挥手,“你明知道,没有我的批条,周老师是不会给你假的。”
采薇不做声了,她懊悔着,自己怎么找了这么一个不高明的借口!
“告诉我,”秦如晋仍然深深地望着她,“你认为,这样做值得吗?”
“值得!”采薇轻声地,却是果断地说,“因为我别无选择。二者不可得兼,我只能舍鱼而取熊掌。”
秦如晋的身子一震,眼睛睁得大大的,嘴角微微颤抖着。突然,他猛地转过身,背对着采薇,好一会儿没有说话。
然后,他拿出一支笔和一张纸,靠在墙上写着什么。写完,他把纸条交给采薇,用命令式的口气说:“拿去,交给周老师。”
采薇低头一看,纸条上写着这样几句话:
“周老师,该生因在寝室里照顾病人,特此请假一节,请予以准假。秦如晋即日。”
实话!高明的实话!“该生”,打了这么半天交道,他竟没有问自己的名字!采薇抬起头来,这才发现秦如晋已经头也不回地走出十来步了,那蓝色的背影在秋风中显得那样单薄。“秦老师!”她忍不住喊道。
“怎么?”秦如晋回过头来,一脸的惊讶,“还有事吗?”
“天气凉了,您,多穿点衣服。”
秦如晋骤然闭上了眼睛,觉得一股热浪猛地冲进了眼眶里。“谢谢你!”他仓促地说。然后,似乎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什么,他猛地转过身,大踏步地向前走去。
采薇默默地望着他,望着他的身影越走越远。她突然觉得,这个蓝色的身影,是那样孤独,那样忧郁。而那挺直的脊背,又是那样坚定,那样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