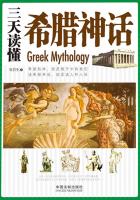佛教禅宗的《维摩诘经》说,维摩诘所住的卧室,一丈见方,但容量无限,称为“方丈”,后来就成为佛教寺院“主持”一职的专称,而道教寺观的主持,有时也称为“方丈”。后人于是把超然于世俗礼教之外称为“方外”或“世外”,那些在僧道寺观的人也就成了“方外之民”。中国古代的不少时期,对“方外之民”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专门的户籍,使之成为士、农、工、商四民之外的又一个重要的户口类别。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户口类别,“方外之民”是在佛教和道教普遍传播之后出现的。俗镀金如来立像称中国自古以来有三教,即儒教、道教和佛教。但儒家学说在汉代以后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儒士大量入仕为官,实际上已成为“方内之人”。以老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道教,是国产品,形成较早。而佛教,大概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虽然是“舶来品”,且传入较晚,但传播较广,影响超过道教。佛、道两家,遂成为中国古代“方外之民”的主体,和尚与道士,则是佛教徒和道教徒的通称,寺院和道观,则成为佛教徒和道教徒居住修行的场所。
进入寺院和道观当和尚或道士,俗称“出家”。世俗之人之所以要出家,除了宗教信仰外,很重要的一条,是逃避民间所受的苦难或其他困境。因此,战乱灾荒之时,赋役繁重之时,往往是百姓“出家”最多的时候。如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之时,唐代“安史之乱”前后,就是如此。有时,也与统治者的倡导甚至身体力行有关。如宋代的彩绘贴金释迦立像几个皇帝热衷道教,道观和道士就遍于中国。元代统治者崇尚喇嘛教,元世祖还尊喇嘛教的八思巴为国师,以后相继当帝师的还有十余人,元代喇嘛教徒就成为当时“方外之民”的主体。而清朝初年,还有顺治皇帝“出家”的传说,可见当时的社会风尚。
历代统治者中尊崇佛教并身体力行者,莫过于南朝的梁武帝。据说梁武帝是个狂热的佛教信徒,曾三次舍身佛寺当和尚,又三次被大臣用重金从寺庙赎回。他还赦免国中的死囚,让他们信佛当和尚,但又怕这些死囚们逃出寺院重新犯罪,就在这些入佛门的囚犯头上烧戒疤,以便随时识别。此后,头上烧香疤就演变为佛教徒的“入门礼”。头顶上的香疤数量不等,越多表示越虔诚。还有甚者,燃去一指或二指以表虔诚。
对于出家的僧道,多数朝代都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有专门的户口登记。如北魏时曾设道人统,后改为沙门统,总管全国寺院僧尼,规定僧民须入僧籍,并要定期查验,无籍者即令入民籍。两晋设有僧司,南朝有都邑大僧正,专管寺院事务。唐宋时在朝廷设有祠部,负责全国僧道事务,并明确规定,百姓出家,须经官府审验,符合规定者,方可发给“度牒”,即出家的正式凭证。凡有度牒者,可免除本身所应承担的赋税徭役。此外,历代的寺院和道观,大都还有自己的田产,甚至还有商业经营,其中有的是官府划拨或赏赐的,有的则是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获取的。凡入僧道籍者,除免本身赋役外,还享有其他一些世外特权,如“不拜君亲”,不依世俗之法治罪等。特别是上层僧道,在不少时期几乎是一个可以与世俗贵族分庭抗礼的特权阶层。
随着寺院、道观的发展和兴盛,需要大量从事洒扫、斋祀、农作等劳务人员。这些人员来源大体有四。一是官赐。如晋朝元康年间,重修今陕西周至县南的道教宗圣观时,官府一次就赏赐给300户,供宗圣观役使。北魏、南朝及唐宋以后,官方也不时向寺观赐户。二是官配。即发配罪犯和官奴到寺院。北魏和平年宽法生兄弟并坐像间,就曾把大批因罪没官的人口配入寺院,叫“佛图户”。三是投附。即破产农户皈依寺院,有的被度为僧民,有的则沦为依附人口,俗称“白徒”(依附道人)或“养女”(依附尼姑)。四是施舍。即寺观的信徒们以施主身份向寺观“送户”,供寺观役使。这些寺观依附人口,有的是世袭的,到隋唐时,世袭依附人口,称为“寺观部曲”。另外,还有一些逃亡到寺观的人口,冒为僧道,实为依附,叫“枝附人口”。上述种种寺观依附人口,大都脱离了当地州县户籍,但又不是正式的僧道,只是在寺观内当役使人员,地位类似奴仆。到晚唐时期,官府与菩萨交脚像寺观争夺人口,不少依附人口被“放卑为良”,重回民间,继续留在寺观的,地位略有提高,称为“常住百姓”。
除寺观上层人员外,普通僧道和依附于寺观的其他人口,社会地位和待遇都不高,但相对于民间百姓,又都算世外之人,可少受一些官府盘剥和战乱侵扰。因此,乱世之时,官府苛捐杂税繁重之时,寺观就成了良民百姓的避难所。据史载,偏安一隅的南朝萧梁,国中就有寺观2846所,僧民82700人。此外,还有大量“白徒”、“养女”,几乎占到当时天下户口的近半数。北周时有寺庙数万,史称“缁衣(即僧服)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即和尚)之徒,数过于正户”。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百姓出家者甚众。宋代和元代的一些时期,大量百姓也纷纷进入寺观,或为僧道,或为依附人口。
人口过多地进入寺观,必然减少官方正常的赋税收入,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财政困难和经济危机,于是,一些朝代又有严格限制百姓出家的法律条文。如唐律就明确规定出家为僧的具体条件和程序,凡不够条件,不合程序而出家者,称为“私入道”,本人及地方官员、寺观头目,都要处以杖刑或徒刑。但是,一遇到财政危机,官方又往往以出售“度牒”的办法来解燃眉之急。如唐代天宝年间,徐州节度使就曾奏准度人为僧,每人,只要出一点钱,即发给“度牒”。据说当地百姓趋之若鹜。北宋神宗时,遭遇饥荒,又逢河堤决口,祠部就公开卖“度牒”以供急需。以后凡遇到赈灾兴役之事,就以卖“度牒”来筹资,价格也随行就市,时高时低。这种作法,实际上等于“剜却心头肉,去补身上伤”,到头来只能进一步加剧财政危机。
法律禁不住,卖度牒又只能是饮鸩止渴,剩下来就只能是兵戎相见了。中国宗教史上的“三武之难”,就由此而来。第一次是在北魏时期,太武帝拓跋焘,采纳大臣崔浩建议,在全国大规模地禁断佛教,坑杀僧徒。第二次是在北周,周武帝宇文邕,下令在全国毁坏寺观,强迫佛教徒还俗为民。第三次是在唐朝,唐武宗大动干戈,史称天下毁寺观4600所,驱还僧道人口四五十万。这三次武力灭佛事件,都发生在佛道最兴盛之时。可见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人世间不可能有真正的“方外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