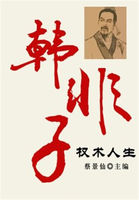转眼又是春天。
漫山遍野的桃花、油菜花盛开着,五彩缤纷,掩映在青翠欲滴的树木草丛之中。在春天和暖的阳光里,五颜六色的蝴蝶,轻盈自如地飞来飞去,组成一幅幅美丽的图案。
白石起得很早,这是他多年的习惯。
今天的他穿着洁白的衬衣,外面套着一件黑色的背心,从屋前到屋后,仔细地观察和欣赏着各种花儿开放的情景。花的颜色、神韵、形态,只有清晨这个时候,才看得真切、生动。
他相信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可以创造的。曾经是一片荒凉的梅公祠,在他们一家辛勤的汗水浇灌下,旧貌换新颜。果树生根了,展叶舒枝,含苞怒放;池塘里鱼虾自由地游动着。
绘画是他田园劳作的延伸,田园劳作是他绘画之余的最好休憩。
从1902年他40岁起,到1909年47岁止,8年间,他五出五归,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游览了陕西、北京、江西、广西、广东、江苏、河北等处的名山胜川,留下了为数众多的画卷,把祖国的山山水水、名胜古迹、草虫花卉、人情事态,一一收入于画卷之中,倾注了他对祖国、对故土、对艺术的无限眷恋之情。
他实践着恩师胡沁园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期望,拓宽了艺术视野,结识了各阶层的名人,了解了各地的民情风俗,临摹了珍藏于朋友之处的历代许多绘画珍品,因而,为他以后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几个月,他把8年游历得来的山水画稿重新画了一遍,昨晚完成了最后一幅。一共合为52幅画。他按时间的顺序,依次排列,编成了《借山画图》。这既是他8年间人生旅程后一段难忘的经历,也是他艺术实践的结晶。
种好最后一棵梅树,他回到画室,喝了杯茶,提笔给一些作品补题记。这时,胡廉石突然到来。他赶快放下手中的笔,招呼朋友坐下,用茶。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白石高兴地问。
“无事不登三宝殿。”胡廉石走到画案前,一张张地翻动着《借山画图》,看得十分仔细。
“你的画越画越好了,能不能给我画几幅?”
“当然可以?你画什么?是人物,还是山水?”
“当然是山水。”胡廉石回到座位上,“我住在石门,你就以石门的景色,给我画个《石门二十四景图》,好不好?”
他边说,边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纸上写着石门的二十四个画题。白石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日出石门、闻茑图、小桥流水……
白石把纸放在桌子上,微笑地看着胡廉石:“写的这些景致,有的我清楚,有的我就不懂了,不知指的是哪个景物。这样吧,既然画嘛,还是要实地去看看。”
胡廉石高兴地点点头:“我们定一下日期,一同去玩玩。”
游了石门之后,白石整整费去了3个月的时间,几易其稿,精心构思,终于画成了《石门二十四景图》。每一景图,在意境、技法上,各有不同,可谓各有追求,各有新意。有的以南朝梁张僧繇的“没骨图”技法,不用墨线勾勒,直接以青、绿、朱、赭等颜色,染画丘壑树石;有的则不着一色,纯用笔墨集、浓、重、淡、清并用,恣肆挥洒,淋漓毕现;有的则点苔、或渲染、或烘托,把一个石门宏伟、壮丽的河山,收入了咫尺之中。
这是他五出五归之后,第一次大规模地连续作画,比起十多年前的《南岳果图》,那是不知提高了多少倍,但他深深地感到自己的诗、词、文章造诣不深。于是,每天除作画不间歇外,几乎天天手不离卷,用功苦读诗、词,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无不下大力气。为了增加自己的艺术修养,除了作品外,对历代诗词、评论,也都收集来细心研读。
因此,在这些故友新朋中,诗、画、金石,样样精通,只有白石一人。所以,朋友黎薇荪约他来长沙的消息一传开,找他画画、刻印的不少。他原来学的是赵叔、邓石如一路。这十多年间,他对汉印作了深入研究,并将它的格局与刀法融汇到赵叔的一体中,在刀法上有了新的突破,方平正直,布局谨严,古朴耐人寻味,深得大家的赞赏。
黎薇荪趁白石到长沙,又请他刻了几方印章,白石自是倾力仔细镌刻。
晚饭后,他正仔细观赏白石的新作,门人通报,说是谭延前来拜见。黎薇荪忙放下印章,热情让座。
十多年前,谭延听了丁拔贡的一面之词,将白石刻的印章全部磨掉一事,黎薇荪是听白山亲口说的。那时,他十分同情白石。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十多年,但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从他的记忆中消失。
他与谭延有些往来,但只是淡淡的。不知为什么,谭延今天亲自登门造访,来得突然,黎薇荪一时也弄不清楚。
谭延看了桌上排着的印章,十分感兴趣地问:
“薇荪兄,这是谁刻的?”
“一位朋友。刻得怎么样?”
“不错。是不是一个叫齐璜、齐白石的人刻的?”
“正是他。延兄可能认识他呢!”黎薇荪笑了笑。“这人我未会过,怎么会认识?”谭延感到有些奇怪。
“延兄还记得十多年前丁拔贡刻的印章?”
“记得,记得。他刻的印章,我还保留着。”
“那么,那个木匠阿芝刻的印?”
“噢,你说齐纯芝刻的吧,丁拔贡说他根本不入流,我给磨了。”
“你知道这齐璜是谁吗?”黎薇荪笑笑,“他就是齐纯芝、芝木匠。”
延吃惊地“啊”了一声,沉默了好大一阵:
“想不到他还有真功夫,难怪这长沙的人都找他。”
“他是王湘绮、胡沁园的高足。你想,没有一定的艺术功力,王、胡二先生会收他为门生?”
谭延呆呆地坐着,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也不知说什么。他后悔当初不该偏听偏信,伤了白石的情面,不知如何是好。
黎薇荪看他懊悔的神色想想他平时对于金石只是喜好,并不得其中真谛,也就谅解了,把话锋一转,问:
“延兄,要我帮忙?”
“事倒是不大,就是请齐先生治几方印。不知是否方便?”
“这嘛……”黎薇荪估计他是为这事来,思索怎样回答好,“我同他谈谈。反正这个人是我朋友,生平耿介傲岸、平易近人。过去又有那一段瓜葛。我同他先谈谈,再回你信。”
“我是糊涂,有眼不识泰山。请你多多转达我的歉意。”
第二天,黎薇荪向白石说明谭延请他治印的事。
白石沉默不语,来回踱着步子,沉思着,十多年前的那桩往事,给予他的刺激实在太深了。以至于后来走过这么漫长的艺术道路,经历过无数次的磨难与欢乐,许多事随时间的推移渐渐淡忘了,唯有这事,却依然清晰地刻在他的脑海里。
不过,事物都是两面的,那一次“胯下之辱”,倒成了他学习上的一种推动力,促使他在镌刻上不断探索,融汇成百家之长,走自己的独创道路。生活中常常有许多挫折,倒成了后来的成功之途。
“他怎么知道我来了?”
“你这长沙城里闻名的金石家,他怎么不知?又听说我请来的朋友,便来找我。”黎薇荪解释说。
“他要刻什么?有具体要求吗?”白石平静了许多。他决心把过去的那段往事,作为人生的一段有趣的插曲,埋在心里。人难免会干些蠢事,明白过来了,就好了。况且自己当时还是无名小辈。如今人家找上门,不正是对自己这十多年艺术探索的一个肯定和评价吗?
黎薇荪见白石不计前嫌,很是感动:
“人家把你刻的印磨了,印谱还精心收藏着。他请你还是照着这印谱刻。”他把一本装帧得十分精美的本子,递给白石。
这以后的十多天时间里,他逐一精心地设计布局、构思,运腕走刀,细心地刻了起来。同时,把刻好的印章,盖在原来的印谱下面。两个印谱,蕴涵着一段耐人寻味的往事。
于是,长沙城里,找他刻印的,纷至沓来,使他应接不暇。回想十多年前,同样是这长沙城,找丁拔贡刻印的盛况和自己一次次被冷落的情景,同今天恰成鲜明的对比。白石有感于此,曾写下一首诗,其中一句是“姓名人识鬓如丝”。
“自古而然,人总是喜欢锦上添花的。”黎薇荪回答说。
“我倒是喜欢雪中送炭。”白石动了感情,侃侃而谈:“在艰难困厄之中,要不是有你们这些朋友相助,我哪会有今天?我这辈子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黎薇荪静静地听着,白石对人生、对友谊的见地,给了他很深的启迪,多少弄清了白石的画,为什么一扫文人画那种孤寞、冷落、凄愁的氛围,而展现出明丽、生机勃勃的基调,有一种新的生命力。
五出五归后,白山筑石山林,想在晚年潜心于绘画艺术,不想远游,何况这两年,他失去爱子、兄弟和恩师,在悲怆的心境里过着凄苦的生活,接连的生离死别伤心事,给予他的精神很大刺激。民国了,国家状况不但没有好起来,而是一天天坏下去。这几天,北京城里风声鹤唳,风传军阀又要打仗。市民惶惶不安。
一天夜里,白石从睡梦中被惊醒。他凝神屏气一听,一阵阵轻轻的敲门声来杂着郭葆生的叫唤声传入耳中。郭葆生深夜叩门,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一天,是1917年7月1日。正如白石所推测的,天将黎明时,张勋身着清朝皇服,出门登车,招呼部兵,往清宫进发,演出了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复辟丑剧。随即全国群起反抗,段祺瑞由天津带兵入京,把4000来名辫子兵打得落花流水,结束了这场闹剧。这是白石第二次进京,来了不到10天,就遇上这复辟之变,他的心境很悲凉,偌大的国土,竟放不下一张宁静的画案。他日日提心吊胆,一筹莫展。他想找一块安静的地方,潜心作画。于是,他搬到了法源寺,希望在这神圣的宝地,借得一个安定的处所,作他的画。
这个宏伟的寺庙是一座4层的、规模宏大的院落。白石住在藏经楼厢房。
白石对于这个地方倒是十分满意。这里环境清静幽雅,葱茏郁郁的古树、青青的小草和到处开放的小花,散发着幽香,给人一种沁人心脾的凉爽、轻快之感,勾起了他的诗情画意。
每天雄鸡报晓,他就披衣起床,用昨晚早已准备好了的一盆凉水,洗了一下脸,点燃了灯。在繁星照耀下的庭院里,转上两圈,凝神思索,然后回到画案前,理纸研墨,再回到床上,倚着被子,闭目凝思。
这是他羁旅作画的习惯。每每提笔之前,对于所要创作的作品,从立意、穿插、构图、设色等等,都预先思考成熟,然后信笔挥洒,一笔写成。
他的作品,名家称之达到不能增一山一石,无法减一笔一画的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他几十年艰苦磨炼的结果。
对于祖国灿烂的艺术宝库,他是极为尊重的,下了很大的苦心去学习。临摹古人名家的作品,一直贯穿于他整个艺术生活的各个方面。不管走到哪里,只要他见到一幅别有新意的画,他都想方设法去临摹,直到把它的神韵、精华掌握到手为止。
他不是一般的临摹,对于新获得的作品,他要花上两三天的时间,步不出画室,伏在画上仔细地反复观察、研究,看看人家怎样落笔、着墨、设色,怎样构图与题识。一张画,他要临三遍,这是他几十年绘画的基本功。他从来没有满足于已有的成就。
白石画荷花,50岁才开始起步。试笔的第一幅作品是《荷花翠鸟》。他不满意,嫌花、叶拘滞,梗茎呆板,没有情趣。白石经过5年的深居苦练,如今,他一反自己过去简叶疏枝的技法,向繁密方向发展。几个展开的荷叶,十多朵怒放的荷花,以及许多含苞待放的花蕾,将画面充溢得满满的,真是繁花似锦,一派生机。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来京两个多月了。白石回到故乡茹家冲,已经是十月初十日。春君和孩子避难在外,尚未回来。他的家被洗劫一空。土匪横行,兵匪一体,肆意抢掠。他几年苦心经营的花木、房屋被破坏不少,到处是一片残破、凄凉的景色,过了些日子,春君得到消息,听说他回来,才带着孩子返回茹家冲。
这一年的冬天,天气异常地寒冷。春节时,全家团聚在一起,虽然没有什么大事操办,但却因为经过这次离乱之后而能安全重逢,在清苦之中也感到十分的欣慰。
谁料到,过了元宵节不久,乡里又谣言四起,听说几个军阀又要在这一带打仗。湘潭城里,来来往往净是军队,他们凶狠残暴,见东西就抢,随时随地乱派捐征税,弄得贫苦农民苦不堪言。
一天,一位朋友,忽然三更半夜敲白石家的门,告诉他,到处传说:“这几年芝木匠发了大财,倒是个绑票的对象。”风声一天天紧了起来。附近几个村庄,稍有点像样的人家已经被绑过不少了。
听到这消息,白石无奈,只好悄悄地带着家人,匿居于紫荆山下的亲戚家里。
在这动荡、颠沛的生活中,他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饱尝了人间的苦涩。
北京回来后,他本打算潜心作品,平静地度过晚年,不与尘世来往。然而这里却没有他的容身之处。他后悔自己不该回来。但这里毕竟是生他养他的故土。父亲已经81岁高龄了,母亲也75岁了,还有妻儿家小。这许许多多骨肉亲情,怎不使他踌躇再三?
父亲、母亲看到这里的情况,希望他到北京去。春君也一再催促他快下决心。经过数次反复的商量,他决意离开他无限眷恋的家乡,离开他多年苦心经营的寄萍堂。
1919年3月初,白石决心北上,临行前,他去看了祖父、祖母的墓。头天晚上,他去看了父母,给老人留了一些钱。
老人布满皱纹、饱经风霜的脸,不断地滚下了热泪。他们知道,白石这次出门,不是暂时的出游、小住了,而是要永远地定居北京。
“这里是你的家,我们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父亲擦着眼泪,喃喃地说:“时局好了点,你要常常回来,我同你母亲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说着呜咽了起来。
母亲只是老泪纵横,哽咽无语。白石含着泪,朝着父亲、母亲拜了三拜,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夜很深了,白石才回到住处,只见春君在微弱的油灯下,做着针线活等他。
他曾经多次劝春君携着女儿同他一道去北京。但是,春君舍不得撇下家乡的父老与部分产业,情愿领着儿女,留在家里。
白石愁绪满腹,无言地坐了下来。春君也拉过一把椅子,与白石对面而坐。
“你放心走好了。我们孤儿寡女,不怕。公婆、叔叔都在,他们会照顾好的,只是你只身在外,客居异乡,举目无亲,很是不便,有一件事想同你商量一下。”她看了白石一眼。
“什么事,你尽管说好了。”
“我想给你找个配室,送到北京,好照顾你。”春君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胸有成竹地说。
白石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白石先是怔了一下,接着被春君的真挚情感所深深地感动了。
沉思了好大一阵子,白石才缓缓地回答说:“这事就不必了,我自己会照顾好自己的。”
“我考虑了好久,我无法照顾你,一定要找一个人代替我照顾你。不然我怎么放得下心呢?”春君有些激动,恳切地说:“我对于你只这一条要求,平生无他求,就这一件事了。”
“以后再商量吧。我到那里再看看。”白石不好伤她的心,宽慰地说。
这一夜,他们都没有入眠,白石对家里的生活,一一作了具体的安排。早饭后,他强抑着别离的痛苦,踏上了去北京的路。
湘潭的阳春三月,是多雨的季节。黛青色的群山,葱郁的树木,沉浸在烟雾之中。寄萍堂屋前的梨花,在细雨中怒放。
白石满怀离情别绪,在春君的相伴下,支着伞,迎着风,冒着雨,匆匆上路。道路旁,水珠顺着青青的竹叶,无声地、静静地流淌,好像是泪的交织。
在长沙住了一夜,买了张车票,他登车北去。但他的心还留在父亲、母亲和春君身边。列车昼夜不停地奔驰着,错落的群山,闪光的湖光,碧绿的田野,不断地、匆匆地从窗前闪过,他无心眺览。一种从未有过的空落、孤寂的情感,充溢着他的脑海。
到北京后,他仍然住在法源寺。安顿好了的第三天,他就在南纸店挂起了润格,卖画刻印,到了夜晚,夜深人静,他常常通宵达旦,难以入眠。只要一闭上眼睛,父母、妻儿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眼前。
藤萝花还开着吗?芭蕉的大叶已经青郁葱绿的了……这一幕幕园中小景,交织地呈现在眼前。
在郁闷、痛苦之中,他送走了夏天。
北京的四季分明,立秋之后,金风送爽,西山的丹枫如血,勾起了他对那孕育他童年艺术灵感的故乡的情思。
中秋节到了,郭葆生接他去小住三天。在那小小的、洁净的庭院里,郭葆生约了几个朋友,在树荫下摆上小几,放着瓜子、糖果、茶水之类,赏月聊天。
他们都了解白石的心境,闭口不谈有关中秋或是望月思乡之类的诗、词,以免白石触景生情,感伤怀念。但是,今晚千家万户笑声盈盈,欢度佳节,白石的心哪能不思念千里之外的亲人呢?他想起了苏轼那千古流传的名句:“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的思绪伴随着飘动的、轻纱般的浮去,飞到了那充满奇异色彩的寄萍堂。春君和孩子们也在赏月吗?父亲、母亲他们呢?
他不知在座的朋友们谈论了什么。他只静静地仰首,凝视着明月、白云,什么也没说。
那晚,他喝的酒特别多。
可能是酒精的麻醉作用,这一夜是他近半年来睡得最好的一夜。要不是有人送信来,他可能能睡到中午。
信是春君来的。他一听说,一跃而起。她告白石,给他聘定了一位配室,几天之内,她将携她一同来京,要白石准备住处成亲。
春君一片诚意,白石非常感动,忙着托人租下了几间房子。朋友们知道白石要办喜事,都来帮忙,桌椅板凳,锅盆碗筷,一一准备齐全。一天下午,陈春君带着一位年轻女子来到北京。
女子叫胡宝珠,四川丰都人。当时才18岁,出落得十分标致。白石一见,满心喜欢。当天傍晚十分,三人一同到了龙泉寺新居,在陈春君的操持下,简单地举行了成亲之事。
春君遂了自己的心愿,心里十分高兴。她把白石的起居、饮食、生活、作画、刻印等生活习惯,一一详细地告诉了她。胡宝珠默默领会,一一照春君教她的去做。
过了立冬,春君说:“这里的事安排停当了,我得早点回去。”
“也好。我同你一道回去,看看家里情况。”白石答应着,“这里的事就托付宝珠妹了。有什么急事,找一下郭葆生他们”。
三四天后,白石伴着春君,南下回到湘潭。1921年元旦,白石在自己的故土,度过了58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