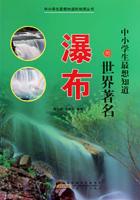有半个时辰了,就这么“巴嗒、巴嗒”地抽烟,谁也不吭,队长舅在暗处的土坯上坐,那烟火明一下的时候,才能瞅见那张黑脸子。他脸上的纹路很浅,总也油腻腻的。蹲着的时候,常让人想起老“瓮”。他生来仿佛就是蹲着过的人,无论冬夏都常披一件破袄,就势把腿遮住,蜷得很舒服。很像“瓮”,却又不笑,老爱用嘴唇舔烟纸,舔得下嘴唇黄翻,还是舔。漫长的夜,既不吭又不散,就靠这卷烟打发了。队里那一日一份的报纸连同那“国内外大事”,想必是被队干部们这样一条一条地卷烟“吸”去了。
那晚,我跟喂牲口的姥爷睡在牲口屋的麦秸窝里,曾扬头看了他们几次,很是无趣,也就不知不觉地睡去了。
尿憋醒的时候,已是下半夜了。听见蹲在暗影里的队长舅说:“上头,又布置下任务了。叫五天收完秋,工作队要检查哩……”
仍然是一片“巴嗒、巴嗒”的声响……
“东岗那百十亩红薯怕是犁不出来了。晚了,要吃‘罐饭’哩……”
吸烟声停了,舅们一脸惶惶。那愁顷刻随了烟雾漫开去,梁上的油灯显得更昏更暗。
队长舅又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声音哑哑的:“上头紧。我看,毁了算啦……”
又是半晌无语。只听秋虫儿长一声短一声叫……好一会儿,众人才应道:“中啊,中啊。三哥,你看着办吧。”
“心疼呀,我也心疼。半年的口粮……可上头催得老紧老紧……”队长舅捂了半边脸,像是牙疼。
烈子舅吭吭着说:“别家好、好说。虽说口粮不大够,都还有些门、门道。就、就、就文斗家是分、分子,成、成天哼叽……要粮,怕、怕是……”
“文斗这货真熊!”队长舅突然骂道,
“这货成天盼着摘‘帽’,老原来汇报思想……”
“汇报个熊吔!咱村就这一家分子,上头能给他摘‘帽’?”
“也不想想……”
天到了这般时候,会才开出了滋味。却又听队长舅说:“就这吧,就这吧。”说着,站起来,从屁股后摸出一串钥匙。听见草动,回头一看是我,骂声鳖儿!一把将我拽起,问:“尿?”
“尿。”早有尿憋着,又怕天黑,不敢出去,我赶忙应了。
队长舅拉我出了牲口屋,却又不让尿,四下看看,便轻手轻脚地往东走。黑咕咚咚地跟他拐了两个弯,来到了仓屋门前。他站住了,又猫样地四下瞅瞅,拿钥匙开了门上的大锁,却不推门,低声对我说:“尿吧,对着门墩尿。”
憋急,我照着门墩浇了一泡!
队长舅这才推门。好重的一扇大门,却不见响声出来。多年之后,我才琢磨出这泡尿的“科学”,知道那“经验”不是一次能总结出来的……
队长舅叫我站在门口,一个人摸黑进了屋。听得“哗啦、哗啦”的声响。一会儿工夫,他走出来了,肩上扛着一个鼓鼓的口袋。
已是三更天了,村里静悄悄的,像死了一般。天黑得像反扣的大锅,在“锅”里走着,那脚也就一高一低,一深一浅,老觉得身后有人。回到牲口屋,当干部的舅们已经把大锅支上,火已烧着,红通通地映人脸。队长舅也不搭话,把半口袋花生倒进了大锅……
朦朦胧胧地睡着,有热腾腾的一堆撒进被窝,知道是煮熟的花生,就闭着眼吃。很为知道干部们整夜开会的秘密高兴。
第二天,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三架套了牲口的大犁来到已割了秧的东坡红薯地,果真把那一季的收成犁了。大块大块的红薯从泥土里翻出来又犁进泥土。牲口默默的,赶牲口的人也默默的……
队长舅披着破袄在地头上蹲着,像坐化了的泥胎一样,目光直直地看那犁在泥浪里翻。他手里捏着的半截烟早被雨点打湿了,点烟的时候,手哆嗦了一下,有泪花含在眼里,却只默默地吸。
抢收玉米的村里人从地边走过,也只瞅上一眼,很冷漠地走开,不问。只有灰蒙蒙的天在哭……
天一黑透,村里狗便咬起来,东一阵,西一阵,伴着湿溅溅的脚步声。舅们早早就背了抓钩出去,连六十二岁的姥姥也拉我到东地来了。在那块犁过的红薯地里,黑压压的一片人!大人小孩婆娘娃子齐上阵,刨的刨,摸的摸,疯了一般。远远看去,黑黢黢的影儿乱晃,像是鬼过节。
半夜时分,我实在太困了,就壮着胆一个人先回。快要走到姥姥家的时候,倏尔瞅见队长舅在前边弓着腰走,那肩上分明扛着一个鼓鼓的大麻袋,不时有喘声出来。走着走着,却见他在戴了“分子”帽子的文斗舅门前停下,呼哧哧地放下一袋红薯,转眼不见了……
天又大亮的时候,只听文斗舅站在门口高喉咙大嗓地喊:
“可是坏良心哪!谁叫红薯背到俺家来了?俺可是头皮老薄呀!我哩娘啊,谁给我当个证见哩……”
烈子舅开门走出来:“你吆喝熊吔?!”
文斗舅脸都白了,双脚跺着喊:“烈子兄弟,我赌咒,我赌咒,要是我天打五雷击!”
烈子舅揉揉眼,让他找队长去。他吆喝的声音更大了,惹得村里人都出来看。这文斗舅四十八了,戴的自然是他死爹的“分子帽儿”,总想摘了,就怕人说他不守法。于是见人就解说,一把鼻涕一把泪。
队长舅见了,愣了一下,随又“瓮”脸一沉,二话不说,上前一脚把他跺倒,喊一声:“绑了!”
立时有人把他捆了起来,挂一串红薯在脖里,游了一条村街。他也就规规矩矩地走了……
村歌三:
往东走腿肚朝西,
吃饱饭当时不饥。
河里水清(呀个)没有鱼,
糊涂涂抹住(了个)肠眼子。
糊了一日说一日……
?选举
一天早上,村里的钟突然敲响了,急煎煎的,很闷。在村子上空淡散的炊烟似也被那震荡的气流惊扰,旋卷着随那钟声飘向田野。
汉子们迟迟地晃出来,纷纷找地方蹲了。女人敞着奶孩子的怀,抱一个又扯一个,滚蛋子往一块挤。脸面上半喜半忧。日子“磨”得太慢太慢了。太阳总是缓缓地升起,而又迟迟不落,夜很长很长,叫人过得心焦。于是想盼一点什么事体出来,且又惶惶地怕,就这么等着。
队长舅在碾盘上蹲着,俩眼熬得烂红。他去公社开会去了,会很长,一连开了七天七夜。回来就敲钟。这会儿,他正低着头卷烟,又是不停地用那厚嘴唇舔破报纸。那嘴唇已燎得焦干,总也舔不湿,就那么慢慢舔。待人齐些了,他打个哈欠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说:
“会开了七天,熬人。我眯糊了一会儿,也记不多全。‘精神,怕是这:上头、上头叫俩人一组,选个坏分子出来,上公社去开会……嗨,上头发话了,爷儿们看着办吧。’”
会场上静了,人们怔怔的。汉子们点烟来吸,互相看了,那捏烟的手竟也抖抖。女人怀里的孩子哭了。有骂声喊出来,又四下看看,忙用奶头塞住娃娃的嘴。一时无话。
村东有狗在路上撒尿,歪歪翘起一只腿,斜眼看人,一时便有尿腥飘过来,臊臊……
狗娃舅站起来,像大人似的头一梗:“老三,选上可记工分?”
话刚落音儿,众眼一起瞪过来,瞅这好不知轻重的弹子孩子。队长舅塌蒙着眼皮,似睡非睡,一张“瓮”脸苦瓜似的木着,随口应道:“记呗。”
一袋烟的功夫,人们似把一生来所做的“恶事”都在心里滤了一遍,越思量越不敢看人。于是,互相看一眼,目光刚搭界,又慌慌垂下头,再想平日所为,有几多对不住政策,不尽人意之处……似乎越想越多,扯起笸箩乱动弹,沟沟壑壑都有错。又赶忙暗暗压在心底,只怕别人瞅见。这么想着,便有汗下来,脊梁沟儿凉凉的。
又过一袋烟的功夫,仁义些的汉子,重又把头扬起,把烟碎了,闷声说:
“……我去吧。”
对面赶忙也应上一句:“欵,我去。”
“还是我去。”
“吔,我去我去。”
这谦让就更让人不能推辞。铁性汉子一拍大腿:“敲了!我去。头砍了也不过碗大一个疤!”
“兄弟,家里……情尽管放心了。”
“选举”倒也和和气气。纵然心里怯,面子还是要的,人是一张脸哪!有小肚鸡肠的女人,在众人眼前,眼翻上几翻,也不好有二话出来。渐渐,百十号人也就选出来了。
文斗舅大概是晓得厉害的。他早早地背了铺盖出来,拣最烂的衣裳穿了,鞋也多备一双,怀里还揣了一兜子凉红薯。因为“成分”本来就高,也就不参加选了,远远地坐一边等着。贤惠女人见了,纷纷回家给上路的汉子准备。一时炊烟缭绕,一片“扑嗒、扑嗒”的风箱声。撑门面的汉子也觉得有再担一缸水的必要,各自挑了水桶出来,顶天立地地走。
一顿饭工夫,舅们各自背着铺盖出来,分明都穿得厚了些。女人扯着孩子送出来,有泪在脸上流,却逗孩子笑着叫“爹”。惟有狗娃舅没有铺盖,套了他瘫在床上的老爹的长褂儿,大甩袖子,人前人后晃悠。竞迫着队长舅的屁股说:“不会不管饭吧?”
没人应,各人脸上苦苦。
于是,队长舅在前领着,拉拉溜溜一百几十号“坏分子”相跟,默默地往村外走去。不时有人回头,恋恋地看那站在村街里的女人。狗欢欢地跑着,一直跟屁股撵到村西,被谁踹了一脚,才夹着尾巴跑回来。
日光斜斜地洒在黄泥巴墙上,久也不动,像钉住了似的。一只拉“犁”的“牛牛”在黄泥巴墙上爬,仿佛有一世那么久了,却还在墙上贴着,总也爬不出那光的圈。它却一刻也没有停过,无声无息又无休无止,叫人不忍去看那韧的坚毅。秋风从田野上掠过来,携来了一阵阵秋凉,树叶一片片地落了,间或有几片随风荡去,终又飘落下来。于是,村舍越加显得破旧,连瓦屋的兽头也狰狞得很无力。村里时时有女人的哭声传出来,断断续续,伴着一两声单调的驴呜。这沉沉的、燃着淡淡秋阳的白日是何等的难熬啊!
落选的汉子背着老镢到地里来了,总也闷闷地往西看,似乎觉得亏心,只有下死力干活。那扬起的老镢一下比一下狠,一下比一下重,腰杀得低低的,弓着汗涔涔的黄脊梁,赎罪似的背那红日头……
饭时,村里哑了似的静。倏尔从田野上飘来了野野的唱,十分地欢快,响亮。仿佛那心底的笑意也随了歌声飘来,染了一村活鲜。原是选上“坏分子”的汉子们又回来了。进村就骂:
“队长那驴日的!上头叫一村选一个,他驴耳朵竟听成两人选一个!……”
于是,欢声、笑声,鸡声、狗声,响成一团。一个个像是大赦归来,各自欢欢地回家与女人温存。
泼辣辣的妗们齐伙拥出来,在村街里把队长舅按住,扒了裤子,笑骂着抬起来在碾盘上打“肉夯”!
只是不见文斗舅回来。也没人问。
村歌四:
河套里有只红蚂蚱呀,
——红蚂蚱呀;
哧愣愣飞上了(呀个)灰灰兔的家呀,
——灰灰兔的家呀;
四条脚出律律律,
——出律律律;
扔下了兔儿子夜夜喊(呀个)妈吔,
——夜夜喊(呀个)妈吔。
谷场上
谷子上场了。
汉子们在场边吸过最后一袋烟,仰脸望天儿,眼刺得芒疼。队长舅一声:“起晌。”纷纷站起,各自扛了扁担回家。瞭见带儿一般的炊烟飘来,始觉饿了,步也就更快。连山舅赤着一张红脸,烈子舅墨着一张黑脸,屁股亲亲地对着,只是不动。队长舅眯着眼儿,看看天儿,又瞅了两人的恨劲,在土里把烟拧了,说:“后晌起垛,二十分。”
烈子舅斜一眼过来:“要垛垛圆。”
连山舅也不看脸儿,对着天说:“要垛垛方。”
“——垛圆。”
“——垛方。”
“你那圆垛算个尿!”烈子舅身子一拧,满嘴喷沫。
“你那方垛算个尿!”连山舅扭身过来,头顶着头,一脸不屑。
“狗日的!百十亩谷草值起俩尿哩垛?反了我,老子不记分!”队长舅火了,一声吆喝,背手走去了。烟布袋在胯上一甩一甩。
“不记就不记吧。”连山舅嘟哝一句,依旧蹲着不动。
“尿!你那工分老子不稀罕!”烈子舅说着,刷地脱去小褂儿,露一身黑肉。两肩弓起,腰带又细细一勒,越显得膀宽,两行排骨,扇儿一般透出来,紧绷绷。就那么甩甩地到谷堆前去了,大脚一挑,一把光溜溜的桑杈顺在水里。于是两腿八字叉开,一个大字挺出去,浑然于天地之间。肩上、肋上、胯上,渐有力显出来了,阳光下,似有钢蓝在韧跳,细听听肉弦儿“蹦蹦”带音儿。接着便是“唰唰唰……”一阵风旋起,谷个子扬得飞花一般!一袋烟功夫,只见那案板似的大脊梁腻腻地亮了,一“豆”一“豆”的泛出七色光彩,酷似锻打的红铁。一时叫你觉得,纵然天塌地陷,这汉子也是不会倒的。
连山舅仍蹲在场边,悠悠地吸着旱烟。那眼似睁似闭,一任日光冉冉。一直待到烈子舅那圆垛的垛根盘起,这才慢慢站起,晃着往谷堆的西头去。走着,不经意地弯腰一捏,那桑杈便粘在手上,又抓一把熟土,轻轻在把儿上一捋,涩涩。就势下巴儿一贴,桑杈又像是粘脖子上一般。一时两手背了,那桑杈便在脖里转,初时慢,紧时呼呼生风。只见那水蛇腰软软,屁股拧拧,脑袋打花儿转,身上似无一处硬。活脱脱似那扳不倒摧不折拧不断的柳!待那屁股不拧,水蛇腰不颤,脖儿挺了,便有桑杈箭一般飞出去,准准地扎在谷捆上。人近了,软软一挑,谷个子飞走,声儿带哨儿,“嗖嗖嗖……”分东西南北向,四角四方,一个长方形的垛根定了,不用量,长长宽宽各有讲究,是一分也不会错的。看呆了你,便有生的滋滋味味从心底流出来,也想昂昂地活。日月尽管漫长,不也很有趣么?
天上飘着一片白净的云。云下有雀儿飞,一圈一圈地在场周围打旋儿,近了,又远了,扇儿一般群旋在地里,再斜斜地飞起,馋馋,却又不敢靠场……
烈子舅在东头看了,也不搭话,只重重地甩口臭唾沫,更撑死那“大”的架式,脖儿犟出两条青筋,扬起长杈,手腕子极快地翻。浑身像洗过的黑缎子一般,汗水泡软了两只大脚窝。那谷个子飞飞扬扬,一个压一个,一个摞一个。只见那圆垛一层层高,一层层高,头朝里,根朝外,茬口齐整整的,像泥抹子抹出来一般光滑。远远地看,似通天立起一根圆柱……
西边,连山舅的水蛇腰像弯弓一样弹着。把一根软软的桑杈,轻轻巧巧地挑着谷个儿,一颠一倒,垒花墙一般利落。步法也是有讲究的,前前后后,那脚印竟也一环环套;方垛也就层层相叠,角是角,棱是棱,四面墙立。
日错午了。太阳斜斜地照着,场地上晃着两条动的影儿,一时大了,一时又小,映现着力的角逐。不时有呼哧呼哧的喘声出来,那影儿却还是麻花般地拧……天静静,地也静静,寂寥的旷野只有这两个汉子。
终于,烈子舅喘一口粗气出来,挑上最后一个谷个子,给那圆垛盖齐了“垛帽儿”。累乏了,却仍然神叉着腰,扬头要唱,却又哑了。西头,连山舅那方方的垛上竟也盖起了“垛帽儿”。桑杈已扬起,只差这一弯腰一直腰……
烈子舅晃晃地站直了,两眼暴起,张开冒烟的喉咙泼口就骂:“日你那方周周——!”
连山舅举着桑杈,勉强撑起水蛇腰,也骂将过来:
“日你那圆溜溜——!”
两人先是各自站在垛上“日”,整整贴上一袋烟的工夫,待气喘稍匀了些,恨极,又一窜一窜地“日”过来。“日”一个昏天黑地!人已累翻,气实实难咽。又甩去桑杈,各自杀紧湿浸浸的腰带,双手背了,来个二牛起架,头对头顶起来!……
一只花狗叫着跑来,围着两人转了三圈,晃晃头,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