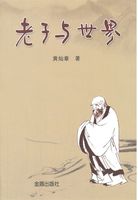在夏日的晚上看流萤,桑果慢慢饱满绽放甘甜,水面不经意间有鱼儿激起水花,月光和时间一样随清风流水过去了。然后自己就蜷在一个高楼耸立的城市里,如儿时喝米酒睡了两天两夜而醒的梦。老屋的顶破了,阳光照着卧室里那棵孤零零的树苗。有雨的时候,有湿润的雨声,在屋内要摆上大大小小的盆接漏进来的雨,倒不似现在无春秋的季节,阳光晃乱了一街的扬尘和人眼。
而早上似睡非睡的时候,正是思绪如水的时候,在尘世烦恼的自己还没有去上班,蜗居在心灵深处的另一个自己可以自由地思骋。或许这也是一种自我分裂的表征,哲学家会对自己自言自语,搞点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的思想,也正是两个“自我”矛盾的原因。音乐家会沉在自己构建的时空里,好在他们还可以演出,找几个音乐情人还是不成问题的。画画的家伙就可怜得多,有个叫自由的东西老在脑子里吵呀吵,还要看面包是否买得起,凡?高就这样一枪把自己崩了。
越是在人多的闹市,或者在繁灯照不到的某个拐角,越是觉得孤独,还有一种与孤独相处的温暖。很希望和人说话,面对面,几个好朋友,抢着说,没有顾忌,大家哈哈地笑,一如大学相聚时。每次分手,说明天见,明天就可以见到。要是现在,要说十年后见,十年就那么快地过去了。
在讲课的间隙,走过学校的后山和竹林,晚上还可以想古代书生的青灯狐影。那些不得意的读书人,在风过四壁的寒舍,希冀在书中找得颜如玉和黄金屋。就如蒲松龄那般牛衣古柳的老叟,也有漂亮的狐仙一遍遍走进他的梦里。放不下的,对于读书人,竟是那份忽远忽近,始终割舍不下的功名。于午夜之时,枕边放一本《易经》,据说可以睡得安稳。洁静轻微,是读易的乐趣。《金刚经》读了心静,在求大般若求空之前,我愿奢求哲学的大一统,有智见障也罢,是生活间的喘息也罢,有破有立也是一种乐趣。
我们渴望找个对话者,希望是个人,不是窗台的一盆仙人掌,不是一条自顾自游弋的热带鱼,不是夏日午后的一场雨。可惜这样的对话者很难找,纵然以前聊得开的也会因时间变成熟悉的陌生人。现在找朋友的途径是网络、酒吧、俱乐部,不知知心的能有几个。古人去的地方叫青楼,文化人尤其喜欢。这帮压抑的人哪,写的诗不好却希望有人能唱,三妻四妾还觉得不够。可以想象当苏小小这样年轻的、风华绝代的、十分懂诗的小美女出现时,苏东坡般这班老杆子的心是多么激动呀。对话者,美丽的对话者,想想都要在梦中笑醒。
或许我们还可以自己创造自己的对话者。比如曾国藩、傅雷,他们是写过家书的。曾国藩教育“立功、立德、立言”。傅雷花大力气把傅聪往音乐的路上引,不知道他们的孩子是否真正快乐。钱锺书也是给阿媛写过家书的,愧疚因为乱世没有把阿媛培养成一个优秀的人。可是我想,只要子女理解父母,心存感恩之意,她就是快乐的吧。
如果找不到自己的对话者,就和自己的心灵对话吧,那是寂寞的快乐。秘藏于全宇宙中的一宝,乃是人的自性,或心灵。提着灯笼走向佛殿深处,把山门掩上,黑夜中点亮的灯光就映出了佛光殿影。而对于修行者而言,无论身在何处,无论世事变幻,追求宁静其实也很容易,把自己的心灯拧亮就行了。“人人都有灵山塔”,修行是不拘泥于形式而在于自己是否主动的。
世人的追逐,入我相、人相、众生相、寿相四相,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相若。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友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使人背着蜗牛的壳,一步步往上爬,低头看见的是欲望不是内心,到达的是枝丫不是高峰。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生蒙蔽心镜之尘,我心常擦拭,那根拂尘竟无处可寻了。
凡?高的《向日葵》是内心激情的投影,《渔歌唱晚》是道者的逍遥,白乐天的《琵琶行》是沧桑过后欲说还休的吟唱。寒山和尚掩上山门,任那钟声随波逐流而去。牛顿在苹果树下静坐,郑板桥守着红薯烤炉。我愿行过小街,买一串山楂,在酸甜的咀嚼里再一次拧亮一盏青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