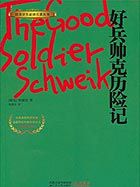半夜时分,一场冷雨把飞镖乔姐浇醒。伤口被生雨一淋,象刀割一般地疼痛,左边的腿子和胳膊,有一种烧心的灼热感。唯独有了疼痛和知觉,她才意识到自己没有死,而且四肢还属于她,并没有丢掉什么。一种生的欢欣涌上心头,她仰起脸,让雨水湿润她干裂的嘴唇,流进象烟筒烘烘冒火的喉管。她蓦地想起了白天的经历:轰响的摩托,飞鸣的枪弹,和她胯下的坐骑……
“那匹把我从阎罗殿驮出来的枣红马哪儿去了呢?”她下意识地伸出手在黑暗中乱摸。地上铺着层厚棉垫一般松软滑溜的松针,雨水在松针下潺潺地流淌。是个斜坡。她的手触到了僵硬的毛皮。那是枣红马!是她的恩人,朋友!她想站起来朝朋友扑去,然而左腿不听使唤,一个趔趄,身子沉重地栽倒在朋友的肚皮上。朋友早死了,毛皮上结着血痂。她抚着朋友的鬃毛,脑袋和长长的脸,她流泪了……
她两手抓扒着松针,把斜坡上紫红色的松针——凭经验她知道是紫红色的,一把一把扒过来,掩埋了她的朋友。冷雨渐渐停歇了,夜空中露出一颗又一颗星星,似少女羞涩的眼睛,一眨一眨的。林中透进一片淡蓝色的静谧的月光,好象梦幻中的幽冥世界,她陡然感到一阵忍耐不住的寒冷和饥饿。还是早晨在云梦江子那儿吃过东西,身上本来就只穿一单一夹两层薄薄的衣服,现在被雨水湿透,山林里寒气加重,身子里里外外都仿佛有无数牙齿在咬嚼她……为了找到点什么吃的,找到个避避夜风的岩穴,她必须尽快离开这地方。左轮手枪,还在她腰带上的枪套里,那支从“黑乌鸦”伪兵手里夺来的“歪把子”呢?哦,甩到了枣红马的那一边。她攀着树干站立起来,一步一挪挨过去,从地上抓起那支“歪把子”长枪。现在“歪把子”成了她的拐杖。她最后一次深情地望了一眼朋友火红的坟茔,拄着“歪把子”一跛一跛朝坡岭上走去。
松树林子没有了,前面的茅草和灌木丛中,不时有小野兽嗖地一声,象蛇一般窜了过去。落了叶的高大杂树林子上,不知名的夜鸟发出凄厉的惨叫声。她实在走不动了,便把“歪把子”斜挎在左膀子上,用右腿右手着地往前爬行。爬得浑身发热,也没碰上能够果腹的野果子或野菜。茅草枯黄,灌木的叶片象老妇干瘪的乳房,没有一点浆汁。月亮倒象个刚出锅的油饼,可惜高高地挂在天上,渐渐被蚌壳色的云块吞噬。眼看就要爬上山顶,不知是因为饥饿还是伤痛,她又一次昏迷过去……
“黑乌鸦”伪兵和头戴钢盔的鬼子,趁着月色摸上山来了。带路的是城陵矶有名的土匪汉奸任屠夫,这个杀猪佬出身的地头蛇,她在城陵矶街头跟师傅卖艺的时候,就跟他交过手,烧成灰也认识。桂花园和下街妓院里所有的女子,几乎都被他坑害过,他还兼做贩卖女子的生意。这家伙今晚带着东洋鬼子搜山来了?专为抓她而来?茅草山坡的那一边,传出一片野人般的怪笑和凄惨的哭叫声。她不知道,在这茅封草长的山坡上,同时还躲藏着那么多从小镇上逃出来的女子。躲在半山坡上的,一个一个都被“黑乌鸦”和鬼子抓住了。有的就在草丛里被鬼子糟踏,有的被伪兵剥掉衣裤,赤条条绑在树干上,再让鬼子去轮番蹂躏……有一个渔家女子打扮的大嫂,被两个红毛野人般呷呷疯笑的鬼子追上山顶来了。她想逃跑,又想去救助那个大嫂,刚从草丛里站起来,就被两个鬼子中的一个扑倒在地上。她和那个大嫂在草丛里跟鬼子翻滚,搏斗,茅草压平了一大片。终于她气力不支,浑身骨头象散了架,衣裤被豺狼的爪子抓破,撕碎。她象掉进了冰窟窿一样打着寒战,胸脯上象压了座大山,窒息,气闷。不知在愤怒、耻辱的地狱中熬煎了多长时间,魔鬼的力气渐渐衰竭了,她反扑过来,用双手紧紧掐住了魔鬼的脖子。魔鬼在她的胯下挣扎,她拚命掐着,掐着,两条胳膊仿佛就要断裂……
“快!收拾掉快走!”那个大嫂搬了块大石头砸在鬼子额头上,拉住她的手,一同朝寂静无人的山坡另一边冲去。
跑呵,跑呵,跑呵……
她的左腿断掉了,不知落到了什么地方。
她栽倒在地上。渔家大嫂背着她继续朝前跑,翻过一座小山,又是一座小山……
渔家大嫂赤裸裸的,她也赤裸裸的。滑溜溜的汗水,使她和她的身子象泥鳅。大嫂反手端着她的光腚,她还是一个劲往下沉。
“你是谁?”
“叫我铁篙嫂吧,渔家人……”
“我们往哪去?”
“下湖打鬼子,报仇!”
“打得赢鬼子?”
“要集合受害的姐妹,先拉支队伍……”
跑呵跑,跑到山脚下,跑到湖岸边。湖边有条船,船上已经有从山上逃出来的另几个姐妹。铁篙嫂把她送进船舱,解下缆子便开船。鬼子和伪兵追到湖岸边来了。风篷哗啦啦升了上去,风帆一鼓,船往黑漆漆的湖面上飞去,气得鬼子伪兵乱放枪……
枪声听不到了,风越刮越大,呼呜呜——呼呜呜——风在耳边发出野牛般的吼叫。快船飞过君山,飞出洞庭湖,在高山大海的上空飞过。船上的姐妹们多么欢快呵!彩云从她们船边飘过去,越来越多的姐妹们驾着彩云集合到她们的船上。船上挤着几十人几百人。刚上船的姐妹满身伤痕,有的没有脑袋,乳头上长着眼睛,肚脐愤怒地说话,用手指着船底下——那里是岳阳城,城陵矶,长江大河,作恶多端的鬼子伪兵象米粒般细小。她们掷去飞镖,飞镖象闪电一样,而且要击中哪个鬼子,就能击中哪个鬼子。她们呼喊着,叫嚷着,天风刮得比洞庭湖的风暴还猛,船在黑暗中触着一座高山,船底轰隆一声象牛口鞭爆炸,炸成了碎片。她抱住一块破碎的船板往下沉,沉向黑暗的深渊,沉人阎罗地狱般的岩穴……
在半昏半醒似梦非梦的状态中挣扎了又挣扎,飞镖乔姐才渐渐清醒过来。清醒了,又还在痴痴地寻找她自己:“我还活着吗?”她想,“我在什么地方呢?”从那个悠长可怕的噩梦开始——她被鬼子糟踏,跟铁篙嫂等姐妹们下湖拉队伍打鬼子,己经过去三四个年头了。从混进岳阳城谋杀谷野次郎,单枪匹马摆脱鬼子摩托队的追击包围到现在,又过去了多少日子呢?她记得最后一次失去知觉,是在天将破晓就要爬上山顶的时候。现在天已经大亮了,她还躺在坡岭上吗?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撑开异常沉重的眼皮。
她惊讶地发现:真如梦境中经历的那样,现在她躺在一个阎罗地狱般的岩洞里。一明一灭的火光映照着洞内的岩壁岩顶,嶙嶙峋峋的怪石巉岩,石钟石乳,在暗影里怒月圆睁,张牙舞爪,如无数牛头马面,恶鬼判官包围着她。她身子下面垫着厚厚的干草,散发出一股枯茅草的清香。胸脯上盖着一床薄棉被,周身暖洋洋的,昏迷前的那种难以忍受的寒冷伤痛感消逝了,她万分诧异地侧转过脸,微微支撑起上半截身子。
岩洞中央生着一堆火,火堆旁边有一男一女。女的象个黑皮肤的观音,盘腿坐在干草上,一动不动,痴痴呆呆。男的最多二十六七岁,一副水乡猎人的打扮,腰上缠着围腰布,额头上盘着俗称“三丈三”的青土布头巾。他那被火光烤得红通通的英俊脸庞,略带几分匪气的眉和眼,在头巾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有神。那家伙正在火堆上烤着什么野物,一股令人垂涎的肉香弥漫过来,使飞镖乔姐感到患绞肠痧般的饥饿。那青年撕了一块烤得油滴滴的兽肉,递给盘坐着的“黑观音”,自己便狼吞虎咽吃起来了。那咬嚼的声响和浓郁的肉香,把飞镖乔姐折磨得忍无可忍。她蓦地伸出手臂呼喊一声:
“给我吃!”
嚼肉的青年惊得一跳,转过身,来到飞镖乔姐躺着的岩洞角落,见受伤的女子瞪着饥渴的眼睛,欠身斜倚在干草上,连忙跪了下去,一只手挽住姑娘的后颈脖,高兴地说:
“你醒过来了?真险呵,昏睡了几天几夜,还以为你……。”
“给我吃!”她瞅着他手里那块油腻腻的熟肉,喉咙里伸出了无数只手。
“不行!”捏着肉的手赶快一缩,他冲火堆旁的黑观音叫道:“哑巴,把稀粥端来。”
黑观音端着茶垢斑驳的搪瓷缸过来,青年将吃剩的那块野兽肉衔在嘴里,腾出手接过搪瓷缸,为半靠在他胸前的姑娘喂稀粥。稀粥不凉不热,飞镖乔姐咕嘟咕嘟几大口就喝光了。强烈的食欲“方兴未艾”,她出其不意,伸右手从青年嘴里夺过那块烤肉,毫不客气地大嚼特嚼起来。
那青年乐呵呵大笑不止:
“慢点吃,慢点吃,你几天没吃东西了,别噎着……”
愁眉苦脸的黑观音也露出了一丝丝笑容。
飞镖乔姐吃过那块麂子肉——凭味道她能分辨出来,浑身有了力气,便坐直身子,猛地推了带几分匪气的青年一把,直言快语地问道:
“你是湖上的‘黑风’吗?”“黑风”本是洞庭湖上最有名的湖匪头子卜元吉的外号,后来成了对汉流土匪的共同称呼。
“黑风?哈哈,”那青年粗野地笑道,“我要是黑风,就要把你抢去当压寨夫人了!”
“那你是什么人?”
“看不出吗?”那青年拍拍结实的腿子,站了起来。
“湖上一个打猎的,专猎大雁,野鸭子。当然,有时也碰到什么打什么。”
飞镖乔姐挪了挪大腿,发现受伤的左腿不再麻木,也不再疼痛了。她试着站了起来,想往火堆边走去。走了两步,腰一闪,差点栽倒。青年猎人连忙扶住她,讥俏地说:
“你这‘女匪’,太性急了,枪伤那么厉害,就想走路?”
“女匪?我是什么女匪?”她倚在他身子上,一步步朝火堆挪去。
“你不是游击女匪,怎么拖枪打仗?”
“那我的家伙呢?”她想起了枪套里的左轮和歪把子。
“放心。”年轻猎人把她搀到火堆边,侍候她在厚厚的干草上坐下,“你那歪把子,左轮,只打得两脚兽,打不了野鸭子,我不会吃黑。”说着,他把长枪短枪一齐从干草堆里翻出来,交还给姑娘。
黑观音往火堆里添上一把干树枝,将熄的篝火又熊熊燃烧了,腾起高高的火焰,在似乎高不见顶宽不见边的岩洞里,照亮了圆盘似的一片地方。
飞镖乔姐抚摸着枪套和歪把子,无意中发现她自己穿了一条可笑的蛮裆裤,而且左腿上也缠了绷带。她侧过头瞅着青年猎人,感激地说:
“是你把我从山坡上背到这个岩洞里的?”
“那天我在几十里外的大山里巡猎,远远看到你,还以为是被猎户打死的一头野猪哩。”青年猎人风趣地说道,“走拢一看,原来是个漂漂亮亮的姑娘,只是被枪子儿打得血糊糊的,伤口都化脓长蛆了。我一探你的鼻子,还有一丝丝气。刚把你抱起来,就听得山下哇哩哇啦,是日本鬼子搜山来了。我管不了三七二十一,背起你提了歪把子就没命地跑。一气跑了几十里没歇脚……幸得你还没有野猪重,要不就把我压死了……”
“你叫什么名字?”她对幽默而又豪爽的猎人感到了极大兴趣。
“你就叫我‘锅盆’吧,”猎人顺手抓了把青草野菜,放在手心里拣着,“打烂了‘锅盆碗碟’,如今一副肩膀拾张嘴—只剩下个吃饭的家伙。”
“你叫‘郭鹏’?”
“郭鹏?嘿嘿,你就叫我郭鹏吧,横竖名字只是一个人的符号……”从此便叫郭鹏的青年猎人,拣去青草野菜中的杂屑砂土,塞进嘴里象牛反当一般咀嚼着。
“她是你妻子?”飞镖乔姐瞅着那个盘坐一旁,一声不吭的黑观音,冲郭鹏向。
郭鹏满嘴鼓胀地嚼着青草,流着青汁,连连摇头咕哝道:
“唔,不不不……”
“呸”地一声,他把满口青汁草渣吐在手心里,接着说:“她是哑巴,前不久的晚上,我在湖边上救起来的,也不知是她家的船翻了,还是——横竖哑巴吃黄连——她有苦说不出!”
“啊,多可怜的姐妹……”飞镖乔姐瞅着木木的哑女,长长地喟叹一声。
郭鹏口里咀嚼的原来是治枪伤的草药,他一口接一口嚼了满满一搪瓷缸。然后,要哑女帮忙,把飞镖乔姐的左边裤管退下,他亲自把姑娘大腿上的绑带小心翼翼地解开,把干得象野菜饼的草药揭掉,取过酒葫芦,从棉外衣上抠出一点棉花,蘸着酒在伤口上揩抹消毒。姑娘的伤口已经长出白嫩红润的新肉。他揩抹得她痒痒的,她吸溜着气,红了脸。红了脸,他便调皮地问她:
“现在该我问问你了。”新草药敷了上去,“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乔——”她想起开始为搪塞云梦江子时取的名字,“你就叫我乔葳吧,乔装打扮的乔……”
“你就是乔姐——飞镖乔姐?!”郭鹏喜出望外地呼喊,拍了拍乔葳的大腿,忘了他在给她换药。
“不——”她没弄清郭鹏是不是真正的猎人,还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身分。
郭鹏的眼神里流露出几分失望的神色。他给她的大腿和胳膊的伤口都换过药,便提着猎枪走出岩洞了。
岩洞的洞口拐了两道弯,在洞子里面根本看不到洞外的光线,也不知道日出日落,昼夜交替。飞镖乔姐在岩洞里不知道又躺了多少个昼夜,只能从换药的次数来估摸时日。每隔一定的时候,郭鹏便提着猎枪出去了,好久好久不见转来。转来的时候,照例带着草药和少量的野味。她怀疑他不是真正的猎人——猎人不会只狩猎两三餐的野物而毫不积蓄。从他每次回来鞋帮上带的不同的泥土草屑,她分析他到过很远的地方,仿佛在寻找什么。他在寻找什么呢?而且她觉得哑女也不象真正的哑巴,仿佛是故意装成哑巴留在岩洞里监视她的。一想到郭鹏听到她名叫乔葳,就迫不及待地问她是不是“飞镖乔姐”,她突然警觉起来。谋杀了谷野次郎这个日军驻岳司令官,鬼子不会不四处悬赏捉拿她。倘若被狡猾的汉奸或一个没骨头的汉流土匪认出她是飞镖乔姐,那就太危险了。好在她的腿伤似乎完全恢复了,在岩洞里走来走去已不当一回事。她趁哑女坐在火堆旁打瞌睡,悄悄挂上左轮,背起歪把子,朝岩洞外面溜了出去。
岩洞外面正是浓雾弥漫的早晨,几十步外便白茫茫一片浑沌,什么也看不见。察看近处的落叶林木,峭壁悬崖,她知道这是在一座大山的悬崖之上。峭壁上有条弯曲的“魔子路”通向山顶。她攀沿着枯草树蔸朝山顶爬去,越往上雾气越稀薄。她对这地方好生熟悉。走到芙蓉花瓣似的峰顶,她果然认出这就是麻布大山中的芙蓉峰!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麻布大山在岳阳城南三十华里的洞庭湖畔,这里四面群山环绕,峡谷幽深,林荫蔽日,风景清丽。山中名胜东风湖、响风窝、木鱼山、罗汉桥、不冰池、莲花井、犀月陵、象鼻嘴,号称“洞天八景”。芙蓉峰头有座麻布大仙庙,自古香火旺盛,游人颇多。相传古时有个贩麻布的客商,船载麻布自湘江入洞庭湖,遇大风到此泊舟登山,上至芙蓉峰,遇见两位银须飘拂的长者坐在大青石板上对弈,客商站在一旁观看。既久,肚中饥饿,仍不忍离去。这时,长者中一人从腰间掏出一颗红枣,用手劈成两半,一半自食,一半递给客商,并不言语。客商吃下半颗红枣,不再饥饿,一直等到两位长者棋终弈结,才循原路下山。寻到泊船的地方,却不见船的踪影,四周风物也有很大改变。经询问湖边渔人,得到的答复是:数百年前,有条满载麻布的商船停泊在这里,因船主不知去向,麻布和船板就烂在这里,不知浸烂多少年了,如今这湖汉就叫“烂船湾”。麻布客商猛然省悟:“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他复登上芙蓉峰,不再下山,从此成了麻布大仙。
岳阳沦陷以后,麻布大山因介于日军占驻的岳阳城和新墙河前沿阵地之间,是块真空地带。小鬼子做梦也没想到在他们眼皮底下,还有这么一个“封闭”的世外桃源。这里便成了飞镖乔姐的“飞镖队”在湖畔的秘密据点。她们从这里袭击铁路公路,骚扰敌人炮楼驻点,进退灵活,神鬼莫知。后来汉奸任屠夫象条野狗嗅到飞镖队的气息,把鬼子伪兵带进麻布大山,血洗了“八大洞天”,焚毁了驻扎飞镖队队部的麻布大仙庙。那场血与火的战斗,已经过去半年多了,现在飞镖乔姐重新登上芙蓉峰顶,望着被烧毁的庙址,断壁残砖上的血痕,她仿佛又看见姐妹们用手榴弹在阻击敌人,用刺刀跟鬼子肉搏;听见渐渐下沉在林莽中的雾霭里,似乎又传来震天的枪炮声,姐妹们的喊杀声……
叭!叭!叭!……
雾霭中真的又传来紧迫的枪声。“难道伪装成猎人的郭鹏,是又一个任屠夫?是他带领鬼子到岩洞里抓我来了?”仔细一想,又觉得郭鹏不象那种人。要拿她去邀功请赏,在她腿伤未愈之时不是易如反掌吗?他救了她,为的弄个好价钱出卖她吗?没时间去推究了,她手中虽有枪但无一颗子弹,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仗着山路谙熟,她朝烂船湾奔去!
后面哑女紧紧地跟上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