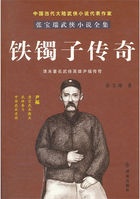湘北山区的古道上,一匹火焰似的枣红马,象一团火球,一颗流星狂奔疾驰而来。钉了铁掌子的马蹄,敲打在高低不平的古道石板上,得得得得,如飓风刮来的一泼暴雨。马背上没有鞍鞯,身穿日本和服的中国姑娘,光凭两条腿夹住马肚子,还不时回过头,用那支日本左轮手枪向后面射击!
后面十几辆日军宪兵的摩托,嗡嗡嗡油门加到了最大档,紧追不舍。乒乒乓乓的枪声似炒爆花豆,带着咝咝哨音的流弹,从马背的两侧和姑娘的头顶飞过。山坡上的松树枝断丫裂,松针纷纷坠落,一只只寒鸦哀鸣着,象黑箭向山外射去。荒凉幽寂的山谷,骤然被轰隆隆的摩托车,枪弹声,马蹄声,搅得翻天复地,仿佛有千军万马在这里鏖战!
在中国人祖祖辈辈的脚板踏出深陷着脚窝的青石古道上,摩托的颠簸摇晃比奔马还要剧烈,难于发挥威力。眼看快要追上的摩托,又拉开了一段距离。中国姑娘两腿象马鞭紧紧抽打着马肚子,身子象水蛭“吸”在马背上,人和马浑然一体,躲过飞蝗也似的流弹,冲上了一座山坳。山坳那边是开阔的平原,一条闪烁着波光的河流,如弯弯曲曲的白练横陈在前面。下山去到了开阔地只有死路一条。回头之间,猛见左胳膊挂了花,血流如注!包扎没有时间,不包扎血流不止也很危险。慌乱间姑娘拨转马头,沿山梁上的一条茅封草长的小径,朝林莽中落荒而去……
这个身穿和服的中国姑娘,便是名扬八百里洞庭的抗日女游击队队长“飞镖乔姐”。她化装成渔女潜入岳阳城,原想刺杀吃人魔鬼谷野次郎,结果却误杀了谷野的保镖而身陷魔窟。幸而得到日本军妓云梦江子的帮助,穿上和服,再次乔装打扮,才脱离险境。在康王落马桥哨卡,撞上巡哨的日本宪兵,她不得不开枪击毙拦路的敌兵而暴露了身分。近午时分,便有一支宪兵摩托队跟踪追击盯住她,象条毒蛇紧紧咬住不放。她钻幽谷越丘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摆脱“尾巴”,眼下已是日头落山时分,一整天马未进料人没下地,饥肠辘辘,人困马乏,人汗湿透了衣衫,马汗渍湿了皮毛。在树林深处一块草地勒住马,跳下马背,她的五腑六脏仿佛被烈火烧枯了,喉头似乎冒出一股焦烟,嘴唇干裂了血口。马停下来并不啃草,找了个积水坑埋下头去喝水。她跟马分享了几捧带着土腥味的积水,退下左胳膊的袖筒,扯下和服的垂带包扎伤口。子弹穿过左胳膊外侧的三角肌,幸得没击碎骨头。她手口并用刚刚扎紧伤口,树林里猛地又响起嗡嗡嗡的摩托车声。她知道敌人沿着山径小路追进树林来了,顾不得喝足水的枣红马刚啃了几把草,便把左边的袖筒往腰上一挽,又跳上马背,两腿一夹,缰绳一抖,继续朝前面的树林奔去。山梁的前面已是缓坡,树林突然低矮下去,透过树梢可见山下又是开阔的旷野。这时从她的后面和左面都传来呼啸的摩托车声,俨然整座山林都被追击的摩托车队包围了。后退决无生路,她只得纵马由缰朝缓坡下冲去!
冲出最后一片树林,那条绕山脚而来的青石板古道又出现在眼前。糟了,古道上的摩托车队离她不到一箭之遥,她眼疾手快连发几枪,前面一辆摩托撞着山墈,人仰车翻横在路上。然而山坡上的摩托象疯狗猛冲下来。子弹又在她头顶上呼叫。她只得横下一条心,策马朝伸向平原的古道奔去。古道突然变成了宽阔平坦的土路,在这样的路上,即使是关云长的赤兔马,也是跑不过机动车的。后面的车队越追越近,乱飞乱窜的子弹又擦伤了她的什么地方,她只觉得什么地方烙铁烫了一般一阵灼热,随后便粘糊糊的。她顾不了包扎伤口,顾不上回头看,死死揪住马鬃,紧趴在马背上,不使自己坠落下来。烈马狂奔冲过一道沙丘,突然一条宽阔的大河横在眼前!
这就是她在山坳上看到的那条曲折长河。人冬水枯,河心里架着一座矮塌塌的木桥。木桥两头设有岗亭。她的马刚要冲上木桥,从岗亭里冲出四五个身穿黑制服,手端“歪把子”的“黑乌鸦”伪兵,一齐把她拦住!面对一排明晃晃的刺刀,枣红马长啸一声,猛地竖立起来,几乎把她甩下马背。她想:“完了!”定定神急着要开枪,“左轮”里却没有了子弹。那几个“黑乌鸦”大概看清她是个女人,而且身穿和服,一时摸头不知脑地愣住了。趁烈马横过身子前腿落地,她一把夺过一名伪兵手里的“歪把子”,一梭子撂倒了两个“黑乌鸦”,侧过身来对付已近在咫尺的摩托上的日本宪兵。前面的摩托在河滩上横七竖八停住了,有的鬼子还跳下车哇啦哇啦朝岗亭奔来。他们预料保安队一定会帮皇军活促住“逃犯”,却不想迎着他们的是一梭原子弹。
被子弹的呼啸激疯了的骏马,载着飞镖乔姐沿河滩朝下游奔去。日军摩托车队拉开成扇面在沙滩上继续追赶。摩托在沙滩上无法施展威力,被拚命疾驰的疯马甩开了一段距离。但是,现在的子弹从多角度集中于一个目标,飞镖乔姐再也无力还击了。她的一条腿已经麻木,挽在腰上的袖筒已经松散,张满了风的和服翻飞上来,卷在右胳膊上象面旗帜呼啦啦飘扬。她听得见流弹撕裂布面的声音。她干脆抬起右胳膊把破碎的“旗帜”甩脱,一心一意横枪夹腿伏在马背上,信马狂奔,把命交付给胯下通灵的坐骑!
日头早已落山,血红的天空,变成一片桔黄,渐渐黯淡,凝重,辽阔的河滩旷野缓缓升腾起一层迷茫的暮霭。万千水鸭子被枪声惊起,在迷茫的暮色中象蝙蝠乱飞乱窜。一座黑魆魆的山嘴挡住去路,河道在这里绕了个急弯。沙滩越走越窄,最后被哗哗的流水吞噬。坐骑陡然压下疾驰的脚步,正准备往绕过山嘴的一条小路跑去,蓦地山嘴的岩石后面,爆发出一阵激烈的枪声。飞镖乔姐不由得大吃一惊,顿时一颗心怦怦乱跳。后面的鬼子尚未甩脱,要是再碰上见国军打国军,见鬼子打鬼子,见游击队打游击队的土匪,她这条捡来的小命可就丢得太不值了!她正想强支起身子看个究竟,没料想刚冲下山崖的几十个乡民打扮的人中间,发出一阵欢呼:
“啊!是飞镖乔姐!”
“是乔姐,飞镖乔姐!”
“没你的事!快走,我们等在这里打伏击,专揍送上门的小鬼子!”
她惊诧万分。那为首的高头大个,竟是跟沦陷前的岳阳专署专员王翦波有点瓜葛的抗日游击队头目胡春台。她的“飞镖队”跟胡春台有过几次“合作”,胡部游击队员当然认识她。胡春台率领部下朝河滩冲去,已经跟追到了眼前的日军宪兵摩托队接上了火。在一片煮粥似的枪弹、手榴弹的爆炸声中,她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眼前一黑,晕倒在马背上……
通灵的坐骑,载着失去了知觉的飞镖乔姐,沿着山边小路,朝暮色笼罩的幽深峡谷走去。马的肚皮和臀部多处“挂彩”,殷红的鲜血,零零落落滴在山路上。浑身汗透了的枣红马鼻子喷着粗气,大张着嘴,高昂着头,仿佛要仰天长啸——然而它发不出声音,它的气血衰竭了,嗓门嘶哑了,钉着铁掌子的蹄脚明显地缓慢下来,缓慢下来……然而它还是走着,走着,走着……
它走向黑夜,走向密林。
它终于在一个不知名的山坡上倒下了,倒下去就再也没有爬起来。
黑暗吞噬了一切,黑夜抚摸着已经脱险的姑娘——她仍然昏迷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