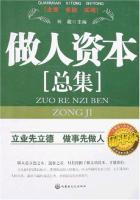牧师轻视不圣洁的本性:这就是他存在的惟一价值。——不服从上帝的“法律”,就是说不服从牧师的“法律”,就获得了“罪”名;“重新服从上帝”的方式(这是被惟一期望得到的)就是用来附属于牧师的方式,这就更充分地保证了牧师的地位:惟有牧师“能使人免罪”……从心理学观点来看,在牧师使之有条理的任何社会中,“罪”是必不可少的:它成了权力的实际工具,牧师生活在罪之中,他需要“罪的委任权”……至高的法是:上帝宽恕忏悔的人——用直率的话说就是:上帝宽恕服从牧师的人。
《反基督》
基督教创立之时,曾向人们提出自杀的可怕要求,并以此作为它的权力杠杆。
它只允许两种自杀方式,并且用最高的尊严和最高的希望加以掩盖。其他的自杀方式是严厉禁止的,不过,殉教和苦行僧的慢性自栽又是允许的。
《快乐的科学》
谁觉得自己是为了观看而不是为了信仰被预先规定的,那么,对他来说,一切信仰者是太吵闹和纠缠不休:他抗拒他们。
《善恶彼岸》
查拉图斯特拉:
“所有的神都已死了,现在我们要使超人活起来!”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给我们展示的这类科学前奏和预演,当初根本没有被人认识到,在古代,也许连宗教也没有被当成预演,而只是人们享受某个神明的自我满足感和自我解救的工具罢了。人们会问,在没有接受宗教教育、甚至在连宗教前身也没有出现时,人们是否已自发产生对神秘力量的渴求并以此为满足呢?普罗米修斯是否必须先承认偷了火种并为此悔罪,最后才发现由于他渴求光明而创造了光明呢?是否不仅人、而且上帝也是他手中的陶土和作品呢?一切东西只是雕塑家的雕像吗?幻觉、偷窃、高加索山、秃鹫,求知者的整个悲剧——普罗米修斯悲剧都是这样吗?
《快乐的科学》
宗教改革是中世纪精神的强化,当这种精神失去良知,宗教改革便促使这两类人大量涌现。
《快乐的科学》
“上帝的意志”(也可以说是保存牧师力量的条件)不得不被人们认识。为此目的,“启示”是必需的。用平易的话说,一种伟大的地道的伪造物成为必然的;“圣书”被发现了,它向公众展露了天使的荣耀,以及终日的忏悔,还有对长年“罪恶”的哀伤。
《反基督》
基督教决意揭示世界的丑陋和恶劣,却反倒造成世界的丑陋和恶劣。
《快乐的科学》
现在,反基督教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动因,而是我们的兴录趣了。
《快乐的科学》
一个人需要多少信仰才能使自己发达兴旺呢?需要多少“坚固物”的支撑才不致使自己动摇呢?这,便是个人力量的测量仪(或者说得更明确些,是他的软弱的测量仪)。
在我看来,古老欧陆的大多数人当今仍需要基督教,所以该教依然获得人们的信仰。人就是这样:对一种信仰他可以反驳千百次,但一旦需要它,又可以说它是“真理”,其根据就是《圣经》上所载的那著名的“力量的证明”。
《信徒与信仰需要》
任何在其血管中具有神学血液的人,无不从一开始就对任何事物都具有错误和不诚实的看法。由此发展而成的心理病症就叫信仰。
《反基督》
道德只赐予那些笃信本人道德的人以幸福和快乐,却不赐予高人雅士。高人雅士的道德存在于对自己和对一切道德的深刻怀疑之中。说到底,还是“信仰使人快乐!”注意!非道德使人快乐!
《快乐的科学》
宗教教徒只考虑自己。
《反基督》
基督教信仰是一种牺牲:即所有自由、自尊、自信的牺牲;与此同时,是奴役和自我嘲弄、自我残害。
《善恶之外》
比任何邪恶更为有害的是什么?——积极同情病残者和软弱者——基督教。
《反基督》
实际上,对于美的世界观,没有比基督教的教义更为大幅度对立的东西。因为,基督教的教义充满了所谓的道德,而且只歌颂具有道德的东西,至于所谓的艺术则被驱逐到虚假的世界——也就是说,基督教否定所有的艺术,甚至对它诅咒、断罪。如果这件事是真确的话,其对艺术当然就会抱持着敌意。因此,我老早就感觉到基督教的这种想法,而以为基督教徒在价值判断方面,一向对生命充满了敌意,甚至对生命存着一种复仇式的憎恶感。因为,所有的生命都基于假象、艺术、迷惑以及光学(看东西的观点),而且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涉及远近法以及谬误之故。
但是,基督教一开始,不管在本质上或者根本上,对生命就抱持着倦怠感。像对“这个世界”的憎恶、对于激烈感情的诅咒、对于美以及感情的恐怖、为了巧妙地中伤这个人世,而发明了所谓的天国。这些东西,无非是对无的欲求,对末世的欲求以及对“安息日中的安息日”的欲求而已——
所有这些东西,跟基督教绝对的意志(只承认道德方面的价值)同样,在所有“走向没落”的形式之中,属于最危险、最为不祥的形式(至少我如此认为)。
至少我认为:那是对生命最为深刻的疾病、疲劳、不满、消耗以及贫困的标志。因为在道德前(至少在基督教的道德,也就是无条件的道德前面),“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不正”。为什么呢?因为在本质上,“生”这件事就是不道德的。
《诞生·自我批评的尝试》
基督教给厄洛斯毒药喝;——他虽然没有死于毒药,但堕落犯罪。
《善恶彼岸》
宙斯并不要人——不管他如何受到其他罪恶的折磨——
逃离他的生活,而是要他继续一次又一次忍受苦难。因此,宙斯给予人希望,而实际上这又是所有罪恶中最坏的一种,因为它延长人的痛苦。
《人类的,太人类的》
基督教让爱神饮鸽止渴,爱神未能死于非命,却从此堕人罪恶的深渊。
《善恶之外》
正如叔本华主张的,形而上的需要并非是宗教的源头,而是它后发的幼芽。在宗教思想的钳制下,人们习惯于“另一个世界”的理念;假若消除宗教的这一幻想,人们便产生难耐的空虚,总感到缺少了什么。从这一情感遂产生“另一世界”,不过它是一个形而上的、而非宗教的世界。
在远古时代,导致人们接受“另一世界”的并非是本能欲望,亦非某种需要,而是在解释自然现象时发生的错误,或者可以说是智力不济吧。
《快乐的科学》
罪……是人类自我袭读的典型。它被发明用来使科学、文化和每一种能提高人的地位和尊严的事物成为不可能。
《反基督》
哪里缺乏意志,哪里就急不可待地需要信仰。意志作为命令的情感,是自主和力量的最重要标志,这就是说,一个人越是不知道如何下命令,他就越是急不可待地渴望一个下命令的人,一个严令的人。
《信徒与信仰需要》
我只能信仰一个知道如何跳舞的上帝。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基督教的创始人以为,没有什么比罪恶更令人痛苦了。其实他错了,错就错在他感到自己无罪,压根儿就没有犯罪的经历!于是,他内心充满着一种古怪的、臆造的怜悯:怜悯犯罪的痛苦。其实,他的子民——罪恶的“创造者”——也很少感到这是一种巨痛!
然而,基督教徒事后追认基督的正确,进而将其错误神圣化,变成“真理”。
《快乐的科学》
人类甸甸于作为福音的起源、意义、道理之对立者面前。在教会的概念中,它宣称为神圣的东西,正是“带来福音者”在他足下和背后所感觉到的东西——一个人将无法找到一个更大讽刺世界历史的例子……
《反基督》
只要有墙的地方,我要在所有的墙上,写上我对基督教的控诉——我拥有甚至可以使瞎子都看到的文字……
我说基督教是一个大灾祸,一个最大的内在堕落,一个最大的仇恨本能。对它而言,没有一种手段是更毒害的、更隐秘的、更卑下的,更微妙的——所以,我称它是人类一个永久的瑕疵。
对一切价值的重新评估,是从这个灾难的凶日开始——也就是基督教的第一天之后。为什么它不在末日以后呢?为什么不在今天以后呢?……
《反基督》
宗教创始人的真正发明,一方面是找到了一种特定的生活模式及道德习俗,并使之成为准则,消除人的厌世情绪;另一方面是阐释这种生活模式,于是,这生活散发出最高的价值光辉,成为人们为之奋斗、有时甚至献出生命的至善之物。
这两个方面的发明,实际上以后一种更为重要,因为某种生活模式通常已经存在,人们只是不知道它与其他生活方式相比,其价值何在罢了;宗教创始人的重要性及其首创精神就表现在他发现并选择了这种生活模式,并首先认识到它的功用,知道如何阐释这功用。比如,耶稣(或者是保罗)发现了一种小民百姓的生活,那是在古罗马占领的地区,即在意大利版图以外的占领区。此乃一种简朴、崇尚道德而压抑的生活,耶稣对它做了诊释,赋予它至高无上的意义与价值,由此也赋予它蔑视其他生活方式的勇气,赋予它摩拉维亚教徒那宁静中的狂热,内心隐秘的自信,这自信日渐增强,终于准备“征服世界”了(指征服罗马以及罗马帝国的上层阶级)。
释逸牟尼同样也发现了一类人,这类人散布在该民族的各个阶层,其社会地位不同,怠惰而善良(更无恶意,绝不冒犯他人),其生活是节制的,几乎没有什么需求——这也是怠惰使然。释迎牟尼懂得,他必定能使他们接受这一信仰:承诺免除人世的艰辛(即劳动的艰辛,行动的艰辛)。这个“懂得”便是他的天才。
宗教创始人还必须从心理学上懂得某些普通人,他们尚未认清同是一个归属,正是他才把这些人捏合在一起。因此,宗教的创立总是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
《快乐的科学》
基督教曾经骗取我们古代的文化收获。
《反基督》
最终,我们也用这样的怀疑态度看待宗教的一切现状和事务,比如罪恶、忏悔、感恩、圣灵化等等,有如“钻牛角尖”,这样,我们在阅读基督教书籍时也产生同样的优越感和洞察力,我们也完全懂得宗教情感究竟是什么东西了!是好好认识和描述这情感的时候了,因为奉行古老信条的虔诚者正在灭绝,让他们拯救他们的投影形象和模型吧,至少为知识界!
《快乐的科学》
犹太人是世界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民族,因为他们对解决存在或不存在的问题,怀有极其强烈的信念,为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把整个自然、整个自然性、整个实在、整个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进行根本的窜改。他们否认自己与所有那些条件,即一个民族能够优先生存,被允许生存的条件相对立;他们把自已造就成自然条件的对立面,——他们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把宗教、宗教崇拜、道德、历史、心理学一个接一个地颠倒过来,落入同他们的自然价值相矛盾之中。
《反基督》
与之对立的便是失去攻击性、已经疲乏的虚无主义,其最有名的形式便是佛教了。它是一种被动的虚无主义、一种懦弱的象征。其精神力已消耗殆尽,对于未来的目标已与现存的价值观念脱节,失去其继续存在的价值了。——其综合性的价值目标早已解体,个体的价值观念亦相互交战而濒临崩溃的边缘。——宗教现今只能粉饰活力,治愈人们心灵上的创伤,麻痹人类上进的灵魂,在道德与政治上达到一个最低的要求。
《权力》
把原因与结果弄错的谬误——以所有的宗教以及道德来说,一般都采取如下的根本方式。
“你们必须做某些事情,绝对不能做某些事情……只要如此,你们就会变成幸福的人。否则的话……”反正,所有的道德以及宗教,都采取如此的命令方式——我一向称此为违反理性的大罪,以及绝对性的不合理。
如果由我来说的话,情形将刚好相反——我将基于一切价值的转变方式如此地说:“教养良好的人,也就是‘幸福者’,根本不会做某种行为;而对于其他的行为,将基于本能而避开,并且将把生理学方面所表现的秩序,带人他跟事物的关系中。”换一种表现方式来说——“一个人的道德也就是他幸福的结果。”
教会与道德如此地说:“某一个种族、某一个民族,由于没有道德以及生活奢靡,势将被消灭殆尽。”已经恢复的理性会如此地说:“当六个民族将灭亡时,生理方面将显著地退化。结果呢?没有道德的行为,以及奢靡的生活方式,将陆续地出现。”
譬如说,有一个苍白,浑身又病惬惬的青年,他的朋友一定会如此地说:“正因为催患了某种疾病才会如此……”我则会如此地说:“他所以会催患疾病,以及他无法抵抗疾病,乃是生活贫困的结果。”
阅读报纸的人会说:“这个党派可能是因犯了这种过失而灭亡。”而我则会基于更高一步的政治论调如此地说:犯了这种过失的党派已经完了,因为它不再具有确实的本能不管何种过失,都是本能退化以及意志分散的结果。这一句话,几乎可以给所有恶劣的行径下定义。凡是所有良好的行径都是因发现本能——是故,它使人感到轻松、自由。所谓“辛苦”的说法,不过是一种反驳罢了。典型的神(指尼采眼中之神——Dionysos神)一向与英雄区分开来。以我的论调来说,轻快的步调,应该是神性的第一个特征。
《偶像》
欧洲人发现自身处在一片辽阔的废墟中,其间某些东西仍高居不下,有些则逐渐转为腐败阴暗,而大部分均已倾纪倒塌。这情景犹如壁上那一幅四处蔓生着高矮参差野草的画——我要到哪里去找比这些断垣残壁更美的景物呢?
这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坚固的宗教建筑——也是硕果仅存的罗马建筑!——它当然不是毁于一旦,而是历经长久以来地震的摇撼、各种精神力量的贯穿、挖凿、噬啮和腐蚀,才造成整体的毁灭。
然而最令人纳闷与不解的乃是:当初贡献最多、最大心力,以保存维护此一教堂的人,竟然也是最不遗余力摧毁它的——德国人。
。看来德国人并不了解一座教堂的本质和精髓所在。难道他们的精神力量不够吗?还是因信仰不坚才导致如此的结果呢?
不论在何种情况之下,教堂的结构一概都是基于南欧特有的自由慷慨精神,同时也基于南欧人对自然、人类和灵魂的怀疑,另外也对于人类经验的认知——这一点恰与北欧人的看法截然不同。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无论就时间的长久,或所牵涉范围来说,都是出于以“单纯”对抗“复杂”的义愤。说得谨慎一点,这乃是一种粗鄙却厚道的误解,颇值得原谅——人们并不明白一个胜利的教会之表达模式,而只见到它腐败的一面;他们误解了怀疑主义的高贵本质,错怪了每一个成功自信的教会权限之下,所能允许的几近奢侈的怀疑论调和包容力量。
《知识》
我要告诉你们基督教的真正历史——“基督教”的“教”字,根本就是一个误解。事实上,只有过一个基督徒,而他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宣传“福音”者已死在十字架上。从那个时候起,被称为“宣传福音者”,实际上是福音者的反面,是“恶音”恶魔的使者。
《反基督》
要在一种信仰中,例如透过基督而获得赎罪的信仰中,去发现基督徒的特征,那是虚假而荒谬的;只有基督的实践行为——像死在十字架上那个人所经历过的,才是基督徒……
这种生活今天还是可能的,对于某些人而言,甚至是必须的。真正原始的基督教,在任何时期都是可能的……
《反基督》
这个“福音的使者”(指耶稣而言)死了,正如他曾生活过一样,正如他曾教训过人们一样——他不是去“救赎人类”,而是告诉人们必须怎样去生活。他用的是他在审判者前,在那些控诉者以及各种诽谤者和责难者前的行为。这个实践是他给我们人类的遗产。
他没有反抗,也没有为他的权利辩护,他没有采取过可能避开最恶劣结果的步骤。相反的,他反而挑起它。他乞讨、受苦、受那些陷害他的人;不反抗、不发愁、甚至对于恶魔也能去爱他。
《反基督》
与“比青铜更久远”的罗马帝国比起来,所有在这之前或之后的历史,都显得拙劣,像是东拼西凑而成的。神圣的无政府主义者及基督徒,执意要去破坏“世界”——这个即使在困境下,仍是最伟大组织形式的罗马帝国——直到日尔曼人和其它野蛮民族能够成为它的主人为止。而这些人却声称自己的行为是“虔诚”的。
基督徒和无政府主义者,都是颓废的,两者除了分化、栽害、衰败外,不可能再产生其他的结果。两者均死命地反对一切存在,包括一切光荣、永恒的存在、一切会为生活带来希望的东西。
基督徒是罗马帝国的吸血鬼——他们一夜之间破坏了罗马人历经千年所建立起来的高度文明和伟大功业——这一点到现在还没有被了解吗?
罗马的历史使我们对罗马帝国有很清楚的认识,这最值得赞叹的大艺术品就是一个开始,它的造成经过数千年来证明,是最具有价值的!一直到今天,没有人能再造出第二个罗马帝国,甚至没有人能够梦想去建造这种组织!
这个组织,坚固得足以承受那些荒诞帝王的蹂躏。人为的偶发事件,丝毫不能破坏它——此乃一切伟大组织的先决条件。
然而,如此坚固的组织,却终究对抗不了那一切堕落中最堕落的基督徒……
这种隐秘的蟊虫,在夜间、在迷茫中,会暗暗的爬到每个人的身上,从当中吸取追求真实的严肃性和寻求实在的本能。这种犹如女性般懦怯、柔弱、外表甜美、分裂的“灵魂”,势必一步步地离开那巨人的结构。那些有价值的、男性的、高贵的人,他们在罗马人身上发现自己的面目,发现自己的严肃性,同时发现自己的光荣。
那些伪善者卑劣、秘密性的集会,在幽暗的概念中,如地狱般的饮血仪式和无罪者的牺牲。尤其是那慢慢煽起的复仇之火——那贱民的复仇之火——这一切都将成为罗马的主人。
于是,保罗出现了……保罗,这个憎恨罗马的贱民,这个憎恨“世界”的贱民,便成为具体的代表,成为天才,成为永远流浪的卓越犹太人。
他所没想到的是,人们如何利用犹太教以外的基督教运动,去燃起“世界之火”;如何运用“十字架上的上帝”的象征以结合所有下等社会的人们,结合一切秘密反抗的人,结合帝国内由无政府主义者煽动的一切遗产,以成为巨大的势力。
他了解,他需要相信那个不朽的信心,以剥夺这“世界”的价值;他了解,“地狱”的概念将成为罗马的主人;他了解,用“来生”的概念,可使人们扼杀生命。
《查拉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