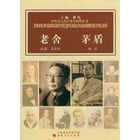其实,不论是利用钱苏做一回临时钦差,还是对将领的大批晋升和逮捕,都是朱元璋精心的安排。说明,他将要采取重大的行动。明眼人已经猜得出来,下—个被整肃的对象,很可能就是炙手可热的胡惟庸。
恰在这时,一件小事引起了朱元璋与胡惟庸的正面冲突。
13
天门外十里长街上,一匹白马,自东向西飞奔而来。马上骑着一名浑身闪着绸光锻彩的青年。他仿佛没有看到街上人来人往,一味挥鞭驱马,旁若无人。
正在奔驰间,路旁的一条巷子里,忽然窜出一个红衣少年。白马突然受惊,嘶叫着人立而起,“噗”地一声,将骑马人远远掀到了地上。无巧不成书,几乎就在同时,一辆装满粮袋的骡车,恰好从旁边赶上来。挽车的骡子受了惊,猛地往旁边急走。车夫挽辔不及,车轮不偏不倚,从落马人的脖子上压了过去。车轮装着铁瓦,几乎将落马人的头颅与身子轧分了家。落马人哼也没哼一声,当即死去。
这个落马人,原来是左丞相胡惟庸的小儿子,名叫胡长兴。是个斗鸡走狗、寻花问柳的恶少。今天,他喝醉了酒,在街市上打马飞驰,结果乐极生悲,作了轮下之鬼。
胡长兴的亲随从后面赶上来,不由分说,将车夫捆起来,牵着去见胡惟庸。胡惟庸一听,爱子暴亡,痛得捶胸顿足。他根本不听车夫跪在地上解释,摸过一条木杖,劈头盖脑打去。车夫被打倒在地,他又命令仆从“往死里打”。一眨眼的工夫,车夫便死在杖棰之下。
消息很快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他只知道胡惟庸的专权独擅,让他忍受不了,没想到胡家还如此地专横跋扈,可以随便打死人。立刻下令逮捕了胡惟庸的大儿子,要他给车夫抵命。
胡惟庸权倾朝野,多年得宠,连皇帝都言听计从,早已忘乎所以。立刻面见皇帝,为儿子求情。
“陛下呀!”胡惟庸流着泪沉痛地呼喊,“那车夫,是压死了臣的小儿子,自己吓死的。与臣的大儿子无干呀——你就饶恕了他吧。”
“是他自己吓死的,还是被你的仆从打死的?”
“臣有治家不严之过。仆人只想教训教训他。不想……”
“不想他就‘吓死’了,是吧?”朱元璋瞪大了双眼质问,“你小儿子的死,主要责任在他自己。他不打马在市街上飞奔,你家的马怎会受惊?马不受惊,你儿子怎会摔到地上?是他自己找死,与车夫何干?”
胡惟庸仍然嘟噜道:“陛下,臣愿意用金钱,赎犬子一条命。”
朱元璋指着他的鼻子怒吼道:“胡惟庸,你认为金钱就可以买到人命吗?你把朝廷的法度放到何处?对于横行不法者,朕决不饶恕。杀了你的大儿子,给车夫偿命!”
“陛下谅情,陛下谅情!”胡惟庸连连磕头求饶。“法令如山。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朕决不答应!”朱元璋拂袖而去。
胡惟庸同时失掉两个儿子,对皇帝恨之入骨。朱元璋除掉他的决心,也终于下定,单等寻找时机下手了。
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国使臣阳须文旦来应天朝贺,向朝廷进呈表章以及大象、良马等贡品。中书省接待后,没有按时奏报。宦官却将见到占城国使臣的情况,及时报了上去。朱元璋勃然大怒,连夜召来左右丞相责问。他厉声喝问道:
“朕居中国,抚四夷,无不以礼待之。今占城来贡方物,尔等竟然置若罔闻,不事上奏。尔等身为丞相,辅佐天子,出纳帝命,怀柔四夷,就该如此吗?”
胡惟庸、汪广洋慌忙叩头请罪,两人异口同声,声称责任在礼部,是他们没有及时奏禀皇上。召来礼部的官员质问,他们则说,早已报给了中书省,按照惯例,都是由中书省上奏。
朱元璋当即下达敕书,严加斥责:“九月二十五日,有怠慢占城入贡事。问及省、部,互相推诿。朕不聪明,罪无归着,只得囚禁省、部主其事者,概穷缘由。若罪行果有所归,则罪其罪者,严加制裁,未能释免!”紧接着,胡惟庸、汪广洋及礼部堂官,一大帮子高官,一起下了大狱。
丞相同时下狱,恐怖气氛弥漫朝廷。人人自危,朝不虑夕。为了保全自己,御史们争先恐后上书,一致攻击胡惟庸擅权植党,祸乱朝廷。
御史中丞涂节于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上书,怀疑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并且提醒皇帝说:“当时任御史大夫的汪广洋,应该知道内情。”
朱元璋心里有鬼,对此事很敏感,立刻提问汪广洋。汪广洋根本不知内幕,自然矢口否认。朱元璋正要找机会替自己洗刷,便以“朋党包庇”之罪,将汪广洋削职夺禄,远贬海南岛,永不叙用。汪广洋离京不久,朱元璋忽然改变了主意,派使臣追上去,宣布敕旨,就地处死。敕文列举了汪广洋一大堆罪状:
公私不谋,民瘼不问,兴造役民茫无所知,本祀诸神略不究心。公事浩繁惟他官,是非随行剖决不问,人才不曾进退,终岁安享大祿。在江西,不能匡正朱文正之恶,在中书,不能揭发杨宪之奸……观尔之为也,君之利乃视之,君之祸亦视之,其兴利除害,英知所为。无忠于朕,无利于民。如此肄侮,法所雎容。差人遠斩其首,以示柔奸。
老实人汪广洋听罢敕文,满腹含冤,惟有对天长叹。然后引颈就戮。随行小妾陈氏,抱着丈夫的尸体大哭一场,想想自己走投无路。抢过公差的佩剑,自刎而死!
朱元璋得知陈氏壮烈殉节,很受感动,准备对烈妇加以褒扬。不料讯问陈氏的身世,得知是犯官陈知县之女。不禁勃然大怒,立即下达命令:“籍没人官的妇女,只赏给有功武将之家,文臣何以得到?他们置朝廷法度于何地?着刑部衙门从严推问!”
这样一来,六部官员全部牵连坐罪。胡惟庸更是首当其冲,罪上加。罪。所有被拿问的犯官,都被诱逼攀扯揭发胡惟庸。
御史中丞涂节受刑不过,决定死里求生。洪武十三年正月初二,他编造了一个胡惟庸结党造反的“大案”,交了上去。他凿凿有据地写道:“胡惟庸虽然官居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专擅独行,不可一世,仍然不满足,野心越来越大。他定远老家的水并中忽然生出了石笋,拍马屁的人都说是祥瑞。又有人跟他说,他家三代祖宗的坟头上,每夜红光烛天,是兴旺发达的吉兆。胡惟庸听了心中暗喜,认为起大事的时机到了。立刻动手拉拢武将,掌握军队。首先找到的是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要作假,就得做到以假乱真。涂节之所以攀扯陆仲亨和费聚,因为两人都是胡惟庸的朋友,而且都受到过朱元璋的斥骂与贬谪,对皇帝心怀不满。有一次,陆仲亨未经批准,自西安擅自返京,而且沿途使用驿站。朱元璋得知后,严厉斥责:“中原战火甫歇,百姓刚刚复业,买马供役,十分艰苦,都像你这个样子,百姓们卖儿卖女也无法供给。”便命他到代县捕盗赎罪。费聚就是当初跟随朱元璋招抚张家堡民团的那个小头领。自从封侯拜爵之后,渐渐奢侈腐化,沉溺酒色,多次受到朱元璋的严厉谴责。
涂节在口供中写道:胡惟庸看到他们与皇帝异心,便主动与二人接近。经常邀到府上饮宴。一天,喝至半酣,胡惟庸屏退左右,鼓动说:“我等皆有不法的把柄,捏在人家手里,一旦败露了怎么办?”两人一时惊骇无语。胡惟庸继续策动说,“只有谋反,才是完全之计。”两人一致赞同。于是,胡惟庸要他们在外地联络军马。当胡惟庸为儿子偿命的事与皇帝公开冲突之后,他便和陈宁、涂节等亲信商童动手,并秘密遣人通告各地党羽,作好起事的准备。
涂节的口供一吐,朱元璋如获至宝。立即全部逮捕,突击审问。重刑之下,焉愁没有供。凭空捏造,瓜株蔓连,像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一供就信,一信就抓,不少人朝登朝堂,暮扛伽锁。只要一个人被咬出来,他的家属、仆从、亲友等,统统株连下狱。刑讯所得到的口供,自然是驴唇不对马嘴。但经过辗转指供,诱供,也能串三搭四,使线索逐渐淸晰、愈合。这就在劫难逃了。
为防止久拖不决,变生不测,三天后,即将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一批官员正法。“族党”一起处决,祖坟被撒骨扬尘。涂节原指望迎合圣意,将功赎罪,保住脑袋,方才编造了胡惟膺谋反的谎言,岂知把自己也织进了死网。当举朝文武同仇敌忾,齐声喊打的时候,皇帝也就“忘记了”他的检举之功,顺手把他送进了鬼门关。
从洪武十三年开始,一浪高过一浪的抓“胡党”运动,此起彼伏。中书省及有关官吏几乎无一幸免。平时有仇怨的人,更是趁机互相告发。而一经攀扯进胡党,立即抄没家产,收监刑讯。更为可怕的是,江南不少富室也被罗织进去,推入陷阱。虽然其中有一些是为害地方的豪强,但大多是夹着尾巴做人的土财主。浙江浦江有郑氏六兄弟,孝义闻名一方,也被牵连进去。朱元璋知道了,感到像郑氏这样的忠义之家,不可能跟着别人造反作乱。立即将郑氏兄弟从狱中放出来,亲自召见慰问,并任命老大郑浞为福建布政司参议。可惜,皇帝的恩泽,只施给了郑氏一家,其他富室豪宅,凡是被牵连进去的,统统结伴去了枉死城。
胡惟庸谋反大案,是涂节一手编造的,本属子虚乌有。但朱元璋宁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甚而将谋反大案,当成一根打人的棒子,想要哪个死,此人便成了死有余辜的“胡党”。侥幸保住性命,则是浩荡圣恩法外施仁。
朱元璋不愧是整人杀人的高手。他发起的抓胡党运动,从洪武十二年起,持续搞了十几年,前后杀了几万人。案情内容也不断扩张延伸。洪武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三年还掀起了几次高潮。就连被贬到江西安远县的老夫子宋濂,也被牵连进去,再次罹难。
此后,搞整人运动,亲手抓大案,成了朱元璋的一种信仰和嗜好。洪武二十六年,他又搞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运动——大抓“蓝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