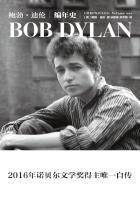杀戒大开,数万无辜成胡党;说情不准,宋濂自缢成冤鬼。牵胡案,李善长险些遇害;为说情,智多星再次惹灾。开国元勋被抄家,七七老人上法场。“铁券”免“二死”,如同儿戏;功臣辩冤诬,置若罔闻。深宫惊噩梦,沉舟“功臣”难逃劫;东征擒降将,反目翁婿成寇仇。
旷的谨身殿,寂然无声。朱元璋正在伏案批阅奏章。忽然,传来轻轻的脚步声。他头也不抬地问道:
“是哪个?”
“是孩儿。”
扭头一看,太子朱标脸色惶怵地肃立—旁。他放下手中的奏章,不解地问道:“标儿,发生了什么事?”
“爹爹……”朱标上前两步,欲言又止。
“嗨嗨——有话快说。没看到我忙得很吗?”
“爹爹!”朱标痛彻地呼叫一声,扑通跪到了地上,“孩儿,是……是给宋老师求情来了。”
“为什么?”朱元璋瞪大了双眼。
朱标嗫嚅地答道:“爹爹!宋老师,为我大明朝,忠心耿耿,并无大过。何必……非要置他老人家于死地呢?”
“这么说,是为父我昏懵不明,冤枉好人啦?”
“孩儿不敢。不过,孩儿的成长,除了严父慈母,全靠宋老师十余载谆谆教诲呀。没有宋老师,哪有孩儿的今天?请爹爹开恩,饶宋老师一命吧。”朱标抽抽嗒嗒哭了起来。
“朱标,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怎么还这么糊涂?我要杀他,除了他罪有应得,还不是为了尔后你能够平安地坐天下?”
“爹爹,话是这么说。杀别人,孩儿不阻拦。可是,宋老师他……”
“他对你有恩,是吧?”
“是的,他对孩儿,从来都是那么尽心尽意。况且,对皇上也是那么……”
“住口!”朱元璋再次打断儿子的话,“朱标呀,朱标!你怎么就不理解为父的良苦用心呢?你认为对咱们有功,就不能杀吗?告诉你,越是功劳大的,对咱们朱家的威胁就越大。像你这样婆婆妈妈,尔后非坏大事不可!
“可是……”
“可是什么?不必多言!收起你的婆娘心肠,回去好好读书吧。”
“宋先生冤枉啊,可我救不了你啦!”朱标只能大声在心里呼喊。揩揩满脸热泪,脚步蹒跚地退了出去。
洪武四年,宋濂因一句“自古戒禽荒”的劝谏,被贬为江西安远县知县。两年后,才被召还。洪武六年,迁侍讲学士,知制诰,仍在文学侍从之列。洪武九年,朱元璋又进行安抚:召他的次子宋璲为中书舍人,长孙宋惧为仪礼序班。他对宋濂调侃道:“宋先生,你为朕教导太子及诸王,朕也教诲了你的子孙呀。”洪武十年正月,六十八岁的宋濂,以年老为由,恳求致仕。朱元璋痛快地答应了,并赐给他一部《御制文集》,以及许多贵重的锦缎。分手时,朱元璋依依不舍地对老夫子说道:“老先生,三十二年后,便是卿的百岁寿诞。那时,拿这绮帛做百岁衣吧!”宋濂感动得老泪纵横,颤颤巍巍地高喊:“皇上的恩德,地载天覆,臣没齿不忘呀!”
宋濂平安地回到家乡,不置田产,不谈朝政,唯以纂述和授徒为乐。每年九月十八,皇帝诞辰之期,他都长途跋涉来到京城祝贺寿诞。洪武十二年来祝寿时,他陪着皇帝登文楼,一步踉跄,摔倒在楼梯上,跌得许久没有爬起来。内侍将他搀扶起来,仍然面色痛楚,气喘吁吁。朱元璋看宋濂实在是老了,就怜悯地吩咐道:“老先生年事已高,明年不要再来为朕祝寿了。”
“谢皇上体恤老臣。”宋濂忙不迭地磕头谢恩。
可是,到了第二年的“万寿节”,因为胡惟庸的案子,搞得人心惶惶,朝廷气氛十分紧张。朱元璋自己也是心绪不佳,看着什么都不顺眼。忽然想到,宋濂往常年年来贺,君臣把臂,饮酒赋诗,谈天说地,何等惬意。今年却不见那老儿的踪影,真正是岂有此理!他把去年吩咐“不必再来”的茬,忘了个精光。于是,命人潜往宋濂的老家浙江金华,暗暗查访:“去看看,那老家伙在忙些什么?”
使者来到宋濂的家乡,老夫子正与几个朋友在饮酒赋诗。对于一个致仕高官来说,本来是个非常普通的事情。但朱元璋听罢汇报,却勃然大怒。哼,那老家伙在家乡吃酒玩乐,却不来祝寿,他的眼里哪有皇上?不用说,他往常挂在嘴上的赤诚耿忠全是作假,朕受了他几十年的欺骗与捉弄!朱元璋恨不得立即将老家伙拿来,抽了他的牛筋,剥了他的老皮。转念一想,宋濂以温厚耿忠闻名朝野,如贸然下手,难免留下欲加之罪的话柄,那岂不是有损皇帝的圣明?他只得把一腔怒火,压了下来。等待找到口实再说。
有一天,朱元璋“不经意”地汛问刑部一位姓郎的主事:“宋濂的孙子宋慎,与胡党有没有联系?”
专擅钻营拍马、迎合上意的郎主事,心领神会,立刻将宋愤“通胡始末”报了上去。于是,宋慎被列名胡党,逮捕处死。宋濂次子、宋慎的叔叔中书舍人宋璲,则连坐被杀。紧接着,派人去抄了宋濂的家,将老人连同他的妻小、仆妇,一绳子拴到京城,下了大狱……
太子朱标正是得到师傅全家被抓,就要杀头的消息后,找皇上为师傅说情的。不料,碰了个硬钉子。万般无奈,只得流着泪去找母亲马皇后帮忙。
皇后得知宋师傅大难当头,心忧如焚。这些年来,皇上杀人如麻,她总是劝他手下留情,为自己积德,也为子孙积点后福。但朱元璋统统当成耳旁风。想不到,现在又轮到了老实巴交的宋先生身上!她恨不得马上跑到谨身殿,向丈夫求情。旋即又想到后妃不得进人三大殿的规矩,只得忍了下来。
她正焦急得坐立不安,可巧皇上来到了乾清宮。平素日,除了吃饭和困觉,皇帝很少驾临后宫。今天破例而来,而且满脸阴云,肯定是有特别烦恼的事情。她倍加小心地施礼让座,然后小心翼翼地问道:
“皇上今日脸色不快,莫非什么人又惹你生气啦?”
“满天下的人,哪个敢惹我生气?”
“那?”
“你的好儿子呗!”
“该打的!不知是哪个不懂事的,又惹皇上生气了?”此时,朱元璋已经有了十九个儿子,皇后佯做不知,“他们都年轻,你就别怪乎他们了。”“年轻?你总是给他们找理——二十大几的人啦,还年轻?”
“莫非,皇上指的是标儿?”
“不是他还有谁?”朱元璋握起右拳,狠狠敲击椅子扶手,“别的孩子不懂事也就罢了。他身为太子,尔后天下是他的。我为他扫淸龙椅周边的虎狼,他竟然给他们讲情——你说可气不可气?”
“原来是为标儿生气。”马皇后沉默片刻又问道:“皇上,不知妾身该不该问?标儿到底做了啥糊涂事,惹得你生这么大的气?”
“宋濂一家是胡党,我把他一家抓来应天等候处置。他竞然哭天抹泪地给他讲情,丝毫不懂得我的一片苦心,简直是糊涂透顶!”
“怎么?你要杀宋先生?”
“那老儿,可杀不可留!”
“皇上,宋先生真的是犯了该死的罪过吗?”
“哼,你寻思我能冤枉他?”朱元璋见皇后泪流满面,嗄声嗄气地问道,“怎么,莫非你也要为那老家伙讲情?”
“妾身不敢。”马皇后急忙揩揩满脸的泪水,“不过……”
“不过什么?你说呀。”朱元璋的口气缓和了下来。
“唉——”马皇后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热泪再次流满了脸颊。“宋’先生真的是犯下了死无赦的罪过?”
“他一家人,都是该死的胡党!”
“皇上呀,民间为孩子请个教书先生,还像对待贵客似的,吃最好的饭食,永远不忘人家的情分呢。这么多年来,宋先生教太子和诸王念书,尽心尽力,你怎么就忍心杀他呢?”
“那老儿在家乡也不安分——死有余辜!”
“能吗?宋先生致仕回家,哪里知道朝廷里面的事?还不都是那些心肠黑的人给他捏造的?皇上可不能听见风就是雨呀!呜呜呜……”马皇后竟然哭出了声音。
“你呀,跟那不肖种一样,糊涂不懂事。”朱元璋不愿再听下去,拂袖而去。
吃晚饭的时候,马皇后陪朱元璋吃饭。她不饮酒,也不吃肉,只吃下两口米饭,便放下了筷子。
“咦,皇后,怎么回事?莫非你病了?”
“不是。妾在为宋先生……祈福呢。”
朱元璋分明有些动情,勉强说道:“看在你们母子的份上,我饶了那老奸贼一命。”
说罢,他放下筷子,起身离去。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宋濂拣到一条命,流放四川茂州充军。七十二岁的老翁,伽锁锒铛,好不容易挨到夔州,已是诸病缠身,骨瘦如柴。
这一天,来到一座破庙歇宿。寒风贬骨,夜枭声声。老人蜷缩在神坛前,哪里睡得着。抚心自问,平生无愧天地圣贤、神佛皇帝,却落到如此悲惨下场!天地虽大,哪里去寻公道和正义?越想越伤心,想想往后的日子,更是不寒而栗。趁着押解人睡得正酣,他解下裤带,颤颤抖抖地在窗棂上拴了一个绳结,引颈进去,了却了可怜的残生。时间是洪武十四年五月二十日。
老功臣宋濂的冤魂去了西天,朱元璋的目光,立刻投向了被凉在凤阳的李善长身上。
当遇到不顺心的事或者大狱大案,朱元璋常常表现得烦躁狂暴,宛如一头被激怒的凶狮猛虎。谁要是不看火候,在这种时候进行忠谏,拂逆皇帝的意志,准成是自找麻烦。
至高无上的皇帝,乃天之骄子,国之主宰。什么事都要顺从皇帝的意志,一切取决于皇帝的喜怒。凡是皇帝说的话,谁都得山呼万岁,凡是皇上做的事,谁也不敢稍有更动。皇帝就是仙佛天神,就是真理的化身,就是王法道德的楷模!
尽管如此,朱元璋仍然常常表现出少有的节制与冷静。知所当为方才为,决不是不计后果地莽撞蛮千。处大局,临大事,他总是成竹在胸,层次分明,决不会乱了方寸。
在审问胡党过程中,凡是牵涉到中书省及各部院衙门的,他连眼也不眨一眨,大手一挥,统统杀戮。而凡是涉及到武将的,尽管是谋反大罪,他却一概宽宥。像陆仲亨、费聚那样的“胡党要犯”,竞然都获得了赦免。这就淸楚地说明,他指挥着刽子手猛杀猛砍所依据的,不是有无罪行,或者罪过大小。而是取决于是否需要。
当满朝大臣同仇敌忾,表示同叛逆分子不共戴天,纷纷要求处死陆仲亨、费聚等武将时,朱元璋竟然理直气壮地当众为之开脱:
“当年陆仲亨才十七岁,父母兄弟都死,为了躲避乱兵,揣着一升麦子藏在树林里,我率部队经过,劝他跟我干,他便随了我。而后,南征北战,功勋卓著。这些人都是最早跟了我的手足心腹,我不忍心治他们的罪。你们就不要再追究了。”
既然连皇帝都不想追究,谁再向武将们下口攀咬,不仅徒劳无益,而且自惹骚臭,甚而引火烧身,自找麻烦。一时间,攻讦武将的奏折与口供,销声匿迹。因为摆在朱元璋面前的绊脚石,不是武将,而是中书省和左右丞相。
洪武十二年汪广洋被杀,第二年正月初六,胡惟庸伏法。正月初七,朱元璋便忙不迭地宣布,罢除中书省,擢升六部,改大都督府为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并写进《祖训》,以便传之后世。列举的理由是: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朝始置丞相,但秦朝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置之重典!
实行了一千五百余年的丞相制度,朱皇帝金口一开,从此废止。这无形中提高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本来对中书省和丞相负
责的职能部门,改为直接由皇帝管辖。最高军事机关——大都督府,权力一分为五,也由皇帝直接统辖,避免军权集中于个别武将手中。再加上都察院(由御史台改)的监督,就构成府、部、院三大互相制约,分别对皇帝负责的权力机制。此外,通政司负责传递内外奏章,大理寺负责复审刑狱,与刑部、都察院共同担负司法审判任务,时称“三法司”。
早在中书省存在的时候,朱元璋就下令取消了地方上的“行中书省”,由承宣布政使司,负责一个省区的行政事物。原来的提刑按察使司,成为刑法监察机构,都指挥使司依然掌管一个省区的卫戍部队,合起来称“三”。构成都、布、按三权鼎立、互相牵制的地方权力系统。形成了新的权力分配格局,进一步加强了皇帝手中的权力。胡党案成了朱元璋加强皇权、废除相权的契机。
利用“奸党”这根大棒打人,是朱元璋的拿手好戏。他使用得是那样得心应手,那样纯熟。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一万五千多名“胡党”,成了刀下之鬼,案子仍然愈滚愈大。胡惟庸究竟是不是有这么大的能量,是不是遍地是胡党?朱元璋自己心里至明至白。他是一名高超的魔术师,不仅能制造子虚乌有的罪名,还能随意将案子变大。不幸的是,清除异党的目的达到了,他的一颗心却越来越发虚。总觉得,人人都用怀疑的眼光盯着自己。尽管他利用一切机会,宣扬胡党的狰狞可怕,罪大恶极,彻底清除胡党是长期的任务,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无奈,越描越黑。不拿出几件富有震撼性的案例,人们不会心悦诚服。于是,他以攻为守,继续把除“奸党”的运动推进下去。以便抓到富有说服力的罪证,解决他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
建国初期,边境并不平静。在漠北,被推翻的旧元王朝仍然蠢蠢欲动。在沿海,日本倭寇不断在沿海侵扰。“南倭北虏”成了大明朝安全的两大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通倭、通虏,无疑成了人人当诛之的滔天大罪。
朱元璋正是从这里,再次找到了突破口。
武十九年,即胡惟庸死了六年后,突然公布了他的新罪状——通倭!
人人籐惊,举国哗然。在人手一册、天天必读的《大诰》中,将胡惟庸通倭始末,写得清清楚楚:
洪武十年,明州卫指挥林贤,奉命护送日本国贡使归廷用进京。皇上厚赏归廷用,令林贤送他出海。林贤在京期间即与胡惟腐结成死党。待归廷用回国后,胡惟痛让林贤以剽倭的名义袭击日本朝贡船只。然后奏报朝廷,将林贤眨往日本。林贤在日本活动了三年,由胡惟麕派
人秘密召回。紧接着,日本赏使如瑶藏主率领四5名武装倭人,前来“通好”。他们把兵仗刀剑藏在进贡的大蟧烛中,词机行事。可是,比及到京,胡惟腐已经仗法。因此,没敢行动。
刑部轮番鞠讯,林贤供认不讳。以伙同胡惟庸通倭的罪名,被灭了九族。妻妾、婢女则被收为官府奴婢。
这样,胡惟庵通倭案便铁板钉钉,罪不容诛。
不久,又“揭发出”了“胡惟庸通虏案”。“通倭”兼“通虏”,胡惟庸天理不容,可真是罪该万死了。新清查出来的“胡党”,更是在劫难逃!胡惟庸通虏案,同样是人证俱全。紧接着发布的《昭示奸党录》,刊登了封绩的供词:
封绩,常州府武进县人。幼系神童。大军破常州时祓百户掳做小厮,拾柴使唤。及长,有千户见绩聪明,招为女婧。后与矣家不和,被告发迁往南海住。因见胡丞相擅权,实封(上秘密奏幸)言其非为时,中书省凡有实讨到京,必先开视,其有言及己者,即匿不发,乃证罪其人。胡丞相见绩所言有关于己,匿不以闻。诈传圣旨,提绩赴京,送刑部鞫问,坐(判)死。胡丞相着人问道:你今当死,若去北边走一趙,便恍了你。绩应允。胡丞相差宣使送往宁夏耿指挥(忠)、于指挥(琥)、王指挥等处。耿指挥差千户张林、镇抚张虎、李用转送亦集乃地面。行至中途,遇鞑靼人爱族保哥等,给与马骑,引至和林,见詹兀不花丞相。詹兀不花令儿子庄家,送至哈剌章栾子处,将胡丞相消息备细告知,并着发兵扰边。待绩回奏后,将京城军马发出去,里应外合,成就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