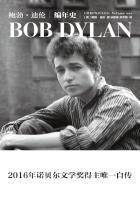今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为了庆贺盛世降临,今年的元宵灯会较之往年更加热烈火爆。临近奉天门外的几条街,是灯会的集中之地。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挂出了各种形状的五彩灯笼,方的、圆的、八角的、六方的、单层的、双层的、多层的、亭阁型的、宝塔型的、荷花形的、仙桃形的……盏盏争奇斗艳。有模拟动物的走马灯、盘龙灯、飞虎灯、卧象灯、凤凰灯、鸳鸯灯、金鱼灯……看得人眼花缭乱。还有模仿戏曲及神话传说的牛郎织女、钟馗嫁妹、西施浣纱、昭君出塞、吕布戏貂禅、千里走单骑、许仙与白娘子、猪八戒戏媳妇……更使参观者不愿移动脚步。每隔几十步,街中心还搭有一座彩坊,上面挂满了各种灯笼,宛如天宫仙阑,美不胜收。
—轮满月,斜挂在东南天际。探着一张白玉盘似的圆脸,俯瞰下界。街道两旁的屋顶上,树木上,都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银光。但今晚没有人去欣赏明镜耀辉的月轮。那明如白昼的灯光彩影,将挤满街道的人流的目光,完全吸引过去了。
走近五颜六色的彩灯前,人们方才发现,几乎每个灯上都有一条或者几条灯谜。谜旁悬赏,猜中者可以得到金钱或者物品奖励。奖品大到一坛酒,一匹布,小到毛笔、砚台、熏鸭、茶具、桃木梳、香荷包。
中国的谜语,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隐语、廋语,就是谜语前身。灯谜兴起于宋代,到元末更加兴盛。猜谜得奖,成了元宵佳节的一大雅趣。
摩肩接踵,人头攒动,十里长街成了人群的海洋。你推****,争看奇巧的灯彩。不少人驻足彩灯下,拍额蹙眉,挖空心思琢磨可以“射中”得奖的谜底。
在一座灯坊的下面,并肩站着两个绅士模样的人。个子一高一矮,高个子长脸准鼻,薄嘴唇上横着两撇八字短髭。身穿紫锻长衫,粉底薄靴。矮个子低额圆脸,下巴上挂着一撮山羊胡子,穿一身浅灰长衫。两人已经在这里站了一阵子。一只方型彩灯上的一则诗体灯谜,拴住了两人的脚步。那灯谜写的是:
开如轮,合如束,剪纸调骨护新竹。曰中荷叶影亭亭,雨里芭蕉声蔌簌。時天却阴阴却晴,二天之说诚分明。但操大柄掌在手,農尽东南西北行。
高个子对着诗迷沉吟了许久,仍然不得要旨。扭过头,用探询的目光望着身旁的矮个子。矮个子会意地一笑,伸出左手,用右手食指在掌心写出了谜底——“伞”。
这则灯谜,以诗论之,算得是好诗。若以谜论之,也堪称上品。它把伞的特征、功用、姿态、打伞人的动作等,描绘得准确生动、活灵活现。可以说诗中有谜,谜中有画,有声有色,有静有动。高个子连连点头,低声笑道:“这诗迷,端的是十分高明!”
不知他是赞美制谜的人,还是赞赏猜谜的人。只听矮个子发出了感叹:
“这制谜人,学问不浅呀。”
高个子分开观灯的人,继续往前走。矮个子紧紧跟在后面。
两人在一家黑漆大门前站住了。只见门楣上挂若两只八角彩灯,一只灯上写的一则灯谜煞是有趣:
倚阑干东君去也,眺花间红日西沉,闪多娇情人不见,闷淹淹笑语无心。
谜下悬着一吊铜钱,上面粘着一根纸条:“猜中者,取走此钱。”
高个子望着矮个子笑道:“这个容易。”
“哦?……猜中啦?”
高个子指着灯谜说道:“这‘阑’字去‘东’(“东”的繁体字与“柬”近似‘间’去‘日’,‘闪’去‘人’,‘闷’去‘心’,四句话不是都应在一个‘门’字上吗?”
“果然高明!哈哈哈——”矮个子赞赏地大笑。
“那咱该得赏了。”
高个子伸手要去取奖钱。矮个子拽拽他的衣襟低声说道:“这奖还是让别人得吧。前面的彩灯更好着呢。”
高个子一听,转身往前走去。
来到繁华的地段,有一座高大的彩坊横跨街上。彩坊底下围满了人,有的指着灯笼窃窃私语,有的拍掌哈哈大笑。两人近前一看,彩坊的正中,悬着一个巨大的圆型灯笼,上面有一则特别醒目的灯谜: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赤着一双特大的脚丫子,双手紧紧抱较一个大西瓜。悬的奖赏是:一坛绍兴陈酿。
高个子看了好一阵子,仍然不解。矮个子伸手扯他的衣襟,示意走开。高个子依然站在那里不动,一面固执地问道:“咦——他们笑什么?”“这……”矮个子欲言又止。
“咳,犹豫什么——说就是嘛!”
“这则灯谜,不怀好意。”矮个子耳语似的答道。
“哦?对谁不怀好意?”
“对咱们淮西人。”。
“怎么会是对咱们淮西人呢?”
矮个子指指画中女人的一双大脚:“这不是明摆着吗?”
高个子顿有所悟,猛地一跺脚,骂了起来:“混蛋——找死的东西!”见两人的举动引起了围观人的注意,矮个子急忙拉着高个子挤出人群,快步往北走去。
这两个人,一个是大明皇帝朱元璋,一个是左丞相、朱元璋信任的淮西人李善长。李善长是陪著皇上微服到街上观灯,与民同乐来的。至于紧跟其后的几十名观灯的人,则是化了妆的侍卫,不过没有人看得出来。
往前走了一阵子,朱元璋低声问道:“丞相,那灯谜,莫非是骂那些贪馋邋遢的女人?”
“臣以为,绝对是讥讽咱们淮西女人的。不然,为什么要画女人是一双天足呢?”
天下的女人多小脚,只有淮西女人天足多,朱元璋豁然开朗:“唔,有道理。那……灯谜的谜底该是什么呢?”
“臣以为是:‘淮西女人好大脚’!”
“狗娘养的!”朱元璋一挥拳头,骂起了粗话,“他们这是在骂马皇后呀!这些江南杂种,张士诚的孝子贤孙,至今仍然视新朝如同仇人——岂能容得!”
“陛下,不必生气。也许是臣的胡乱猜测。谜底未必是这样。”李善长抑制着兴奋,点拨道:“陛下不妨找个谙于此道的行家里手,推敲一番,看看谜底到底是什么。”
“大臣之中,哪个长于此道?”
李善长不动声色地答道:“陛下莫非忘了?刘基就是一个制谜的能手呀!”
“问他?”朱元璋摇起头来,“他未必跟朕说实话吧?”
“他要是不说实话……”李善长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哼!讥讽自己一向敬重的马皇后,就是骂到了皇帝的头上!李善长这么一点拨,朱元璋立刻对刘基产生了怀疑。
像前些日子惩治那些说皇帝“坏话”的老妪一样,第二天,朱元璋颁下一道口谕,将条街上的居民都捉起来杀了。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因为一则灯谜,这条街上的无辜百姓糊里糊涂全都做了屈死鬼。
自从进了应天,每当朱元璋要无端杀人,不论是冤杀大臣,还是残杀无辜百姓,善良的马皇后总是极力加以劝阻。无奈,常常被他用种种理由搪塞过去,甚至用“女人不得干政”顶撞回去。但马娘娘仁慈舍德的美名,仍然不胫而走,在朝廷内外传为美谈。那个灯谜的制作人所奚落的对象,未必就是马皇后,更大的可能是反映了江南文人对淮西暴发户的嫉恨和蔑视。因为淮西将领的原配夫人中,天足者大有人在。要说戏弄的是这些淮西高髻,则未必是诛心之论。李善长借着一则灯谜,巧妙地将刘伯温端出来,正是这种矛盾斗争的反映。因为要想抓到刘基别的把柄,并非易事。李善长与刘伯温的矛盾,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建国之初。
谓淮西暴发户,是指那些追随朱元璋征战厮杀的红巾军弟兄。他们生长在淮西,无一不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庄稼汉。十余载战场拼杀,出生人死。战死者弃尸沙场,幸存者蛾冠博带。他们的荣耀和富贵,完全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而文士集团则不同,他们大多是胜利渡江后投奔而来,也有不少趦开国后征召来的。他们今天的高官厚禄,可谓是无为得福,无功受禄。但在他们眼里,那帮鹑衣百结的穷汉贱妇,尽管成了光耀天下的公侯,仍然不过是沐猴而冠,不屑一顾。
早在立国之前,浙江崇德有一位名叫贝琼的诗人,就曾写诗感叹:
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园可避秦?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鬌半淮人。
短衣楚客(指淮客)依靠马上征战夺得功名富贵,家中的大脚婆娘自然就成了招摇过市的高髻贵妇。足见武夫们的飞扬跋扈,已经使得儒生们十分反感。不过,江南文士所凭借的,仅仅是知识优势。舌底与笔下的优势,在武人集团的刀剑和显赫的地位面前,无异于以卵击石,根本不堪一击。
李善长就颇受这种矛盾对抗的影响。他是淮西旧人,但又是一个读书人,既有知识,又有战功,兼具南北双方的优势。照理,应该起到协调与弥缝作用。但是,在中书省这个文人齐集的地方,他却感到非常孤立,似乎始终处在南方文人的包围与挤压之中。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势,他便尽量拉拢淮西文人和中下级官吏,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削弱和打击江南籍上层官员。南方人自然不肯任凭挤压甚至宰割。于是,派系林立,各怀成见,狗嘶猫咬,矛盾不断,把一个中书省折腾得乌烟瘴气。
埋在深层的地火,总是会冲出地面的。李善长与刘基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洪武元年五月,朱元璋到汴梁巡视,同时部署北伐机宜。他命左丞相李善长和御史中丞刘基留守京城。临行前,朱元璋特意召见刘基,心诚意挚地嘱咐道:
“中丞,朕离京期间,你尽管放手地干:督察奸恶,整肃朝廷,连宫内的事,也可予以纠察检举。”
刘基感动地答道:“陛下的重托,微臣一定戮力而为。陛下尽可放心地北上。”
“好。朕就放心啦!”
皇帝如此信任,怎能不竭尽忠诚?何况,刘伯温一直主张,新朝初立,应该有个良好的开端,奖善伐恶,严肃法纪,以纠正自宋元以来,对官吏放纵优容所造成的吏治腐败。于是,他命令御史们认真纠察,对不法官吏和事件,一律奏闻弹劾。宮内侍卫和宦官如有违纪犯法者,则及时禀告皇太子加以处置。这样,弹劾官吏违纪的奏章,雪片似的飞到了御史台衙门。
李善长坐不住了。他认为刘伯温的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是冲者自己和中书省来的,甚至怀疑,这是刘基代表江南文士集团的一次反扑。可巧,他的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贪赃枉法的事实被揭露出来,李善长赶忙去刘府,当面说情。
刘伯温知道他无事不登三宝殿,献茶之后,主动问道:“丞相公务繁忙,屈驾来访,谅必有所教诲。在下当洗耳恭听。”
“哈哈,中丞大人太客气了。”李善长皮笑肉不笑,“老夫是特地向刘大人请教来的。”
“不敢,不敢。丞相有何教诲,不妨径直说来。”刘伯温彬彬有礼。“中丞大人,都事李彬被抓起来,有据可查吗?”
“大人,李彬的案子已经审结,贪赃枉法,证据确凿。”
“真的是这样吗?”
“丞相放心,对李彬并没用刑。在证据面前,他本人只能如实招认。”“这么说,是供认不讳啦?”
“正是。”
“中丞打算如何处置?”
“李彬罪行严重,按律当斩。”
“不能通融些吗?”
“不能——那厮罪不容诛!”
李善长沉吟了一阵子,痛恨地说道:“那厮竞然在老夫的眼皮子底下作荸,真是罪不可恕!”李善长这句话的潜台词,仍然希望刘伯温看在他的面子上予以通融。
“好,有了丞相的谅解,卑职就可以从公而断了。”刘伯温顺水推舟,故意装糊涂。
“不过,眼下江南大旱,如开杀戒,只恐与祈雨不利呀。”
“正相反——杀了恶人,天公喜悦,必降甘霖。”
李善长满脸愠色:“中丞大人,这么说,李彬是死定了?”
“是的,无法宽恕,应当立即正法。不过,眼下皇上在外巡视,还要听从圣旨定夺。”
李善长说情碰了壁,愤愤离去。
铁面无私的刘伯温,竞然没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左丞相留面子。事后想想,害怕被李善长抓住辫子,立即派飞骑呈报朱元璋,请诛李彬以肃法纪。朱元璋一向最为痛恨贪贿之徒,当即作了批复。刘伯温接到圣旨,立刻将李彬正法。从此,他与李善长的矛盾更深了。
八月,朱元球御驾返京。李善长一再攻击刘基专横跋扈,那些受到惩戒的官宦们也纷纷说刘伯温的坏话。无奈,刘伯温的所作所为,都是朱元璋临行前所嘱托的,而用御史台牵制中书省,正是朱元琢的本意。现在两家撕咬起来,正是他希望看到的。
不过,刘伯温的智糖计谋,就像他的满脸落腮胡子,多得不可胜数。相形之下,自己这个圣明天子,简直就是一个愚笨的后生。这不能不成为朱元璋的一块心病。如今天下平定了,皇帝的龙墩坐稳了,智谋韬略不亚于孔明的刘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韬略智谋,不但失去了用武之地,他的超人智蒽,非凡的能力,反而成了遮挡灼灼皇冠的一片阴影。
“看来,刘基与李善长一样,都是要不得的。”捻着胡子梢,朱元璋暗暗在心里叨念。
武元年秋,肆虐了半年之久的旱情,仍然没有解除的迹象。
焦急的朱元璋把怨气发泄到御史台身上。不知听从了什么高人的指点,他一口咬定,是御史衙门的御史,以及在外面巡按的御史昏聩庸懒,冤枉百姓,触怒了上天的缘故。遂将在外公干的巡按御史何士弘等逮回京城,捆缚在马房里,等候处理。同时下达命令,朝臣一律上书言事,检讨在哪些地方得罪了上天。
心地坦荡的刘基,并不知道皇帝对自己已经心生嫌隙,仍然一如既往,揆情度理,连夜上书,贡献自己的“陋闻拙见”。他一共奏了三件“有违天意”的事:
第一,战争期间阵亡的将士,他们的妻子一直安置在“寡妇营”里集中居住。数万未亡人圈在一起,既不能出嫁,又不得与家人团聚,阴气郁结,怨尤凝聚;第二,修城建宫殿时死亡的工匠,尸骨暴露荒野,至今未得安葬,第三,张士诚的降卒,全部沦为被管束的军户。所有这一切,不仅有损于圣朝的仁爱与德治,更有违上天好德之意。
刘基的条陈,条条在理。朱元璋只得接受,马上发布命令:寡妇听从改嫁,不愿改嫁者,送还原籍或投掭亲故;死亡的工匠,由官府代为葬埋;所有服役降卒,一律释放回家;张士诚部投降的头目统统免于充军。
害怕上天示警的朱元璋,情急之下,不但给了刘基极大的面子,而且再一次表现了从谏如流的广阔胸怀。
倘若近期内天降甘霖,庶几乎可以平息朱元璋的焦灼。孰料,老天爷并不理会他的祈求与诚意。半个多月过去了,旱魃照常肆虐。沟溏干涸,禾稻枯死,农夫的一颗心,宛如在烈火上烘烤。朱元璋更是焦躁得近乎疯狂。他觉得,刘伯温欺骗了自己,立即传来责问。
“你说,上天示警,方才殃及百姓。为什么朕——改正了,仍然滴雨不降?你胡乱狂吹,当负什么罪过?”
“臣本以为,陛下做了三件好德之事,自会平息上苍的怒气。”刘基极力平静地回答,“眼下旱情持续,也许还有其他惹怒上苍的地方。”
“刘基,你是在嫁祸于人!”
“微臣不敢。”刘伯温急忙跪到地上,“多年来,微臣得到皇上信赖,自知并非事事独具灼见,之所以屡屡知无不言,无非是一片血诚使然。”
“哼!你的知无不言,只能给朕躬添烦!”朱元璋在地上大步踱着。“你还有什么高见?”
“罪过,罪过。”刘伯温只能自怨自艾,狠狠地在方砖地上撞脑袋。皇帝无故迁怒,使刘伯温痛切地感到,自己已经成了多余的人。继续流连朝堂,凶多吉少。于是,他伏在地上,唏嘘奏道:
“陛下,微臣有一事启奏,不知当讲不当讲?”
“有事就奏,不必绕弯子!”朱元璋冷冷地回答,然后重重地坐回到龙椅上。
“陛下,微臣的老荆,近日病逝。恳请皇上准假,回去料理丧礙。”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讣告已经到达五天了。”
“为什么今日才上奏?”
“皇上正为祈雨忧心,此乃区区私家小事,微臣不敢给皇上添乱。”
刘伯温的回答,使朱元璋听来很舒服。他轻叹一声说道:“丧妻不是小事,朕准你回乡料理丧事。”
“谢陛下。”刘伯温又磕了一个响头。
刘伯温想不到,这么容易便轻易抽身,赶忙收拾行李,连夜离开了京城。
不料,刘伯温前脚刚离开应天,朱元璋紧跟者便下达了一道圣谕:“着刘基还乡料理妻丧。御史台、按察司各官,全部自驾船只,发往汴梁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