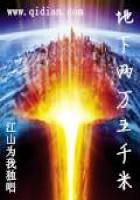“陛下君临天下,扬威四海,臣下岂敢乱了纲常礼仪。”徐达诚惶诚恐。“快快起来,今日是私宴,不谈国事,只叙兄弟情谊。”朱元璋将徐达搀起来按到座位上。
“那,岂不是太放肆了?”徐达又站了起来。
“坐稳,是朕赐座!”
“臣谢坐。”徐达偏着身子坐了下来。
朱元璋这时才注意到,徐达的两眼微肿,脸色僬悴。看来,常遇春的暴亡,给这位患难兄弟,增添了深深的悲伤。近年来,两人多次发生龃龉和矛盾。在是否穷追逃亡的元朝皇帝和封闭大都皇宫这两件事上,两人竟然闹翻了脸。常遇春为此特地向自己告过徐达的状。但,他在心里各打五十大板:认为两个人都有错。
徐达封了元朝皇宮的大门,把金银珠玉、珍宝古玩,分毫无损地献给了朝廷,自己毫不染指,这是多么难得的廉洁与自律。徐达从上千名宫女中,挑选了一百名绝色少女留下来,毫发未损地统统运回应天,献给了自己。其余的该遣散的遣散,不该遣散的给将士们做了小妾,他自己竟然一个没要。这样的柳下惠、铮铮铁汉哪儿找去?他对朕躬是何等的忠诚呦!朱元璋不满意的是,徐达办事不知机变。如果当时准了常遇春的请求,派数千人的一支轻骑,穷追逃亡的元顺帝,也许能斩草除根,不至于留下北方的祸乱。当时,他真想将徐达从北方前线调回来,训斥一番,甚至严加惩处。忽然想到,自己曾经当面说过,元运已衰,穷寇勿追的话。如果为此处置徐达,岂不是言而无信、嫁祸于人?朱元璋虽然打消了惩诫的念头,但心里始终结着一个疙瘩。可是,徐达对自己不仅无可挑剔,忠诚如一,他对常遇春的哀痛,也使人十分感动。想到这里,朱元璋把憋在心里许久的话,爽快地说了出来:
“朕听说,大都刚刚收复时,你曾与遇春有过一次争吵。不知为了何事?”他故作不知。
“呀!吵架的事皇上果然知道了!”徐达不由一愣,旋即平静地答道:“为是否该追胡元皇帝,我们两个几乎吵翻。臣以为将帅之间,有分歧乃属常事,故而没有禀报。陛下恕臣隐匿不报之罪。”徐达离坐要下跪。
“坐好,不要动!”朱元璋平静地说道,“我要治你的罪,还用等到今天吗?今日是闲聊,朕不过是旧话重提罢了。”
“谢陛下宽恩。”
“谢什么?朕本来就没有放到心上嘛。”朱元璋扯起谎来神色平静得很,“喂,天德,你知道不知道,开平王不但跟你这位主帅吵了架,还向朕躬告了你一状?”
“不知道。但臣并不感到意外。”
“你还记恨开平王吗?”
“两人都是出自公心,为什么要记恨?再说,遇春性情暴躁,臣更不会跟他计较。”
宽大的胸怀,凜凜的正气,朱元璋颇有自愧弗如的感觉,但他仍然没有打消心头的疑虑。
“天德,你的两只眼睛,为何如此红肿?”
“刚才又去开平王府吊唁了一通,不由得落下了恨泪。”徐达声音哽咽,“遇春刚刚四十岁呀,正是为大明朝出力的好时候,上天怎么就把他叫了去呢?”
“唉!朕何尝不是万分难过。不过,人已死去,痛伤何用,爱惜自己的身子要紧哪。”
“是,陛下。”
“天德,朕想问你一件事,你能说实话吗?”
“陛下!”徐达又是一惊,急忙站起来回答,“凡是臣知道的,一定如实柬报。”
“坐下,听我说。”朱元璋指着徐达的眼睛问道,“天德,你为老友开平王,连眼睛都哭肿了。”
“臣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眼泪。”
“怕是还有别的什么伤心事吧?”
“不,不。臣功微赏显,高兴都来不及,怎么还会有伤心事呢?”
“嘿嘿,刚刚说过如实禀报,立刻就隐瞒起心事来了。”
“臣不敢!”
“嘿嘿,你不说,朕也知道。一定是那位谢夫人,又向你发过虎威,是吧?”
“那……”徐达第三次怵然而惊。前天夜里夫人才与他发生口角,皇帝怎么今天就知道了?他惶怵地答道:“陛下,谁家也有本难念的经——夫妻之间,争争吵吵都是难免的。”
“我所倚信的大功臣,竟然在一个女人的淫威下讨生活——真真岂有此理!”
“陛下,谢氏无知浅薄,性情暴躁,不值得跟她一般见识。”
“可是,天长日久,胡搅蛮缠,你就能忍受得了?”见徐达低头不语,朱元璋继续说道,“我知道你这几天心里不快活,故而特备酒宴,我们喝个痛快。”
朱元璋心里暗暗高兴:徐达的心事果然被猜中了。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垒块。原来他是借着哭祭常遇春,发泄淤积于内心的憋屈呀。
不瞒陛下,臣心绪不佳,没有酒兴。”
“咦——正是因为心绪不佳,才要借酒消愁呢。朕不是同样不爱酒吗?今天朕是舍命陪君子,咱们来个一醉方休。明天,朕就帮你把那解不开、挣不脱的忧愁,一股脑儿驱除干净!”
举杯消愁愁更愁。徐达不相信借酒能够消愁,更不理解,皇上怎么能够给自己把忧愁驱除干净,而且就在“明天”!但他不敢问,更不敢违拗圣意,只好强作笑颜地答道:
“有幸陪伴陛下饮酒,乃是微臣的荣幸。”
朱元璋扭头吩咐:“来呀,酒宴摆下。”
酒过三巡,朱元璋兴致勃勃地说道:“你给我献来的一百名宮女,我挑选了十六名,教她们歌舞,已经学会了几出,今日让她们试演一番,给我们侑酒取乐如何?”
徐达心里无兴致,正想找借口辞谢,话没出口,一队歌伎已经列队登场。
乐曲悠然而起,舞伎踏乐起舞。十六位舞伎,个个面如仙子,身轻如燕。薄罗轻绡掩不住丰乳细腰,俯仰回旋更显露玉臂纤指……
不谙弦歌酒色的徐达,第一次看到这美妙的歌舞,耀目的美姝,开始是痴痴地注视,继而忘情地击节赞赏……
由于他是打横坐在朱元璋的旁边,一切细微的表情,都没有逃过朱元璋的眼睛。
“天德,”朱元璋低声问道,“你看,这歌舞如何?”
“喷啧。臣从未见过如此美妙的歌舞——今日大开了眼界!”
“你看,她们面貌身材如何?还能看上眼吗?”
“陛下,岂止是能看上眼,简直个个赛过月里嫦娥、瑶池仙子!”徐达忘了掩饰。
俗话说,天下的英雄爱美人。一向不喜欢“腥荤”的硬汉子,在美女们的淸歌燕舞、红袖紫裙飘拂下,照样目迷旌摇。朱元璋看看时机到了,大手一挥,歌伎悄然退下。笑眯眯地问道:
“天德,这么说,你也喜欢看她们?”朱元璋故意把“歌舞”二字隐下了。
“这么好看的歌舞,怎么能不喜欢看呢?”徐达没有听出皇帝的言外。
“好。那就让你天天看,看个够。如何?”
“陛下国事繁剧,微臣岂敢天天前来打搅。”
“为什么非得进宮来看?不可以在右丞相府上看吗?”
“不瞒陛下,臣的府上并没有歌伎。”
“把她们带回去不就有了吗?你知道,朕并不喜欢歌舞。之所以训练她们,就是准备赐给你们这些大功臣的。”
徐达一时愕然:“陛下的意思是,把她们赐给微臣?”
“是呀。怎么,你不愿意?”
“陛下的厚赐,微臣焉能不愿意。不过……”
“说下去!”
“臣常年领兵征战四方,哪有时间看歌舞呀。”
“等到把王保保那个汉人的叛逆消灭掉,也就没有多少仗可打了。你也该留在京城享点淸福了。拼杀大半生,为的是什么?不就是等待这一天到来吗?”
“不瞒陛下,臣对她们——女人,并不感兴趣。”
朱元璋佯怒道:“咦?刚才还说,她们比月里嫦娥、天宮仙子还好看,一转眼便改了嘴。难道连欺君之罪都忘了?”
“微臣不敢。”徐达离座跪到了地上。“臣是说……是说,不想把她们带回府去。”
“言不由衷!圣人都说:食色,性也。文王乃是大圣人,后宮嫔妃成群,给他生了一百多个儿子。史家并未对他的‘百子千孙’有何疵议。汉高祖自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但汉祚绵延了四百多年。元主隳坏纲纪,醉生梦死,亡国丧邦,也并非是色之过,而是无道所致呀。”
“臣觉得,有一个女人足矣。所以,并不喜欢再有别的女人在身边。”“哼!自古天下英雄爱美人。我就不信你能例外。不用说,是那只母老虎把你给镇住了。快起来吧!”
“……”徐达坐回到座位上,不知如何回答。
“我听说,那疯婆娘常常跟你争吵,夜间甚至把你关在门外,不准进她的卧室。你这统帅千军万马的长胜将军,怎么就制服不了一个奥女人呢?难道,怕她吃了你?”
“不是怕,是臣不屑于跟她一般见识。”
“哼,这已经不是寻常的事情!我劳苦功高的大将军,竟然天天受一个女人的欺负、折磨,真真的岂有此理!此事朕不能不管!”
“陛下千万不可为此劳神,是臣有失教海的罪过。往后,一定对她加意教诲就是。”
“你要是能够教诲得了,她何至于如此张狂?别开口,等朕把话说完。有其父必有其女,她跟谢在兴那个坏种一样,竟然不知天高地厚,不只是虐待你,连朕她都敢当众辱骂!”
“啊,有这等事?”
“你常年在外面打仗,谅不知情。你那个狼心狗肺的老丈人,在张士诚完蛋时,被一起抓了来。朕本想给他一碗饭吃,可是,他不但毫无悔过之意,竞说是朕逼得他走上了反叛之路。没办法,朕只得成全了他。你那个疯女人,摆酒给他送行也就罢了。竟然跑到法场上,当着成千上万的人,大骂朕躬‘逼走了同患难的弟兄,还要杀死他。他的女婿在前线为他卖命,他却在这儿杀他的老丈人——忘恩负义,狼心狗肺!’天德,你说,这样的女人不是死有余辜吗?”
“陛下,看在一双未成年儿女的份上,饶她一命吧!”徐达流着泪恳求。
“也罢,只要她从今往后,谨遵妇道,不再恶意辱骂朝廷,看在你的面上,我饶她一命!”
“谢陛下。”徐达再次跪到了地上。
“快快起来。”朱元璋扶起徐达,安慰道,“别尽说些煞风衆的话,还有一件高兴的事忘了告诉你。朕要封赏给众功臣的‘丹书铁券’,伯温先生已经监造完毕,这是仿照宋太祖的古制。正面镌功臣的功勋,恩赏,以记其功;中间镌免罪减禄的数目,以防其过。一共铸了九十七副,每副分左右券,左券颁赐功臣,右券存于内府,左右相合以为佐证。你看一看铁券吧!”
内侍捧来一枚铁券,内外都是明黄色,左右卷曲似一片厘瓦。朱元璋指着说道:“按照爵位大小,铁券分作七等:公爵分二等,一等高一尺,宽一尺六寸五分;二等高九寸五分,宽一尺六寸,侯爵分三等,伯爵分二等,依次类推,尺寸递减,最小的高六寸五分,宽一尺二寸五分。”
“庄重大方。”徐达望着铁券,点头称赞,“陛。下将丹书铁券奖赏功臣,可谓是恩重千钧!”
“朕不仅要赏你们这些大功臣丹书铁券,还要在鸡鸣山建功臣庙,生者死者都要人庙受飨祭。”
“怎么?活着的功臣也要入庙?”徐达大惑不解,“那……”
“不吉利,是吧?你忘了帝王生前大造陵寝,百姓家也是未死而大做其棺木。这正是免灾延寿、大吉大利的事情呀!”
“活着受人祭拜,终有隔世之感。不过,死后能跟众位功臣在一起,倒也不寂寞。”
“那是呀!朕要让千秋万代永远记住大明朝的开国元勋!”朱元璋得意地摇着长下巴,“天德,时候不早了,你也该回府了。回去晚了,当心母老虎不让你进房上床呦。”
达回到右丞相府,谢夫人便迎上前来,没等徐达开口,谢氏便审问似的问道:
“今日又去了哪儿,喝得一张脸赛过关老爷?”
“今日陛下赐宴,作臣子的焉能不尽。”
“听说朱元璋身边好看的女人成群,没让出几个美人来陪陪你?”“没,没有。”
“没有?你能喝成这么个糟模样?他不是说,不稀罕陪人喝酒吗?原来也是个大酒鬼!”
“你!对皇上,岂能如此说话!”
“哼!他杀我爹的时候,我当着成千上万的人,骂他忘恩负义。他也没敢把我怎么样!”
“咳!你这人就是听不进劝。如此胡来,总有一天要吃大亏的!”
“我要是怕他,就不骂那没良心的啦。哼!我的丈夫拼死拼活给他打下了天下,他自自在在地做皇帝……”
“住口!”徐达愤怒地打断了谢氏的话。
正在这时,家人来报:圣旨下。
徐达猛吃一惊。刚刚见过皇上,并没有说有别的事情,怎么一转身就来了圣旨?眼前并没有特别紧急的军情呀。徐达顾不得多想,急忙吩咐摆下香案接旨。全家人一齐跪到地上听宣。徐达万万没想到的是,奉旨太监所宣读的,竟是这样的内容: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论达南征北战,功勋卓著,以往封赏,仍不足以称朕之意。特賜敬贤惠的宫人两名,收房为妾,侍奉枕席徐达望诏鉗恩。
“万岁,万岁,万万岁!”徐达带领全家人一齐谢恩。
徐达听出来,自己惊讶得声音都变了。方才在宫内,皇帝要把歌伎送给徐达,他还以为是开玩笑,想不到,真的把两个他曾经多看了几眼的歌伎,赐给了自己!
皇帝恩赐的东西,哪怕是一粥一饭、半丝半缕,都是莫大的荣耀和恩典,何况是两个美如天仙的姑娘!但今天的恩赐,不啻是徐家的一场灾难。
徐达久久愣在那里。连请太监落座喝茶,都差一点忘记。对于谢氏来说,更不啻是一声轰顶的霹雳。奉旨太监一走,她便当着两个女子的面,气咻咻地向徐达质问:
“他这是什么意思?”
“你说谁?”
“还有谁——你们的好皇帝呗!”
“你怎么还用这样的口气说皇上?”
“老娘不骂他,就是给了他天大的面子!”谢氏两眼含泪,胸膛起伏,“他什么不好送,偏偏要送女人?这不是诚心地要害死人吗?”
“有两个女人在身边,就能出人命?再说,皇上赐给女人的大臣,不止是我一人。人家不都活得好好的吗?”
“哼,人家是人家,你是你。你连一个女人都不能让她满意,再弄两个害人精回来,还不得早早要了你的小命!”
“你,如此不通情理!”徐达终于忍不住了,“你到底想干什么?”“马上把这两个贱货给他退回去!”
“要退你去退——我可不敢抗旨。”
“我没法活了哇!”谢氏一屁股坐到地上,放声大哭,“老天爷呀,我的命好苦呦!啊啊啊……”
徐达慌了手脚,急忙连拖带抱地拉她起来,扶到了内室里。
过了好一阵子,谢氏方才抽抽嗒嗒地说道:“你既然不敢把她们送回去,我就收下她们。不过,这是我的家,她们处处得听老娘我的!”
“那还用说吗。”徐达急忙借台阶下驴。他扭头一看,远远站在一旁的两位姑娘,一个低头揩泪,一个满脸愠色。急忙招招手:“你们两个,还不快快过来见过夫人。”
满脸泪痕的姑娘率先走过来,施礼说道:“柳儿给夫人请安。往后,望夫人多多指教。”
另一个一脸愠色的姑娘,名叫玫瑰,她慢慢地近前来,把柳儿的话,重复了一遍。
谢氏望着两个陌生姑娘,恶狠狠地说道:
“往后,你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看我的眼色行事。要是有半点违犯,休怪我手下无情。”
“夫人说的是,俺们不会违犯的。”柳儿急忙作答。
“玫瑰,你哪,怎么不说话呀?”
玫瑰用偁硬的口气答道:“夫人尽管放心,该遵依的,俺也决不会违犯。”
“什么,该遵依不该遵依?告诉你,我是一家之主,不论什么话,都是圣旨,你们都得乖乖地遵依!”
“夫人玫瑰冷笑道,“俺们是皇上派来侍奉右丞相的,不是你的使唤丫头。要知道,皇上可是一国之主,他的话才是圣旨哪!”
“你看,你看!”谢氏怒视着丈夫,“她们刚刚进门,就这么狗仗人势
地朶畚皇帝来历我!往后,这个家,我可怎么当呀!啊啊啊……”谢氏再次放声大哭。
“好啦,有话以后慢慢说。”徐达克制着愤怒扭头吩咐,“搀扶夫人回后堂去,给两位新来的姨娘,收拾房间让她们好好安歇。”
当天晚上,徐达来到了两位姑娘的住处。玫瑰在低头生闷气,柳儿虽然止住了哭泣,可也是满脸忧戚,心事重重。看到徐达进了房间,两人急忙起来让坐。柳儿未语先流泪:
“相公,她当著你的面,都那么凶,你出征不在家的时候,俺们姐妹可怎么过呀?”
“柳儿,不必害怕,夫人就是这么个脾气。你们是皇上赐来的人,只要处处当心,谅她不敢越轨行事。”见柳儿的双眼湿润了,徐达急忙用衣袖给柳儿揩着泪,“我要是外出,就把你们都带上。”
“相公!”玫瑰愤愤说道,“早知道会这样,俺就是死,也不肯来。”“唉!玫瑰呀,看在我的面上,千万不能跟她一般见识。”徐达把姑娘拉到怀里,“宰相肚子里能撑船,你也得多克制自己。古语说,能忍自安,你说是吗?”
“要是忍不住呢?”
徐达无言以对。过了许久方才痛苦地说道:“唉!忍不住也得忍。摊上这么个……大概是命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