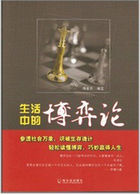然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前几天,在医院里,我见了冯先生最后一面。他虽然还活着,然而已经不能睁眼,不能说话。我顿感毕生知己又少一个。我坐在会客室里,泪如泉涌,我准备放声一哭。他的女儿姚平连卢说:“季伯伯!你不要难过!”我调动起来了自己所有剩余的理智力量,硬是把痛哭压了下去。脸上还装出笑容,甚至在泪光中做出笑脸。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的泪都流到肚子里去了。为了冯至先生,我愿意把自己泪库中的泪一次提光,使它成为我…生中最后的一次痛哭。
呜呼!今生已矣。如果真有一个来生,那会有多么好。
悼组缃
在30年代的第一年,我就认识了组缃,当时我们都在清华大学读书。岁数相差三岁,级别相差两级,又不是一个系。然而,不知怎么一来,我们竟认识了,而且成了好友。当时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林庚和李长之,可以说是清华园“四剑客”。大概我们都是所谓“文学青年”,都爱好舞文弄墨,共同的爱好把我们聚拢在一起了。我读的虽然是外国语文系,但曾旁听过朱自清先生和俞平伯先生的课。我们“四剑客”大概都偷听过当时名噪一时的女作家冰心先生的课和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先生的课。结果被冰心先生板着面孔赶了出来;和郑振铎先生我们却交上了朋友。他同巴金和靳以共同创办了《文学季刊》,我们都成了编委或特约撰稿人,我们的名字也堂而皇之地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
我们“四剑客”是常常会面的,有时候在荷花池旁,有时候在林荫道上,更多的时候是在某一个人的宿舍里。那时我们很年轻,我的岁数最小,还不到20岁,正是幻想特多、不知天高地厚,仿佛前面的路上全铺满了玫瑰花的年龄。我们放言高论,无话不谈,“语不惊人死不休”。个个都吹自己的文章写得好,不是妙笔生花,就是神来之笔。
我们会面的地方,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工字厅。这是一座老式建筑,里面回廊曲径,花木蓊郁,后临荷塘,那一个有名的写着“水木清华”四个大字的匾,就挂在工字厅后面。这是一个非常清静的地方,平常很少有人到这里来。对我们“四剑客”来说,这里却是侃大山(当时还没有这个词儿)的理想的地方。我记得茅盾《子夜》出版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又凑到一起,来到这里,大侃《子夜》。意见大体上分为两派:否定与肯定。我属于前者,组缃属于后者。我觉得,茅盾的文章死板、机械,没有鲁迅那种灵气:组缃则说,《子夜》结构宏大,气象万千,这样的辩论向来不会有结果的。不过是每个人淋漓尽致地发表了意见以后,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又谈起别的问题来了。
组缃上中学时就结了婚。家境大概颇为富裕,上清华时,把家眷也带了上来。有了家眷,就不能住在校内学生宿舍里,他在清华附近西柳村租了几间房子,全家住在哪里。我曾同林庚和长之去看过他。除了夫人以外,还有一个三四岁的女孩,小名叫小鸠子,是非常聪慧可爱的孩子。去年下半年,我去看组缃,小鸠子正从四川赶回北京来陪伴父亲。她现在也已60多岁,非复当日的小女孩。我叫了一声:“小鸠子!”组缃笑着说:“现在已经是老鸠子了。”相对一笑,时间流逝得竟是如此迅速,我也不禁“惊呼热衷肠”了。
清华毕业以后,我们“四剑客”,天南海北,在茫茫的赤县神州,在更茫茫的番邦异域,各奔前程,为了糊口,为了养家,在花花世界中,摸爬滚打,历尽苦难,在心灵上留下了累累伤痕。我们各自怀着对对方的忆念,在寂寞巾,在沉默中,等待着,等待着。…直等到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组缃和林庚义都来到了北大,我们这“三剑客”暌离20年后又在燕园聚首了。此时我们都已成了中年人,家事、校事、同事,事事萦心。当年的少年锐气已经磨掉了不少,非复昔日之狂纵。燕园虽秀美,唯独缺少一个工字厅,缺少一个水木清华。我们平常难得见一次面,见面大都是在校内外召开的花样繁多的会议上。一见面,大家哈哈一笑,个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也。
时光是超乎物外的,它根本不管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从无始至无终,始终是狂奔不息。一转瞬间,已经过去了40年。其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中国的老知识分子无不有切肤之痛,大家心照不宣,用不着再说了。我同组缃在牛棚中做过“棚友”,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终于都离开了中年,转入老年,进而进入耄耋之年。不但青年的锐气消磨精光,中年的什么气也所剩无几,只剩下一团暮气了。幸好我们这清华园“三剑”(长之早已离开了人间)并没有颓唐不振,仍然在各自的领域里辛勤耕耘,虽非“志在千里”,却也还能“日暮行雨,春深著花”,多少都有建树,差堪自慰而已。
前几年,我同组缃的共同的清华老友胡乔木,曾几次对我说:“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我颇惊其伤感。前年他来北大参加一个什么会。会结束后,我陪他去看了林庚。他执意要看一看组缃,说他俩在清华时曾共同搞过地下革命活动。我于是从林庚家打电话给组缃,打了好久,没有人接。并非离家外出,想是高卧未起。不管怎样,组缃和乔木至终也没能再见一面。乔木先离开了人间,现在组缃也走了。回思乔木说的那一句话,字字是真理,哪里是什么感伤!我却是乐观得有点可笑了。
我默默地接受了这个教训,赶在组缃去世之前,想亡羊补牢一番。去年我邀集了几个最老的朋友:组缃、恭三(邓广铭)、林庚、周一良等小聚了一次。大家都一致认为,老友们的兴致极高,难得浮生一夕乐。但在觥筹交错中,我不禁想到了两个人:一是长之,一是乔木,清华“剑客”于今飘零或广陵散矣。我本来想今年再聚一次,被邀请得范围再扩大一点。哪里想到,如果再想聚的话,又少了一个人:组缃。暮年老友见一面真也不容易呀!
不管我还能活上多少年,我现在走的反正是人生最后一段路程。最近,若干年来,我以忧患余生,渐渐地成了陶渊明的信徒。他那形神相赠的诗,我深深服膺。我想努力做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我想努力做到宋人词人所说的“悲欢离合总无情”。我觉得,自己努力并没有白费。我对这花花世界确已看透,名缰利锁对我的控制已经微乎其微。然而一遇到伤心之事,我还不能“总无情”,而是深深动情,组缃之死就是一个例子。生而为人,孰能无情,一个“情”字不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那一点儿“几稀”吗?
有·件事却让我触目惊心。我舞文弄墨60年于兹矣。前期和中期写的东西,不管内容如何,不管技巧如何,悼念的文章是极为稀见的。然而最近儿年来,这类文章却逐渐多了起来,最初我没有理会。一旦理会到了,不禁心惊胆战。一个人到了老年,如果能活得长一点,当然不能说是坏事。但是,身旁的老友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自己,宛如郑板桥诗所说的“删繁就简三秋树”,如果“简”到只剩下自己这一个老枝,岂不大可哀哉!一个常常要写悼念文章的人,距离别人为自己写悼念文章,大概也为期不远了。一想到这一点,即使自己真能“不喜亦不惧”,难道就能无动于衷吗?
但是,眼前我并不消极,也不颓唐,我绝不会自寻“安乐死”的。看样子我还能活上若干年,我耳不聋,眼不昏,抬腿就是十里八里。王济夫同志说我是“奇迹”,他的话有点道理。我计划要做的事,其数量和繁重程度,连一些青年或中年人都会望而却步,借用冯友兰先生的话,我是“欲罢不能”。天生是辛劳的命,奈之何哉!看来悼念完还是要写下去的。我并没有老友臧克家要活到120岁那样的雄心壮志。退而求其次,活到几十多,大概不成问题。我还有多少悼念文章要写呀,恐怕没有人敢说了。
3.深情古谊,淡而弥厚,清而弥永
潘天寿
潘天寿,(1897~1971)字大颐,号寿者,浙江宁海人。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其艺术博采众长,形成个人独特风格。作品笔墨苍古、凝练老辣,具有摄人心魄的力量感和现代结构美。著述有《中国绘画史》、《听天阁画谈随笔》等。
我在27岁的那年,到上海任教于上海美专,始和吴昌硕先生认识。那日寸候,先生的年龄,已近80岁了,身体虽稍清瘦,而精神很充沛,每日上午大概作画,下午大概休息。先生平易近人,喜谐语,在休息的时间中,很喜欢有朋友和他谈天。我与昌硕先生认识以后,以年龄的相差,自然以晚辈自居,态度恭敬,而先生却不以此而有距离,因此谈诗论画,请益亦多。回想种种,如在眼前——一·种深情古谊,淡而弥厚,清而弥永。真有不可语言形容之概。
有一天下午,我去看吕硕先生,正是他午睡初醒之后,精神甚好,就随便谈起诗和画来。谈论中,我的意见颇和他的意趣相合,他很高兴。第二天就特地写成一副集古诗句的篆书对联送给我。对联的句子,上联是:“天惊地怪见落笔”,下联是:“巷语街谈总入诗”。昌硕先生看古今人的诗文书画,只说好,也往往不加评语,这是他平常的态度。他送给我的这副篆书集联,自然是奖励后进的一种办法,是昌硕先生平时所不常用的。尤其他所集的句子,虽原出于褒奖勉励,实觉得有些受不起,也更觉得郑重而可贵。很小心地仔细珍藏,有十多年的长久。抗日战争中,杭州沦陷,因未随身带到后方而遭遗失,不知落于谁人之手?至为可念!回忆联中所写的篆字,以“如锥划沙”三笔,“渴骥奔泉”之势,不论一竖一画,至今尚深深印于脑中而不磨灭。
有一次,我画成了一幅山水画,自己觉得还能满意,就拿去给昌硕先生看看。他看了以后,仍旧只是说好。但是当天晚上,却写成了一首长诗,第二天早晨,就叫老友诸闻韵带交给我。诗里的内容,可说与平时不同,戒勉重于褒奖。因此可知道昌硕先生对于研究学术的态度,极重循序渐进,不主张冒险速成。兹录其长诗如下:
读潘阿寿山水障子
龙湫飞瀑雁荡云,石梁气脉通氤氩。久久气与木石斗,无挂碍处生阿寿。寿何状兮颀而长,年仅弱冠才斗量。若非农圃并学须争强,安得园菜瓜果助米粮。生铁窥太古,剑气毫毛吐,有若白猿公,竹竿教之舞。昨见画人画一山,铁船寒壑飞仙端,直欲武家林畔筑一关,荷蒉沮弱相挤攀。相挤攀,靡不可,走入少室峰,蟾蜍太么麽,遇着吴刚刚是我。我诗所说疑荒唐,读者试问倪吴黄。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堕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
我在年轻的时候,便很欢喜国画,但每自以为天分不差,常常凭着不拘束的性情和由个人的兴趣出发,横涂直抹,如野马奔驰,不受羁勒。对于古人的“重工夫、严法则”的主张,特别加以轻视。这自然是一大缺点。昌硕先生知道我的缺点,便在这幅山水画上明确地予以指出,就是长诗末段中所说的“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堕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他深深地为我的画“行不由径”而发愁。
吕硕先生逝世以后,每与诸旧友谈及近代诗书、绘画、治印等项,总是要谈到昌硕先生。因此也常常引起旨年与昌硕先生许多过往的情况。抗日战争中,流离湘、赣、滇、蜀,笔砚荒废,每怀念吕硕先生诗、书、绘画、治印的卓绝而特殊的风格,而为左右一一代风气的大宗师,不禁有所怀念,也因怀念而曾咏之于诗篇。兹将《忆缶庐先生》的诗录下:
忆吴缶庐先生
月明每忆斫桂吴,大布衣朗数茎须。
文章有力自折叠,性情弥古侔清癯。
老山林外无魏晋,驱蛟龙走耕唐虞。
即今人物纷眼底,独往之往谁与俱。
4.挂一漏万说朋友
崔永元
崔永元,1963年生于天津。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毕业后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曾参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等节目的策划工作,后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先后主持《实话实说》、《小崔说事》、《电影传奇》等栏目。出版有《不过如此》。
一
那年我8岁,认识了杨长江,年龄相仿,情趣相投,很快就好成一团。我的志向是买齐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所有小人书。在1970年,这个志趣很奢侈。父亲虽然是团政委,无奈家里亲戚太多,每月钱发下来,几家分分就所剩无几。赶上谁生病,顿时捉襟见肘。我亲眼见到母亲搬着几公斤重的模子用力撞击,黑色的塑料粉末沾在她的鼻翼下面,她在家属工厂干着繁重的丁作。发工资的日子她的心情最好,上街的最后,一站总是新华书店。新出版的小人书散着油墨清香在书架上排列成行,幸运的口子,我也只能买上两本。有时候我要求太高,母亲就翻了脸,常常是高高兴兴上街去,腻腻歪歪回家来。
小人书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以至于许多年以后,很多场景都让我旧事重温。去看话剧,台上的纨绔子弟说,将来老子有了钱,拿糖葫芦当饭吃;我马上想到,将来老子有了钱,小人书重复着买。
1985年,我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小人书基本找不到了。
再后来就像疯子一样去搜寻过去的小人书,万水千山走遍,好多人见面都问,是真的吗,为什么?
我的朋友杨长江明察秋毫,发现了我的癖好,于是帮我友情购买。多少次,他红着脸,手伸到母亲的钱包里,然后,紧紧攥着几毛钱,我们飞到新华书店,新书买到手,像英雄雷锋、王杰阅读毛主席著作一样,如饥似渴。
我的朋友杨长江这样提心吊胆作了3年的“案”。
后来,我认真回忆分析“案情”,感到不可恩议,屡屡“犯案”,杨长江妈妈会没发现?还是因为知道是为买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她的母亲是老师。
小人书不是四书五经,而我们60年代出生的这拨,知识结构中很大部分由它构成,在这样的结构下,历史的厚重,艺术的奢华,哲学的严谨都极易被通俗,小人书培养了这样一批人,不求繁琐,只爱简单。
小人书虽小,要求却高,百十幅画面讲透一个故事,每幅画的担子都不轻,留给文字的位置只是一指来宽,言简意赅便成了最低标准。
字少,又精彩,铭记的可能性就大些。
出3道题,谁说出书名就算及格,再知道谁画的,就判优秀。
“白骨精两次被悟空识破真相,差点丢命。她满肚子气愤,回到妖洞,一言不发,杀气腾腾地坐着,心里直打主意。”
“狼一心想吃东郭先生,便连忙答应,真的又钻进布袋里去了。”
“盛佳秀歇了一阵气,才觉察靠在别人怀里,顿时差得满脸通红,飞身就跑。雨生叫:‘慢点跑吧,仔细绊跤呵,啊,谢谢你呀。’佳秀回了一句:‘哪一个要你谢!’飞快不见了。”
这是字书,所以进度缓慢,现在我用小人书继续讲我的朋友杨长汀的故事,一共两幅,拿钱买书算一幅,另一幅是我俩在路上走,忽然,有小青皮谩骂我们,这已不是第一次了,3年来,我们忍气吞声。那天,杨长江忽然甩掉了往日的文弱之气,健步走到几个小无赖面前,手指顶着他们的鼻尖,你再骂一句!
沧海桑田呵,小无赖居然鸦雀无声。
杨长江的手没有放下,你再骂一句!30年以后,我清楚地记着这个画面,后来我们走出很远,也没听到一点声响。
这幅画面的文字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我们上的是一所农村小学,3年不长,打下了一个朴实的底子。3年后我进了城市,30年后我开始在电视上主持节日,无论怎样打扮,都包不住一股土气,欣赏的人说,真诚,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