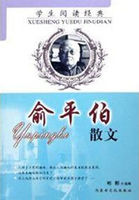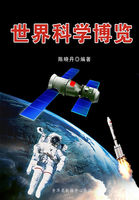被采访人:王敏修,男、47岁、山东省邹平县礼参镇大刘村人,现在北京总后勤部建筑设计院工作。文职干部,技术13级。
采访地点:总后勤部营房部设计院办公楼11层王敏修办公室。
由于是老乡,当我提出写写他时,他说我有什么可写的,我说你会开车吧,他说开车会。我说那就行了。我们不但是老乡,还是酒友。头几年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一起去房山山里玩,中午都喝了不少酒,低度酒他至少喝了有一斤,回来的路上,车开到山顶向下走了不多远,司机停车撒尿,我们俩正迷迷糊糊坐在车上打盹,看车停了,我们俩都挣开了眼睛,他起身下车,我以为他也下车撒尿,没想到他下车后,又上了前面的驾驶座,我说不行,大哥,你喝了酒。他说谁说我不行。然后发动着了车,他开车下山,我害怕的坐在车里大喊,司机在后边追。他开的还挺快,旁边就是悬涯峭壁,一失手我们就会粉身碎骨。在跑了好大一段路后,他才笑着停下来。他笑着对我说,你还不相信我的技术。司机上气不接下气的追上来,说老王,你想吓死我。这天我去他办公室,先是聊了些别的,然后言归正题,说上了采访的事。
我是71年11月份高中毕业,那时征兵都是12月份,我原想当年就去当兵,那年林彪出事后,没有征兵。我们几个高中生回村后,有的被分去养猪,有的分去积肥,我被分去跟老饲养员喂牛。过了年村里选送一名高中生去县拖拉机站学开拖拉机,我们听说后,都盼着能挑上自己,那样就能不用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了,开着拖拉机去给全公社各村耕地,一年两季,麦收和秋收后,一共要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到哪里都能吃点好的不说,还会得到许多年轻姑娘投来的倾慕的目光。最后我被幸运的选上,在县拖拉机站学习的一个月里,我时常激动的想唱歌。学完后我被分到公社拖拉机站,真的开拖拉机去全公社各村耕了好几个月的地。72年底我就当兵出来了,我们是在北京丰台总后分部新训的,训练完我就被分到了总后营房部管理科公务班,当时我们和司机班住在一排平房里,由于在家开过拖拉机,看到那么多小车,看到开小车的老兵都很神气,我心里想我能当上一名驾驶员多带劲。当时每个人填一张登记表,其中有一栏是填自己有何特长,我填的是会开拖拉机。我们班长看我表现好,怕上级把我调去开车了,他把我表上填的特长一栏给划掉了,当时我还想不通,但只能安心当一名公务员了。
没多久,周总理亲批的530格拉工程(格尔木到拉萨的输油管线工程)开工,我随从勘察设计大队去了格尔木,当时大队里有三台北京吉普车,由于平常和司机们不错,帮他们擦车、修车等,有时出去办事的时候就带着我,甚至没领导在场的时候就让我学着开一会,反正荒原上车少人也少,有时在外边跑半天也碰不上一个人影。有一次跟我们大队政委下去上唐古拉山看望工作人员,那时政委是正团,也是坐的北京吉普。因下了小雪路上比较滑,当时政委因高山反映坐在车里睡着了,上一个坡路时,车向一边侧翻了,政委醒来就问,是不是又扎轮胎了。我们说不是,是车翻了。当时的沙石路上老有修车扔下的垃圾扎轮胎,有时一天轮胎能被扎五、六次,一个车最多带两个备胎,坏了就停下来补胎,司机随车都带有补胎工具,我总是下车来帮忙,补完胎,还得用给自行车打气的气筒给轮胎打气,一个胎要打五、六百下,总是我和司机轮换着打,在高原你不干活还喘不上气来,给轮胎打完气,我和司机就象刚跑完马拉松下来。高原上不用高压锅是做不熟饭的。有时跟藏族干部到当时老百姓家去,好客的主人端上酥油茶让我们喝,人家藏族干部端起来就喝下去了,我们喝不了那个味,人家藏民就问怎么回事,我们的领导就说,他们是汉人。因为紫外线强,我们的脸蛋也是又红又黑,所以从外观上看上去真象藏民。
76年11月我被调回北京,回公务班当班长,77年6月调设计院办公室干公务员,当年提了干。当时也有老同志劝我,把农村定的对象吹了,在城里找个有正式工作的,省的两地分居。我没有听别人的劝告,79年回家和原先订的对象结了婚。后来有了儿子,81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孩子刚两岁半。夏天我出差回来中途回家,回到家看到儿子又瘦又黑,我鼻子酸酸的,到自己家的地里一看,人家的地里是看见庄稼看不见草,我们家的地里是看见草看不见庄稼。我脱下军装就干,整整干了一个星期,把三亩地里的草全除完了。看她带着孩子没法干活,我决定把儿子带回北京,小孩他舅舅骑车追到车站,不放心的问我,孩子这么小,你把他带走到底行不行?我说不行也得行,没有别的办法。才开始还挺高兴,一上车看她妈妈不上车,就哭着不愿意了,火车已徐徐动了起来,孩子在车上哭,他妈在车下哭。
说到这儿,王大哥停了下来,他把头扭向窗外,过了好大一会,他才转过身来,深深的叹了一口气。看着他不到五十岁,已是满头花白的头发,我想这白发是他生活的见证,这白发下埋藏着许多感人的故事。
后来我到管理处工作,分管行政这一块。早晨要组织出操,打扫卫生。其中分管司机班,跟老司机学习了一年多,终于拿到了驾驶本。有时有紧急事,司机不够用,我就亲自开车跑一趟。孩子跟我来部队后,我联系让他上了幼儿园,那时幼儿园没有让住的,所以天天接他回来,我们那时住集体宿舍,两个人一个房间,儿子就和我挤一张单人床睡。早起去出操或打扫卫生,怕他醒来闹,每天走时就在枕头边给他放一块糖或一个苹果,有时回来还没醒,有时回来看他坐在那儿啃苹果。晚上累了,一躺就睡着了,半夜睡来,赶紧起来给他洗衣服,幼儿园的老师说,你真不容易,他母亲不在身边,但王军穿的比谁家的孩子都干净。
89年我带两个司机去珠海接一辆丰田面包车。走时领导交待,一是注意行车安全,第二还是安全问题,不要夜间行驶。走到后我们住在一个小旅馆,离开前一个转业回珠海的干部,听说我们去了,找到我们后,最后一夜非安排我们住宾馆去,晚上两位司机说咱到楼下转转,我说你们去吧,我先洗个澡。他们去后,我就去卫生间洗澡,刚洗一会,电话响了,我出来接电话,里边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先生,你寂寞吗,让我上来陪陪你。我一听可吓坏了,我壮了壮胆子说,我是公安局的,你不要胡闹。那女人说,哟,大哥,你真会开玩笑,哪个房间住什么人我们还不知道,这儿绝对安全,公安局有行动,我们会提前知道的,你等着,我上来了。我忙擦了擦身子,赶紧穿上了军装。不大一会,有人敲门,我不敢吱声。停了一会,又敲。我去开了门,一个小姐站在门口对着我笑。我问你找谁?她说找你。我说我不认识你。她歪着头说,现在咱们不是认识了吗?说着她就要进屋,我说我是军人,请你也自重些。说完关门后上了锁。我没再去洗澡,躺下看报纸。过了不大一会,又有人敲门,我在屋内不言声。敲门声一直不停,没办法我赶紧起来又把军装穿戴整齐。敲门声响了好大一会,他们俩开始笑着在外边喊我开门,又叫这两个小子吓我一回。我们回来时走郴州、岳阳、武汉,三天后本应在信阳住下第二天再走,可没找到有停车场的住处,我们商量了一下,说反正到了北方了,咱们再住前赶路吧。晚上八点多到河南确山附近时,前边被一堆沙子堵住了去路。我们正在犹豫怎么办时,从路边的黑影里窜出来二、三十人,手拿木棒围了上来。我告诉司机不要熄火,万一打起来,撞着一个是一个。后来他们走上来,一个领头的说,弟兄们等了很久了,哥们,借个小钱花。我们说,我们是军人,没有钱。他们就使劲的看前后的车牌子,我们问你们要多少钱,他们说一百。后来我们的一个司机从兜里掏了一把钱递过去,说就这些了。他们放行了,但我们不敢向前走了,我们赶紧调头向回走,没走多远碰上一个大卡车,碰巧也是军车。我们说前边有截路的,有没有别的路能绕过前边去,他们说还有一条路能过去,就是远点。我们带路,你们就在后边跟着走就行。后来我问司机,你刚才给了有多少钱。他说有一张伍元的,一张两元的,剩下就全是毛票了。我们一起大笑起来。原来他们截去一共还不到十元钱。幸亏是个大黑天。
过去生活困难,家里也穷。我父亲去世时,49岁,得肺结核死的。那年我27岁,两个弟弟两个妹妹还都没结婚。后来我大弟结婚,我把一块北京牌手表都卖了。卖了伍十块钱。那块表是李政委在北京手表厂支左时得到的,后来送给了我。现在生活好了,等退休了,中国入世后车便宜了,买辆小车开开,正儿八经的过过开车的瘾。
生活的磨难没把他压垮,倒把他煅练成了一个说话幽默,对世事达观,爱于助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