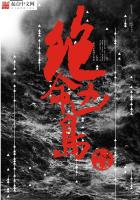里克顿足曰:“惜哉,惜哉!若早些儿与子商之,祸也许可止也。”
说毕,别丕郑父归家,登车之时,故意跌倒,遂假称足疾,不复上朝,在家养病。
消息传到优施耳中,忙去禀告骊姬:“姐姐,可贺呀可贺!”
骊姬笑问道:“何事值得汝这么高兴?”
优施道:“里克果不食言,故意跌伤,不复上朝。”
骊姬道:“好,好,姐这就放心大胆地干了。”
是夜,骊姬枕着晋献公臂弯,喁喁私语道:“世子数次将兵,无往而不胜,盛德日著,然与臣妾有隙,久居曲沃不归,请君为妾召之,叙以母子之情,君一旦有所不测,世子登位,不至亲亲相害也。”
晋献公大悦,翌日便降旨一道,宣申生进宫。
申生应召而至,拜见献公,问之曰:“君父召儿臣回来,有何见教?”
晋献公回曰:“夫人回心转意,甚是思念吾儿,吾儿且莫辜负夫人一片慈心,速去益香阁叩拜。”
申生本来就是一个孝子,又有父命,焉能不去。
骊姬见申生到来,不只问寒问暖,还问他如何将兵,如何治民,装出一副慈母之样,中午,又设宴相款。晋献公闻之,满脸都是笑。
他笑得有些早了。
他因为处理一件棘手的事情,俟至夜半方归,却见骊姬坐在床头,满目泪水,惊问道:“出什么事了?”
骊姬被他这么一问,“嗷”的一声哭了起来:“臣妾欲回世子之心,求主公召之,谁知,他竟然对臣妾无礼。”
晋献公道:“他怎个对卿无礼,请卿言之。”
骊姬道:“臣妾为回世子之心,问寒问暖,又留他午膳,饮之半酣,世子一脸淫邪地瞅着臣妾,戏之曰:‘我父老矣,夫人应该早作打算。’臣妾怒而不应。世子又曰:‘昔我祖老,而以我母姜氏,遗于我父。今我父老,必有所遗,非我而谁?’一边说一边来拉臣妾之手,臣妾拒之乃免。君若不信,明旦,臣妾约世子周游于圃,君从台上观之,必有睹焉。”
晋献公强忍怒火道:“好,就依爱卿之言。”
第二天,用过早餐,背着晋献公,骊姬用蜂蜜涂其发,而后召申生同游于圃,因蜂蜜之故,蜂蝶纷纷,都飞到她头上。
骊姬小声说道:“不知何故,我这头上尽是蜂蝶,请世子为我驱之。”
申生应了一声,从后以袖麾之。
晋献公瞧在眼中,误以为申生有调戏骊姬之事,怒发冲冠,正要遣武士去捉拿申生,骊姬一溜小跑,向他跑来。
申生一脸愕然地站在原地。
骊姬跑到晋献公跟前,气喘吁吁地说道:“刚才之事,君可见乎?”
晋献公一脸怒气道:“申生果真是个畜牲,寡人这就传旨斩之。”
骊姬慌忙跪了下去,叩头说道:“世子乃臣妾所召,召之而又杀之,是臣妾杀世子也。且宫中暧昧之事,外人未知,姑且忍之。”
晋献公见骊姬为申生求情,所言也有一定道理,便赦了申生,但命他即刻出宫,返归曲沃。
他尽管赦了申生,心中这口怨气还在,遣一心腹大臣潜入曲沃,搜集申生之过。
这大臣一遣,骊姬明知晋献公不会放过申生,但又怕夜长梦多,又生一计,非要置申生于死地。刚巧晋献公要去翟桓巡视,大概要六七天时间,骊姬忙遣使曲沃,对申生说道:“夫人说她昨晚做了一梦,梦见我儿之母,大冬天穿着破祅,面黄肌瘦地走进宫来,对夫人说道,‘我冷啊,我饿啊!’是不是我儿好久没有祭祀先夫人了?”
申生慌忙谢罪,对使者说道:“我明日便去祭祀先母。”
因晋献公之先祖曾都曲沃,其祖庙设在曲沃,故齐姜之庙亦在曲沃。翌日晨,申生赴母庙设祭。祭毕,按照惯例,申生将祭奠用过的胙肉派人送给献公享受。因献公打猎未归,乃留胙于宫中,六日后,献公回宫,骊姬以鸩入酒,以毒药涂肉,献之曰:“臣妾梦齐姜苦饥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世子而使祭焉,今至胙于此,待君久矣。”
晋献公曰:“卿做得对。”遂取觶斟酒,欲饮之。骊姬跪而止之曰:“酒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试。”
晋献公曰:“然。”乃以酒浇地,地上立刻烧出一个土坑。
晋献公吃了一惊,命宦者牵来一只犬,以胙喂之。犬惨叫而死。
晋献公还不信,又召一小宦,强逼他将胙吃下,口吐白沬而亡。
晋献公见此情景,直气得又是咬牙又是跺脚。骊姬也嚎啕大哭起来:“多么狠毒的世子啊,老父能有几天活头了,还想去害死他呀!”
她一边哭,一边偷瞅着晋献公脸色说:“世子要谋夺君位,还不是因为臣妾和奚齐呀,愿君以此酒赐妾,妾宁代君而死,以快太子之志!”当即取酒欲饮。
晋献公夺过酒杯,将酒倾之于地,气咽不能出语。
骊姬哭倒在地,恨曰:“世子真忍心哉!其父尚欲弑之,况他人乎?始君欲废之,妾固不肯。后圃中戏我,君又欲杀之,我犹力劝。今几害我君,妾误君甚矣!”
晋献公铁青着脸,许久说道:“尔起,寡人这就布告群臣,诛杀逆子。”
说毕,撞钟出朝,召诸文武议事。惟狐突久已杜门,里克称足疾,丕郑父托以他故不至,其余毕集朝堂。
晋献公开门见山,将申生如何调戏夫人,如何置毒胙中以害君父等罪一一讲给群臣。群臣明知这是诬陷,一个个面面相觑,不发一言。
晋献公怒道:“尔等为何不言不语?”连问三遍,东关五出班奏道:“世子无道,罪该当死,臣愿为君讨之。”
晋献公喜道:“寡人固知卿乃忠臣尔,寡人拨卿兵车二百乘,梁五为副,出讨曲沃。”
东关五高声叫道:“遵旨!”
晋献公嘱道:“世子数将兵,善用众。尔要慎之!”
东关五、梁五齐声回道:“请主公放心,臣等这次出征,必定凯歌而还。”说毕退朝,整顿器械。
狐突虽然杜门,时刻使人打探朝事,闻“二五”奉命征讨曲沃,忙遣次子狐偃密报申生。申生又告太傅杜原款。
杜原款曰:“胙已留宫六日,其为宫中置毒明矣。子可上书自理,群臣之中岂无明白之人?请不要束手就死!”
申生叹曰:“君非骊姬,居不安,食不饱。我自理而不明,是增罪也。幸而明,君爱骊姬,未必加罪,又以伤君之心,不如我死!”
杜原款曰:“子既不愿自理,逃亡他国怎样?”
申生曰:“君不察吾无罪,而行讨于我。我背弑父之名以出,人将以我为鸱鸮矣!若出而归罪于君,是恶君也。且彰君之恶,必见笑于诸侯,内困于父母,外困于诸侯,是重困也。弃君脱罪,是逃死也。我闻之,仁不恶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
杜原款长叹一声,不复再劝。
申生作书付与狐突,书曰:“申生有罪,不敢爱死。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望舅爷努力以辅国家,申生虽死,受舅爷之赐实多!”书毕,北向再拜,自缢而死。
翌日,东关五率兵来到,闻申生已死,乃执杜原款囚之,以报献公曰,“世子自知罪不可逃,乃先死矣。”
杜原款身带镣铐,被押进宫来,晋献公责之曰:“尔乃三朝重臣,寡人要尔辅佐世子,教以为君之道,难道就是弑父自立么?”
杜原款大呼曰:“天乎冤哉!原款所以不死就俘者,正欲明世子之心也!胙留宫六日,岂有毒而久不变者乎?”
这一喊骊姬慌了,忙从屏风之后抢出呼道:“主公,杜原款辅导世子无状,罪该万死,何不速速杀之!”
晋献公竟然听信了骊姬之言,喝令力士用铜锤击杀杜原款,脑破而死,视者无不暗暗流泪。
但也有拍手称快的,那便是骊姬、“二五”和优施,趁晋献公出游之机,聚在一起,置酒相贺。
酒至半酣,东关五突然停杯不饮,还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梁五惊问道:“东关兄这是怎么了?”
东关五道:“申生、杜原款虽死,重耳、夷吾还在,彼二人之智、之声望,不在申生之下,彼二人若是不除,必有一人为世子,主公百年之后,岂不找我等算账?”
梁五道:“如之奈何?”
东关五移目骊姬。
骊姬道:“若为重耳、夷吾之事,东关大夫不必担心,本宫设法将他们除掉不就得了。”
翌日,晋献公出游归来,仍由骊姬侍寝,睡至夜半,晋献公醒来,忽见骊姬在暗自抽泣,忙问道:“爱卿是不是哪一点不舒服?”
骊姬道:“非也。”
晋献公道:“既然无病,为何而哭?”
骊姬道:“妾哭申生矣。”
晋献公道:“申生,畜牲耳,哭他作甚?”
骊姬道:“臣妾听人言之,申生之所以敢大胆弑君,乃是受了重耳、夷吾教唆。申生既死,二公子归罪于臣妾,终日练兵,欲袭绛而杀臣妾,好图大事,主公不可不察!”
晋献公将信将疑道:“不会吧!”
骊姬道:“怎么不会?主公知道不?前次申生征伐落,之所以大胜,乃是因二郎山四盗和赵衰、介子推相助,此六人者,皆重耳之友也。”
晋献公良久方道:“此事容寡人察之。”
到了翌早,早朝已毕,有近臣奏告:“蒲、屈二公子来觐,已至绛郊,闻世子之事,当即调转车辕,回蒲、屈去了。”
这事千真万确。
赵衰、介子推伤未痊愈,便欲去蒲地投奔重耳。行至中途,闻重耳赴绛,忙追至绛郊,哭诉了申生自杀之事。
重耳大惊,忙叫住夷吾商议对策,彼二人全都觉着,此行入都,凶多吉少,不如折回封地,观察一段再说。
这一折,使晋献公心中愈发生疑,恨声说道:“不敢入都,乃是心中有鬼,必同谋也!”
当即命寺人勃鞮率师征蒲,捉拿公子重耳;大夫贾华,率师往屈,捉拿公子夷吾。
事为狐突所知,密呼次子狐偃至前,谓之曰:“重耳骈胁重瞳,壮貌伟异,又素有贤名,他日必能成大事。且世子已死,次当及之。汝可速往蒲,助之出奔,与汝兄毛,同心辅佐,以图后举。”
狐偃点头允之,牵了一匹快马,连夜奔至蒲地,来投重耳。重耳听了狐偃之言吓得面如土色,许久不语。
狐毛赔着小心问道:“据偃所说,勃鞮马上就到,公子意欲何为?”
重耳道:“我欲出奔他国怎样?”
狐毛道:“也可。”说罢,忙奔出前厅,招呼车夫壹叔及管家头须等准备出逃之物。
谁知,物未备齐,勃鞮率兵来到,若依狐毛、狐偃之意,当即关闭蒲门,命军士登城守禦。
重耳长叹一声道:“这城门一关,便是抗拒君命,君命不可抗也!”
于是勃鞮未受到任何抵抗,轻而易举地进入蒲城,围重耳之宅。
重耳入居蒲城前,已娶过二妾。初娶徐赢,早卒。再娶,生一子一女,子名,女曰叔姬。夫妻二人恩爱无比。今见勃鞮围宅,忙与狐毛、狐偃商议出逃之事,按重耳之意,要带上母子一块儿走,狐毛、狐偃反对。正争执不下,勃鞮闯进大门,忙与狐毛、狐偃一齐趋向后园,勃鞮提剑追之。
狐毛、狐偃跃墙而逃,推墙以招重耳。不想那重耳迟了一步,衣袂被勃鞮抓住。衣袂者,衣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