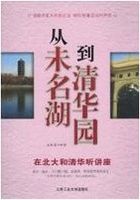我们都要学习水塔,只有站得高,才能望得远,要做好工作,首先就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还要学习水塔那种慷慨无私的精神,有了水就毫无保留输送给别人。谢守正想了一下补充说:“我看这个高,主要指思想上的高,而绝不是要我们站在群众之上。我想到文华楼的水井,它深深埋在地底下,正因为扎得深,有了无穷尽的源泉,才能取之不尽,作出贡献。我们呢,要扎根群众之中,向群众学习,才能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在后来的谈话中,金婉蓉也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工作总是不大胆,有时心里想得蛮好,就是不敢说出来,不敢照着做。辅导员说得对,青年人要敢想敢做,不怕错,错了就改嘛!我想,自己就要像这六角亭一样(她指着学生会)轮廓分明,而不能圆滑没有棱角。”这次谈话,昙华林的水塔,六角亭,文华楼的水井,深深刻入了我的脑海,让我终生难忘。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星期四
下了两天雨,天又晴了。我拿了一本《学习雷锋专刊》,坐在校园草地石块上阅读。眼前,有几只燕子低低地飞着,不时在嘴上衔着一根草或是一撮土,飞到体育馆的屋梁上停了下来,我好奇地瞧着它们,原来,它们是在做窝……“南来的燕子啊!
新来的候鸟,从北方飞到了南方……”
是谁在朗读雷锋的诗,回过头去,原来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刘燕平,她在我旁边坐了下来,平时嘻嘻哈哈的,今天显得有点严肃。“傅永昌,最近我想了很多事情”。我问:“什么事情?”她犹豫了一下说:“我告诉你,想征求你的意见,可不准告诉别人。”我爽快答应:“行!”她的眼睛望着远方,像在沉思,隔了好一会,她才慢慢地轻轻地说了起来,她说到学习上高标准的目标,说了盼望早日加入团组织的心愿,甚至说到毕业后的打算,说自己要申请到边疆去,“把青春献给边疆,献给少数民族,多有诗意啊!”她边说边笑边摇头,随后,又轻轻地唱了起来:“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齐飞翔……”她见我没有反应,凑过来问我:“你怎么不吭声呀!”我故意说:“幻想,十足的幻想。”她一听,扭过头去,生气了。我还想激她一下,拿起手中的书,念着:
“七分热情,三分幼稚
就像那羽毛未丰的新燕,虽然爱着白云蓝天,可才刚刚要展翅起飞,还没有经受雨打风吹。”
她一把把书抢过去,接着念:
“风里,不退,雨里,不退!”
念完,啪的一下又把书扔还给我。我看玩笑不能再开了,就只有平心静气对她说:“你也想得太简单了,你就不想想到边疆有多少困难?”
“谁说没想困难的,有困难就克服呗!”她的气还没消,嘴努得高高的。
我又说:“要是到时候边疆不要人,派你到别处去呢?”
“雷锋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她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觉得她比以前长高了。
昙华林春晨的校园,景是美的,人是美的,情是美的,景,人,情组合在一起,唱出了一支最动听的赞歌。这是青春的赞歌,是前进的赞歌!
(傅永昌,1962年入中文系。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曾任武汉市江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差一点没能跟大家成为同窗
【王继超】
入学50周年欢聚过了,现在大家又在撰文回忆校园生活。此时此刻,我却记起了当年差一点卷辅盖回家。不能和学友们同窗共读的往事。
记得已经入学后安顿下来,“洪湖水浪打浪”般的高粱糊也吃过了好几天,突然有人通知我去一趟系办公室,说是有重要的事情找我。会是什么事呢?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还是在一个中午不到两点的时候去了。系办公室还没有人上班。门关着。只见一位年青人手拿一本书,正坐在地上,背靠着墙。看儿眼书,又闭上眼默默记忆一会儿。从他胸前的校徽上,看得出他是一名教师。估计也是来办公室办什么事的,利用等开门前的一点时间读书。后米才知道他就是邢福义老师,怪不得人家那样博学多才,那是惜时如金的结果啊。
待到见了找我的老师,他的一席话却似一盆凉水从天而降:说的是经过体检,我的“肝大”,不能入学。稍微缓过一点神来,我惴惴地问:“那是不是得要明年再来报到入学呢?”答曰:“明年就得要重新参加高考了。”这下子,我就紧张了:虽然我的母校武汉六中算是一所重点中学,但当年的高考入学率也才三分之一的样子呀。去休息一年,谁知道明年会是个什么结果呢?
回家后跟家里人谈起此事。家姐在一所部队卫生学校任教,遂带我去到当时还在汉口黄埔路的武汉部队总医院挂了个号作体检。一位军医来检查完后,说:“什么事都没有。”然后在检查结果单上大笔一挥。签上了“上校军医某某某”的大名。
拿着这份体检单,我喜滋滋地回到系办公室。以为这下没事了。谁知被系里叫来的医务室那位刘医生(当时就是他阁下检查说我“肝大”的)狡辩说“即使我检查的不准,那也不能说他检查的就一定准啊”!
怎么办呢?系里只好要我到桂子山校本部医院作最后的检查。
那时候,去桂子山可是件难事,我步行了多久也说不清。去到校医院外,也不着急进去,先找了一棵大树坐下来,靠在树上,掏出一本书看了好久好久,一是为了休息一下,二是为了平复一下紧张的心情;这可是事关前途命运的大事啊!
进了医院。讲清来意,一下子过来了四位医生。这阵势可让我更加紧张起来,好在他们在我腹部按来按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切正常!
同去的路上,那可真是“风含情云含笑”啊,不知不觉就到了昙华林。那位从来也没有穿过一件干干净净白大褂的刘医生,再也无法说出一个“不”字来,我也才得以与大家同窗四载。
说起昙华林的医务室,还有一段经历,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至今仍然难忘。那是1962年的某一天。具体的日子倒确实记不清了。记得已经睡到半夜。突然间我胃疼得要命,真是疼得在那张上铺打滚。这下惊动了寝室里的同学,大家都翻身起床。几个反应快的说道:赶快送校门口的湖北医院!于是儿位同学匆匆赶往医务室抬担架。不一会儿,担架来了,同学们抬的抬、送的送。片刻工夫就把我送到医院看了急诊。医生问: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没有?这个问题还真是无法回答。虽然说这个时候吃的饭已经比高粱糊糊强一点了,那可能也就是大麦馒头、清煮的蚕豆之类的东西;再说。那个年月。除了学校饭堂里的这些食品,哪里还有么别的“不干净的东西”吃呢?不管怎么说吧。医生诊断为急性胃炎,经过输液、留院观察等治疗,到第二天下午也没事了。后来才听说,同学们去医务室抬担架时,大门紧闭,无论如何敲门,里面的值班人员都没有反应。情急之下,还是亏得陈泽范兄一拳打破了门上的一块玻璃,从破口处伸手进去拉开门闩,这才能够进去抬担架,泽范兄也付出了皮开血流的代价。在此衷心地向泽范兄道一声谢!
说来也巧,自从那次胃疼之后,五十年来,我虽然大病小病或多或少都犯过。胃却再也没有疼过。真可以称得上是吃嘛嘛香,咸的淡的、甜的苦的、酸的辣的、干的稀的、冷的热的、荤的素的,百无禁忌。也许这都是托了同窗之福吧。
“胃”事不小,“肝”事更大,可来不得半点糊涂啊。
(王继超,1961年入中文系。高级讲师)
青春易逝岁月难忘
【周宝珠】
1961年9月,我被武汉一师保送入华师教育系学习。在桂子山读了一年教育专业,因国家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高校也按此方针调整了某些专业培养计划。这样,我就由教育系调整到了昙华林的中文系。
记得我是1962年暑期参加校团干集训之后,便离开桂子山进入昙华林、跟着中文系二年级一起学习的。当时我带着如饥似渴的心情投入到语言文学专业紧张的学习中。心想,中文专业我比其他同学少学了一年,自己应该快马加鞭迎头赶上,而且唯恐漏掉应掌握的文学语言知识。当时,中文系对学生培养规格提出两个“一”一个“三”的基本要求,即“一口话,一笔字,三百篇诗文”,我知道自己的差距,所以,那时上课,我总是喜欢坐在教室的前排,以便听得清楚,笔记也容易记得完整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