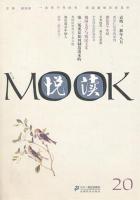我初来昙华林时,正院长是杨东莼,国务院的任命书下达不久,是从广西大学校长的任上刚调过来的。杨院长,著名的历史学家,资深的民主人士,民进中央副主席。1954年秋季开学不久,杨院长参加全国第一届人大从北京返校后,在昙华林大操扬作传达报告。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年过半百的老院长,聆听他的教诲。杨院长满口桂林官话,在我听来是格外亲切的。
“同学们,毛主席一贯提倡联系群众,可我这个人的名字呀,不太好念,有人叫我杨东纯,有人叫我杨东专,可见我这个名字就太不联系群众了!”
幽默的开场白,引来了满场笑声。杨东莼的“莼”字,念“纯”。“莼”的繁体字特别生僻,写成“草字头下面一个繁体的‘专’”,很容易错念成“杨东专”。杨院长把自己的名字调侃一番,巧妙地作自我介绍,告诉大家不要把自己院长的名字给念错了。
杨院长亲自抓新生工作,带着一个精干的专班,到各系开新生座谈会,倾听大家发言;还亲自听课,雷厉风行解决所发现的教学问题。
一天吃中饭时,杨院长突然来到我们食堂,陪同的只有一个秘书。他边看边闻边问,“四菜一汤,够吃么?味道怎么样?”走到我跟前,大概是觉得我个子小不太像大学生,使劲捏了捏我的胳臂,“小鬼,多大啦?”……体育系的同学向杨院长反映:“饭是吃得饱的,就是运动量太大,营养有点跟不上。”杨院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三天之后,体育系的伙食立马就大改善:早餐,每人加了一个鸡蛋、一个馒头;中晚餐,每席加一大盘荤菜。那时,其他系只有在过年过节时、在考试时,才能这样打牙祭,我们真要“垂涎三尺”了。
杨院长是个大忙人,在校外的参政议政活动非常频繁。在报上看到,毛主席在北京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我们的杨院长也是为数不多的与会者之一,此时,昙华林仿佛平添了几分光彩与自豪。1957年春天,杨院长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华师院刊发表了一篇访谈录《语重心长话别情》,有的细节太感人了:配给院长使用的所有公物,包括茶瓶、茶杯、痰盂之类,凡是损失了的,一一按价赔偿。“质本洁来还洁去”,于微细处见精神,我读着读着,不由得热泪盈眶。
昙华林没有大楼,但有饮誉海内外的大师
一位教育家讲得好,光有大楼不是大学,有大师才称得上大学。
当年的昙华林,确实没有豪华壮观的大楼,但已经拥有一批在各学术领域响当当的名师、大师。作为中南地区领军的师范大学,华师是实至名归的。
各系的同学、同乡、朋友聚在一起,最喜欢追捧自己系的名师、名人。历史系的夸他们的“国学大师钱基博”“历史文献专家张舜徽”,中文系的夸他们的“语言学家高庆赐”“文学家方步瀛”,政教系的夸他们的“哲学家詹剑峰”“华大老校长韦卓民”,化学系的夸他们的“高分子化学家张景林”,物理系的夸他们的“核物理专家韦宝锷”,音乐系的夸他们的“指挥家陆华伯”,美术系的夸他们的“著名导演汤麟”……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名师名人的成就地位、奇闻轶事,津津乐道,引为骄傲。
钱基博,国宝级教授,全国屈指可数。这位年逾古稀的国学大师,那时已经不教课了,专心做研究和指导青年教师。那时,他儿子钱钟书,还远没有其父有名,小说《围城》还没有流行开来呢。
韦卓民,在我们学生心目中,是一位“潜龙见首不见尾”的高深莫测的人物。他,是旧华中大学最后一任校长,学贯中西的哲学家,在海内外有深厚的人脉。解放前夕,他拒绝出国、拒绝赴台,毅然决然留在昙华林,把华中大学完好地交给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然后功成身退,还当他的教授。这位从旧社会过来的,有复杂海外关系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是在劫难逃的。
在昙华林,同学们看到韦卓民按时到政教系上班,穿着整洁的中山装,一脸饱经沧桑的皱纹,不卑不亢的神态,令人敬而远之。他继续潜心翻译、研究康德哲学著作,还开过康德哲学讲座。听说,韦老的海外旧交来华访问时,还特地来昙华林拜访他。
被称为“三好教师”的高庆赐教授,跟同学们的关系特别亲近。清晨,在轻纱般的薄雾里,高教授同我们一起长跑,你追我赶,谈笑风生,在400米的跑道上要跑上四五圈。高庆赐时任华师副教务长,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我听过他的汉语语音知识讲座,深受教益。
陶军、陈铁、高原,被称为昙华林时期华师讲坛上的“三剑客”,只要是他们作报告,大家闻风而动,抢占座位,会场绝对爆满。三位演讲家各具特色:陶军的演讲,观点独到,见识渊博,纵横捭阖,妙语连珠;陈铁的报告,纲举目张,条分缕析,逻辑性强,雄辩无比;高原的讲话,内涵丰富,有血有肉,激情四射,感召力强。听三位的报告,如沐春风,简直是艺术享受啊。
三剑客,各自走过了不平坦的人生道路,但归宿堪称圆满。据说,陶军,在文革后出任过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副代表;陈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颇有建树;而高原,最后当了华中师大的党委书记。
昙华林时期,章开沅还是个青年讲师,但学术上已经崭露锋芒,令人瞩目了。当时,万里长江第一桥开始修建,他在报刊上发表一篇署名文章,说古论今,畅谈太平天国时为了军事的需要,在长江上修了一座大浮桥,选址竟与百年后的武汉长大桥不谋而合,讴歌中国人民的大智大勇。我是从拜读这篇文章之后,知道章开沅的大名的。这位后起之秀,以后成了著作等身,蜚声海内外的近代史专家,曾任华中师大校长。
昙华林里,留下了章开沅那一代学者学术起步的脚印。
昙华林里,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昙华林的早晨是最美妙的。丛林里,小鸟们的啾啾鸣叫声;林阴道上,学子们的琅琅书声——抑扬顿挫的俄语朗读声,还有韵味十足的古典诗词唱读声;从校园各个角落琴房里传出来的钢琴声,从声乐教室里传来的练嗓声:汇成一曲独特的昙花林青春交响曲。
在这青春交响曲的旋律里,我们开始了一天的学习生活,紧张而快乐。我们埋头读书,但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世界风云、国家大事的敏感和关切,是华师人的一贯传统。同学们不仅抢着去听陶军、陈铁、高原的报告,而且对校外名人的演讲会,也是争先恐后,力争参加的。我就争取到几次难得的机会。
1955年秋,有一次团支部让我去武大听胡耀邦的报告,我真幸运,真高兴啊!胡耀邦,当时是共青团中央的第一书记,他到广东、海南检查指导工作后,来到武汉,同青年们见见面,谈谈心。胡书记个头不高,留着平头,劲头十足,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爱做大动作,有点像列宁演讲的风采。他从广东人敢吃蛇、爱吃蛇讲起,激励青年大胆创新,开拓进取。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我听得热血沸腾。
我听过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报告。同胡耀邦慷慨激昂的讲话风格不同,王任重作报告却是娓娓道来,与听众促膝谈心。针对某些大学生对生活困难的抱怨,他说,“同学们,我只是个高中生,没有条件读大学。现在如果让我来上大学呀,睡地板我都干……”引发了全场的欢笑和议论。
1958年初的一天,得知当晚周扬要到武大作报告的消息,我们奔走相告,相约前往。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长,是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他的报告非听不可!我们火急赶到会场时,连过道都已经挤满了人。怎么办?冲!涌上舞台,坐在舞台地板上听,只给周扬留出讲台立足的一小块地方。那天,周扬穿着呢子大衣,为大家的高度热情感染,兴致勃勃地讲了一个多小时。报告结束,同学们围上去提问:“周扬同志,请问应该怎么看丁玲的作品?”
“丁玲的作品还是可以读的……”周扬只答了半句,就被保安人员保护出场。当时反右运动刚过去,丁玲被错打成右派,这个问题是非常敏感的,具有挑战性的。周扬的回答,并没有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极左”态度,是发人深思的。
在昙华林,除了抢着去听报告,还有一“抢”——到阅览室抢占座位。那时还没有空调,但阅览室夏天有电扇,冬天有煤炉,冬暖夏凉,室内特别安静,还有几百种报刊可供浏览,实在是读书的最好去处。
到阅览室抢座位这个细节,生动地反映了莘莘学子读书热情的高涨。没有频繁的考试,没有辅导教师、班主任的监督,更没有物质刺激的奖惩,大家却如饥似渴地读书,孜孜以求的是学业上的长进。读书是快乐,长进最光荣!
谁学业有成,比如,在报刊上发表了作品什么的,大家是最最羡慕的。1956年春,我写了一篇散文《临别的一课》,通过一位苏联女教师在撤离回国前给中国学生上最后一课的描述,反映了中苏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作品获得了全校征文赛一等奖,还发表在《长江文艺》《长江日报》上。应该说,这是我文学写作、语文教学的一个闪光起点。
许多学友的成就更令我艳羡。
邢福义,同我一样都是1954年进华师的,我是外文系,他是中文系,相互并不认识。邢福义还在上大一,就开始在刊物上发表语言研究的文章,有的文章居然发表在《中国语文》上,那是汉语科研期刊的最高权威,真不简单哪!据说,汉语学大师吕叔湘,就是从那些文章中发现邢福义的。如今,邢福义是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语言学家。在华师百年校庆的庆祝大会上,我听着邢老兄的讲话,感慨万千:他,应该是从昙华林走出来的,取得学术成就最辉煌的校友了。
李德复,我的学长,是外语系的。我进华师时,他已经读完大二了。看着他用流利的俄语跟同学对话,我真羡慕啊!我们都喜欢晨练,在昙华林的运动场上是常常相见的。1956年秋,他分配到襄阳工作,不久就不教外语,专心于文学创作了。1958年发表短篇小说《典型报告》,有幸获得了时任文化部长、作协主席的茅盾的赏识与推荐(同时被推荐的还有茹志娟的《百合花》)。李德复一鸣惊人,陆续创作出数百万字的作品,成了著名作家,我们还请他来学校作过报告呢。
昙华林里,走出了全国有名的相声艺术家夏雨田;走出了教育部副部长邹时炎;走出了数不胜数的高级教师、特级教师、教授、博导、专家、学者、各界精英。昙华林啊,你不愧为人才的摇篮!
婚礼,就在教室里举办
也许有人会问,当年昙华林里的大学生,会谈情说爱么?
回答是肯定的。爱情是大学生活的永恒主题,只不过有着不同的时代特色而已。比起意识超前的90后,那个时代的谈情说爱要含蓄一些,内敛一些,循规蹈矩一些,但心都是火热的。
讲一点似乎不可思议的趣事吧:当时有一批参加工作三年后再来上大学的“调干生”,他们年龄大一点,有的已婚,有的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学校对他们有非常人性化的安排。我们班有位调干生办好了结婚手续,可到哪里办婚礼呢?班长请示系里,系主任说:“婚礼,就在教室里办!”周末,我们向学较借用了一个稍大的教室,张灯结彩,在黑板上写上大红喜字,有司仪主持,有节目表演,只发喜糖,不摆酒席,婚礼办得既热热闹闹又简朴节俭。
我们班有一个叫汪洁的转业军人,妻子探亲来了,学校安排一间空房给他临时住宿,被褥自备,分文不收。
无微不至的体贴,浓浓的人情味,昙华林里情浓爱深啊!
昙华林里,文化氛围浓郁,精神生活丰富。露天电影场每周都放映新片,当然是免费的,座位可要自备。你不会跳交谊舞吗?不行!班上马上扫你的“舞盲”,把你拽到周末舞会上去“出洋相”。校、系的文艺社团百花齐放,任你展示。学校剧团群英荟萃,演出了不少名剧大戏。老舍的新作《西望长安》,由教师演员担纲,教务长陶军也粉墨登场。1956年,根据巴金同名小说由曹禺编剧的话剧《家》盛大演出,是华师戏剧活动的高潮。演出的精彩和成功,是可以跟专业剧团媲美的。《葛麻》等楚剧节目演得很地道,夏雨田演的葛麻,唱功做功都很到位,赢来了一阵阵喝采声。
当时,物质生活相对匮乏一些,但基本生活条件是国家包干的。所有师范生,一律免交学杂费、书籍费、住宿费、伙食费、医药费,也就是讲上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看病不要钱(包括大病转院治疗),有困难还可以申请补助,调干生每月发十多元生活补贴。我在华师读了四年书,没给学校交过一分钱,还申请过两次冬装补助。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在艰苦创业时期,国家百废待兴,人民生活水平还较低,作为新中国早期的大学生,我们感到很幸运,很满足,更感到背负着人民的重托,肩头沉甸甸的!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华师的发展,离不开全国的大气候、大环境。在华师的四年里,我觉得,前两年昙华林的气氛还比较正常、和谐,1957年以后就不太正常了、不够和谐了,原因是众所周知的。
昙华林里尽朝晖。作为华师的摇篮,昙华林是美丽的。但是,如果没有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失误,如果没有违反客观规律的“三面红旗”的挫折,昙华林里的朝晖一定会更加灿烂,百花齐放的春景一定会更加瑰丽。
(彭树楷,1954年入外语系。湖北文理学院教授)
难忘昙华林
【骆道书】
离开昙华林近半个世纪了,但对那里的一草一木、对在那里认识的老师、结识的同学,仍难以忘怀。
一、昙花、银杏、桂花
昙华林自然应该是有昙花的。
记得在入学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昙华林忽然喧闹起来,轰传植物园里昙花开了,于是大家蜂拥而去看“昙花一现”的这个昙花了。我随着人群挤进去看:白白的花朵,似乎有香味。并未看得仔细就被挤出来了。它的枝干,叶片,乃至花的具体形态都未看明白,但似乎却已满足,我已经看到昙花了,真切地看到昙花了,至于其他已不重要了。后来在有关的书上见到关于昙花的介绍:“昙花:仙人掌科,肉质植物。灌木状。老枝圆柱形;新枝扁平,绿色,呈叶状。花生于叶状枝的边沿,白色,大型,两侧对称。美丽,芳香。夜开,翌晨即萎,仅数小时,故有‘昙花一现’之说……”。也许,正因为“昙花一现”,所以弥足珍贵,所以才令人难于忘怀,连同那个难于忘怀的夜晚。
昙华林的银杏给我印象很深。
我并不认识银杏,一次我在银杏树下,拾起一片银杏的叶子,询问一位做卫生的老伯,他告诉我,这叫银杏,又叫白果树,是很珍贵的树种,我说:“这一排树,有十几年了吧?”他笑了笑说:“十几年?我解放前就在这里做事了,那时,它就是这个样子了,那棵大的树,少说也有五十年了。说不准已有百年了。”我再次仔细打量那挺拔的银杏树,很有些感触。后来,我查阅有关资料,证实环卫工人的说法:银杏落叶乔木,高达40米,叶,折扇状;种子,椭圆形或倒卵形。系孑遗植物,生长较慢,树龄长可达千年……我大为吃惊:“孑遗植物”!那是和熊猫并列的珍稀生物啊。我为它受到冷落而不平。可它傲然挺立,恬然生长,淡然面对世人。
凡是在昙华林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都忘不了那两株桂花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