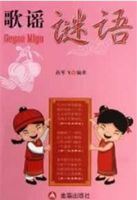回忆的闸门一旦打开,难以收煞,耳边仿佛听到了杨潜斋教授讲《语言学概论》的声音。这位颇具特色的教授,每次来上课必带提包,拐杖,香烟,打火机。头发梳得锃亮,衣服穿得整洁,步履走得从容,讲义用毛笔书写,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字字端庄。他上课时不断地抽烟,讲得入神时香烟熄灭,又不断地按打火机。火机常常出故障,有时要停下来按半分钟。宁静的教室只听见火机发出的咔嚓咔嚓声。香烟又终于点燃了,他猛吸一口气,似乎过足了瘾,再接着大讲起来。什么语言不同于言语;什么声音与符号;什么索胥尔,王国维,高明凯,把一个个古今中外著名语言学家搬上讲台,让初入大学门槛的新生,听起来像他吐出的烟雾那样云遮雾罩,但大家听此不疲,乐在其中。不嫌老师讲的听不懂,只怪自己水平差。杨老师有时讲到得意处,乐不自禁,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们更加感到他吐出的烟圈里飘散着知识,他发出的笑声中浸润着学问。出于对老师的崇敬,当年上写作课时,我写了一篇命题作文,题为《我们尊敬的杨老师》。教《阅读与写作》的朱源滔老师评讲习作时,当场朗诵了我的这篇习作全文,把它当作范文向全班同学推介。我想,朱老师如此看重我的拙文,显然是对学生尊师态度的赞许,给学生敬畏学问的虔诚予以肯定。
由资深教授杨潜斋先生而忆及当时的年青助教邢福义老师。他教我们《现代汉语》时,也就二十多岁,正值盛年。他的刻苦好学精神在师生中很有影响。他讲课从来不看教材和教案,却讲得清晰流畅,生动活泼;声音柔和有着磁性的魅力,耐听而让人乐听。他板书速度极快,且字迹工整,美观漂亮,一个语言例子口述完毕,板书就完成了。他还会画几笔素描,例句中描绘的人物情景,经他在黑板上几笔勾勒,就活灵活现地翩然而出。邢老师讲课所引用的例句很多出自《红楼梦》。对这部名著,他似乎能烂熟于心,由此也可见其勤奋刻苦的一斑。如今,他已是语言学大师,国内知名教授,博士生导师。能够有如此成就,跟他一贯尊师重道是分不开的。记得1962年的某天,中国语言学大师,中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先生到华师讲学。在昙华林大礼堂舞台上,高庆赐教授带领其弟子邢福义向吕先生引荐,在台下上千双眼睛的注视下,邢老师毕恭毕敬地向吕先生作90度三鞠躬,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老师的人品和学品是影响学生人生和学术的重要因素。在母校,尊师重教,教学相长,是代代华师学子的精神资源。
可以说,昙华林里生美景,华师校园出精英。虽然教过我们的大多数前辈恩师因时光流逝而离开了人间,但今天的母校,人才辈出,硕果累累,薪火相传,兴盛不衰。由师范学院而师范大学,由师范大学而进入“211”行列;由“211”大学正在向“985”工程攀登。根深才能叶茂,树大源于根深。百年华师于1903年滥觞在昙华林,是昙华林这块风水宝地孕育造化了母校和一代又一代学人。母校给了我们知识和智慧;母校给了我们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重访故地,并非游山玩景,而是在寻求我们的学“根”,是在向学问“朝圣”,也是在向母校致敬。
然而昙华林里昔日的许多美景已不复存在了,我们只有到尚存的遗迹中去挖掘,到残存的记忆中去搜索,比如看到未拆掉的图书馆,想到了当年的读书生活;看到已经废弃的体育馆,回忆起了当年的周末娱乐活动。
三年困难时期,食难果腹,衣难御寒,大家营养严重不足,健康状况普遍较差。国家对大学生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除周六一小时卫生大扫除之外,不安排其他体力劳动,甚至一度取消体育课。这是因为物质生活极为贫困所取的下策。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却较为充实。如饥似渴地读书,是寻求精神富有的共同途径。每天除上课,作业外,就是读书。教室里,树荫下,操场上,石凳前都有读书、背书声。图书馆借阅处排起长龙,等待办理还书借书手续;阅览室座无虚席,不得不提前占座位。必读书,参考书,工具书要读,新华书店最新售书也要买要读。古今中外经典名著和报纸期刊读物都在阅读范围。读书时,做摘录,制卡片,写读书笔记。老师指导如何选题,如何科研,培养学生学术意识;同学们每有新书,都相互介绍,交流传看,茶余饭后,热烈讨论,以致争论不休。此时已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乏,似乎每一天都过得很平和,很实在。
紧张的读书生活也有调节一下的放松方式,那就是看电影,开舞会。每周星期三,星期六可各看一场电影。但每张电影票价需要五分钱,而我们农村来的穷小子没有这笔开销,也就免去了那种令人欣羡的艺术享受。唯一引人快乐的是在体育馆或饭厅举办的周末交际舞晚会。每到周六夜幕降临之时,闪烁跳跃的红绿灯分外吸引眼球,篷嚓嚓的音乐声十分具有召唤的魅力。男女舞者蜂拥而至,不放过一周一次的良机。舞盲也踊跃参加,图个新奇,看个热闹。我读中学时从来未看过舞会更不会跳舞,一种好奇心的驱使来到舞厅围观,寻找快乐。只见许多长于此道的男女同学,伴随音乐节奏翩翩起舞,有的舞步婀娜多姿,有的旋转热烈奔放,跳得如痴如醉,大汗淋漓。没有舞伴的同学,禁不住篷嚓之声的诱惑,怦然心动,跃跃欲试,脚下情不自禁地打起节奏来。而我只是一名快乐的旁观者,下不了舞池,常常被热心的同学生拉硬拽拖下水,却因缺乏舞蹈细胞不得不爬上岸来。后来学生会号召扫舞盲,并给积极分子分配了扫舞盲的任务。我自然是重点扫盲对象,毛艾伦同学是我的交际舞启蒙导师。不论她如何拖着,拽着,鼓励,打气,我就是学不会。不是自己走歪了步,就是踩了她的脚。天资愚钝,孺子不可教也。交际舞终究没有学会,但收获了围观的快乐,也体验了同学的友善与真诚。
昙华林给了我们一生受用不尽的知识,也给了我们在困难年代的苦中之乐。
昙华林以生长珍稀的昙花而得名。据植物志记载:昙花是一种常绿灌木,主枝圆筒形,分枝扁平呈叶状,没有叶片,花大,多为白色,亦有红色,可供观赏。但开花的时间极短,且多在夜间开放。故有“昙花一现”的成语。《辞海》解释:据宗教传说,转轮王出世,昙花才生,本来是说昙花难得出现。一般则用“昙花一现”比喻事物一出现就很快消失。《现代汉语词典》释为:比喻稀有的事物和显赫一时的人物出现不久就消逝。显然,这些解释都对运用对象有贬谪成分,无疑是对的。照我的理解,“昙花一现”还有瞬间的精彩的意思。能够存留下来的美好记忆不是瞬间精彩么?我们的大学四年在漫漫人生中难道不也是“瞬间精彩”么?任何人物和事物只要有精彩,它就会有价值。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给社会留下一点精彩,哪怕稍纵即逝,世界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汪昌松,1961年入中文系。黄冈师范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黄冈师范学院中文系党总支书记)
昙华林轶事
【薛晴】
初识教授
那是秋高气爽的一个上午,盼来了在文华楼一楼阶梯教室第一次上课,不少同学比我到得还早,前头的座位已坐满,只好往后头走。刚一落座,只听得教室里“哄”的笑声响起来。抬头一看,我也乐了:只见一位不修边幅的、身架高高、面容清癯的长者,穿着一件灰色长衫走进来低声问了前排同学什么话,然后直起腰,摇摇头,笑着说:“错了错了,走错了!”边说着边挥挥手摇晃着转身走出了门。教室里笑声更大了,真逗!我们还以为来了个说相声的!后来才知道他叫石声淮,是上课走错了门,他是教另两个班的教授。教我们这两班的是王凌云教授。随着铃响王老师走了进来,此王教授可是仪表堂堂:方正的脸上目光灼灼,衣冠楚楚端庄利落。王老师走上讲台,放下皮包,从包里往外掏书本教案时却带出来一把小梳子,一下子掉在了讲台上,教室里又发出一阵窃笑声。教授原来也是风格各异啊!
王老师上课不苟言笑,娓娓道来有条不紊。印象最深的是讲到屈原的《离骚》,快接近收尾了,他问同学们:“要不要听我吟唱两段?”“要!”大家异口同声回应。待教室里静下来,他用浓重的湖北乡音抑扬顿挫地吟唱起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一边吟唱,一边在教室讲台前踱来踱去,眼光望望课本又不时地扫视着同学们。那吟唱声低沉婉转,回环往复。直到下课铃响停止了唱诵,我们才从屈子激昂的情感中苏醒过来。几年后,我在一个小县城里听说王凌云老师在文革中被隔离审查,他竟然割腕自杀了!在那个红色恐怖笼罩的岁月里,他是深感人生理想遭遇毁灭,对世道彻底绝望或不堪忍受人格的屈辱而追随屈原去的吗?我无法想像那是怎样一个惨烈的情景。得知那消息,我只是默然呆坐了好久好久。
心仪“闰土”
我们除了上课,经常有一些政治学习,就得往男生宿舍跑。要是平时,誰会去那地方!男生住文华楼二楼一个大教室,一、二十张高低床由蚊帐隔开一个个的小单元,看上去很是凌乱。班上的男生特爱给人起外号,大概是我这人大大咧咧、蛮里蛮气地搞惯了,没多久我的“蛮子”外号就叫得山响。一上楼就听见有人数落:“小蛮子,炸丸子……”我听了,一点也不在意。
男生多数来自专县,我觉得有个郧阳山区来的穿草鞋的同学显得格外扎眼:他圆圆的脑袋,圆圆的脸,脸膛红红的,眼泡似像有点肿,眼睛细眯成一条线,黝黑的上身穿一件月白色土布小马甲。看到他,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鲁迅先生《故乡》中所描述的在金黄的月夜,一望无际碧绿的西瓜地里,手执一柄钢叉刺向猹的闰土,他就只是缺了颈上的银项圈和手上的钢叉罢了,他叫孙天富。我心仪他的憨厚拙朴,就在心里叫他“闰土哥”。这也算我给男生起的唯一一个外号了。
一日,又逢政治学习,走进男生宿舍,见闰土哥正盘腿坐在下铺缝补衣服。做针线,这哪是男生干的事!我就立马凑上前去说:“让我来给你缝吧!”原来是条蓝褂子上挂了一个三角口子。他一声没吭,把衣服递给我。我坐在床边很细心地飞针走线,不一会就缝好了。递给他,他还是没吭声,只是眼睑抬起了一些,朝我略微笑了一下。我发现他的细眯眼睁大时,眼仁还是蛮亮的。
几天后有同寝室的女生取笑我给男生补衣服。我说:“这算什么!帮忙是应该的!”她说:“你以为你很行啊,你一走人,他就把你缝的拆掉了!”
噢,原来如此,呜呼哀哉!这真是:蛮子妹多情献殷勤,闰土哥冷意毁针线。笑料一桩。
墨水炸弹
张庭芳,湖北蕲春人氏,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人也长得矮小,貌不出众,大家本该叫他“小老弟”,可不知怎的却得了“小老大”的雅号。他人小鬼大雄心在,时而也会闹出些笑话。
进校不久,小老大想看看武汉三镇面貌,从学校徒步走到汉口最繁华热闹的江汉路一带,在交通路口古旧书店旁,看到有一家正在推销大约两斤装一瓶的减价墨水,五毛钱一大瓶。看这价码着实划算,他掏出二元,买了四瓶。心中喜滋滋的:习练书法,来日方长,且不必操心再研墨了。
小老大舍不得花钱乘车、坐船,用两只手各挟持两个大墨水瓶,匆匆往回赶路。走了一程又一程,从汉口到汉阳再走上长江大桥。岂知远路无轻担,早就累得大汗淋漓,手指酸疼,忍无可忍。站在大桥之上,望滚滚长江东逝水,感天地之苍茫浩瀚,念个人之力微无助,那就减轻负担扔掉一些吧!他于是举起一瓶墨水朝江中扔去,看着它自由落体没入了黄浊的波涛,然后提着三瓶墨水继续走,走了上十米,无奈地又举起一瓶扔下去。正在目送那墨水之际,忽然听到背后一声大喝:“干什么的?不许动!”转过身来,原来是个荷枪实弹的守桥战士地从桥头跑过来,正拿着枪,比着他。
“你在扔什么?搞破坏啊!”
“扔墨水呀!怎么了?”小老大指了指脚下那两瓶剩下的东西:“就是这一样的。”
“你还不老实!跟我走!”
“真是闖了鬼!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小老大自己嘟囔着,他心中十分镇定,自己是被人误会了,眼下也只有自认倒霉,跟着那个大兵朝龟山下的守桥部队驻地走去。
一到驻地,那大兵就报告一个尉官说:“这家伙在桥上扔炸弹。”
“你胡说,我扔的明明是墨水瓶!我是华师中文系的学生,哪来的炸弹!你这不是冤枉人!”
那尉官问明了原委说:“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守桥驻军决定派一潜水员潜入江下,去打捞起那两枚疑似炸弹,以辨明真伪。
小老大在武汉三镇转悠了几十里路,正好在一间小房里坐等结果,歇歇脚。过了一、两个小时,疑似炸弹被捞起,经验明正身为“过期墨水”。小老大终得放还。小老大笃志高远、勤学不怠,孜孜以求,不谋官职,几十年弹指过去,成为当今戏剧家、书法家、收藏家之集大成者,是我们班上成就最高、最有出息之人,此是后话。
(薛晴,1964年入中文系。武汉铁路技术学院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