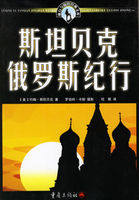天霞把奶头从小树叶嘴里抽出来,慢慢系着衬衫的扣子,胀鼓鼓的乳房似乎比男人头顶上的灯都炫目。男人这几天成了台机器,只晓得坐在堆满布料的工作台前做活做活不停地做活,人本来就不很舒展,这下更显老相,有点像他们甘家洼老火山坡梁上的老头杨了。那张脸呢,因为少了风吹日晒,村里人惯有的黑是没有了,却白得寡淡,看上去像新刮了腻的墙。
天霞心一沉,捅了一下男人的后背,柔声说,上去晒晒吧,都几天没挪窝了。
男人茫然地回过头来,好像没听懂她在说什么,半天才开了腔,你去吧,抱上小树叶,我还得赶活儿。
天霞摇摇头,小树叶,你就知道个小树叶。
男人笑笑,又拿起剪子咔嚓咔嚓剪开了。天霞不肯走,往他身边移了移,固执地,几乎是要挤进他眼窝里了,挑衅似的说,真偏心眼,你从来就没说过让我出去晒晒,就知道你家小树叶。她是你亲骨肉,我算什么?就是个给你做饭洗衣的吧?男人怔了一怔,渐渐地,脸上的笑一波一波荡漾开来,你也是啊,小树叶是我小女儿,你是我大女儿,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心坎坎。天霞伸手打了他一下,你还有精力油嘴滑舌?走吧,上去晒晒。
男人摇摇头,我哪顾得上,你快去吧,多站上一会儿。
天霞不满地说,嫌我烦了吧,嫌我站这儿妨碍你了吧,走就走。
男人说,哪有啊,想看你尽管看。
天霞瞪了男人一眼,别以为自己有多好看,我才不想看你呢。就抱起小树叶,在脸蛋上夸张地叭唧叭唧亲了亲,又举到头顶在屁股蛋上亲了亲,这才朝外面走去。过道里黑糊糊的,天霞咳了一声灯就亮了,灯虽然亮着,她还是觉得自己像只地老鼠。走了几步,她碰到了另外两只地老鼠,是住在隔壁的一对男女,男的大块头,东北汉子,三句话不对就动手,揪着女的的头发往墙上撞,房子隔音不好,她在这边能听到咚咚咚的撞击声。厮打过了,过不了一会儿又会亲热起来,弄出一些暧昧的声响。往日,这一对人总是回来得很晚,也不知今天怎么就早早回来了。又走了十几步,她遇到了住在斜对门的那个身材高挑的女的,每天这时都会背着一件歪把子乐器回来,进了屋便悄没声息的,安静得像一片树叶。至于别的老鼠出去干什么,回来又干什么,她就不甚清楚了。可她知道,这些地老鼠多数不像她男人一天到晚守在地下室,他们白天去有阳光的地方做活,到了晚上才钻进来。
想想,他们搬进这里也有几年了,男人学的是裁缝,最初还能揽一些活儿,做成件衣服的不能说多也不能说少,反正是够他忙乎的了,后来业务就稀稀落落的,寻上门的多是些修修改改的零碎活儿。顾客也多是附近的居民,知道她家男人手艺好,脾性也好,衣服有问题就拿了过来。隔壁最初住着一对河南夫妻,替人看管自行车,后来存车子的越来越少,就卷了铺盖走了。她和男人商量了一番,把这营生也揽了过来,还是没人来存车,就也不做了。
爬上一层,再爬上一层,天霞和孩子就升到了地面。
阳光劈头盖脸打在她娘俩儿身上,天霞不由得眯起了眼睛,她怀里的小树叶也眯起了眼睛。多好,多好的阳光啊,天霞心里感叹着,全身的细胞似乎都张开了嘴,像要把这满世界的阳光都吸进肺腑里,灌进身体的旮旮旯旯。马路上的车多得数不过来,刷的一批过去了,又刷的一批过去了,永远没有过完的时候。天霞盯着马路,她怀里的孩子也盯着马路,两腿踢腾着,她知道孩子想下来,就把她放下了。孩子需要多走走,这样面条似的柔软,将来又怎么上学呢?
小树叶就生在这地下室,生下来好多天没见过太阳,她不敢抱出来,怕受了风。一直到孩子十个月头上,天气转暖了,她才敢抱到外面来了。也许是少晒了太阳,缺钙,孩子走得就迟,都一岁几个月了,走起来仍踉踉跄跄的。说话也迟,只会说几个简单的字,比如,要,不要,吃,不吃,冷,不冷,抱,不抱。她也去诊所给孩子开过一些钙片,吃了后效果并不怎么好。医生笑笑说,你多带孩子晒晒太阳,这是最好的药方。天霞本来要断了孩子的奶,想想终于没忍,反正她也没工作,想吃就吃吧。
刚把孩子放下,小家伙就张开两只手臂朝马路那边跑去。天霞心里不由一惊,赶紧追上去把她抱在了怀里,箍得紧紧的,任她怎么踢腾也不肯松手。闹腾了半天,孩子乖了点,目光移向她们身后不远处的饭店门口,那地方不知什么时候新添了两个又高又大的花瓶,特别惹眼。天霞就想,这饭店就是肥,门口都摆这么高这么大的花瓶,里面又摆了多少好东西呢。这她就不知道了,她从没进里面吃过饭,有时男人也逗她,要不我们进去吃一顿?天霞就摇头,你有多少钱啊,吃上一顿不过了?她知道那不是他们去的地方,他们最多去马路对面的小餐馆吃顿饭,就是小餐馆也不敢常去。
他们的腰包很瘦,这城市,这个叫北京的城市却很肥,路上跑的都是明晃晃的小车,跑得不是很畅快,隔不了多久就吱地停下来,有时停不了多大一会儿,有时又一堵就是老半天。
天霞再把目光转向饭店那边时,台阶上已坐了一排溜年轻人,都是这饭店的服务员,有说有笑的,有几个把手机捂在耳朵上,不停地说话,也不知在跟家里人还是朋友说。天霞站在这边,常常看到这一道风景。那些年轻人自然也会看到她们,有几个姑娘有时会走过来,抱抱小树叶,学着她的样子亲亲小树叶的脸。天霞怕她们把孩子捏弄疼了,就教她们怎么抱,这样啊,对对,托住屁股蛋,揽住腰,对对就这样啊。几个姑娘就学着她的样子抱,还给孩子当姨,小树叶,叫姨啊,小树叶,叫我姨啊。她们睡的也是地下室,每天这个时候就会坐在台阶上晒太阳,像一排灿烂的向日葵。天霞知道,再过一会儿,他们就会回到饭店里面,各就各位,有的下厨,有的端着盘子在厨房和餐厅间来回跑,有的像蓄足了阳光的向日葵立在过道上。
这风景是很让天霞开心的。
这么看着,天霞一回头,看到身旁多了个人,是一个村出来的小雪。天霞假装很生气地说,小雪你怎么这样啊,过来也不吱一声,吓了我一大跳呢。小雪没吭声,脸色有些阴沉,像是有什么心事。天霞心里一咯噔,她这是怎么了?这时,小树叶探出两只小手,姨、姨地叫。小雪好像没看到,脸上依然没一点亮色。孩子受了冷落,两条小腿踢腾起来,两只手固执地探向她。天霞就笑了,小雪,小树叶想让你抱呢。小雪勉强笑了笑,把小树叶抱了过去,虽是看不出多少亲热,孩子还是咯咯咯地笑了。孩子吃得好看,脸胖嘟嘟的,下颌重了呢,手也胖嘟嘟的,手弯像带了两个肉镯子,腿也是胖嘟嘟的,脚弯也好像带了两个肉镯子,谁见了都喜欢。
天霞觉出了什么,问,你没事吧小雪?
小雪摇摇头。
天霞说,不对,你肯定有心事。
小雪眼里忽然有了泪。
小雪几年前就到北京打工了,学理发,因为原先有些基础,加上心灵手巧,没一年就出了徒。师傅也就是她现在的老板,便让她带了两个徒弟负责了一个分店,离这条街也不远,最多几里吧。有次天霞去剪发,转来转去就转到了小雪的理发店,两个人谁都没料到能在北京碰上,那叫个亲热呢。小雪和她的徒弟也住在地下室,只是房钱由老板出。
天霞更急了,有事你就跟姐说呀。
小雪说,我爹让我回去,说是给我说了个对象,让回去看看。
天霞就笑了,我当你遇上了啥事,你也该找对象了。
小雪摇摇头,才不找呢,我还不想回去。可是我爹每天打好几个电话呢,打得我都烦死了。
天霞又要说什么,听得小雪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就把小树叶抱过来,让她接。小雪哦哦地应承着,挂了电话说,真不好意思啊天霞姐,我们老板马上要过来,我得赶回店里去。
天霞说,有事你先去忙,晚上过来吧,我们请你吃个饭。
小雪冲她笑笑,天霞姐,能过来我就过来。
天霞说,一定过来啊,姐等着你。
小雪点点头,朝马路对面匆匆走去。
天霞一直目送她的背影消失在了人群中。再回过头时,饭店门前那一排溜晒太阳的“向日葵”也都不见了。
天霞忽然记起了什么,就也抱着孩子回,孩子小脚踢腾着,不肯走。天霞说,听话,该把你爸叫出来晒晒太阳了。孩子依然在闹,小腿一踢一踢,小手一抓一抓的,脸涨得通红。天霞也不管她怎么闹腾,加快了脚步。孩子哇地哭了。天霞就责备,惯坏了,真是把你惯坏了,一点都不懂得疼人,就你知道个晒?你爸要是弄下毛病,将来谁养活你?孩子好像给吓住了,慢慢地安静下来,就像风刮过后的小树。
回到了地下室,天霞看到男人还坐在缝纫机前忙活着,两只手旋着布料在机针下一点一点走,那张脸比刮过腻的墙都白。天霞把孩子往床上一扔,腾地立在男人面前,眼睛似乎要冒出火来。男人愣愣地看着她,你怎么了,遇上啥事了?天霞说,都是你害的。男人眼睛睁得越发大了,我怎么了?天霞没好气地说,还嘴硬?你说你怎么了?男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你说明白点,我到底怎么了?天霞说,你不顾着我,也得为小树叶想想吧?男人还是不知自己犯了啥错,呆头呆脑地看着她。天霞憋不住笑了,瞧你这傻样,去晒晒吧,你要弄下毛病,让我和孩子将来怎么过?
男人一跺脚,神神道道的,我还以为我犯了啥错呢。
天霞说,真要生了病就迟了。
男人摇摇头,腾地站起身,倔倔地出门。孩子受了惊吓,又哇地哭了。
天霞忽然喊住了他,等等,我娘儿俩也陪着你去。男人有些不耐烦,却还是等了天霞,一起出门。
一家人升到了地面。
这已经是黄昏了,挂在楼谷间的夕阳像个熟透的橘子。
天霞看到男人脸上满是橘色的光晕。就说,你看看你,嘴撅得能拴头驴,你说我让你出来是害你吗?男人摇摇头,脸上渐渐有了笑。天霞说,这不就对了吗?多晒会儿太阳对你没坏处。男人说,我这不出来了吗?天霞也笑,出来就好,你看这太阳有多好呢,我们甘家洼的太阳比这更好。啥时回去看看呢,回去了也像我嫂子月桂,气气派派地晒太阳。
男人说,你想回去,你嫂子可是想跟着你哥出来呢。
天霞点点头,也是啊,她真有这个想法呢,她是不知道城里的难啊,不知道我们做梦都想回去晒太阳呢。
男人叹口气说,乡下我们躺在炕上也能晒太阳,可是没钱花,城里我们住地下室,却有钱赚,这世上的事真是说不清啊。
天霞忽又想起了小雪,就把事情跟男人说了。男人摇摇头说,小雪也到了出嫁的年龄,她爹三铁匠也是为她好呢。再说,这事我们怎么管,根本就管不了。天霞一撅嘴,你这像个当姐夫的说的吗?就不能宽慰她几句吗?三铁匠那人我知道,眼光小着呢,他哪懂得小雪的心思。男人说,可是我哪有那闲工夫?你不知这几天人家催着跟我要货吗?天霞说,你怎么这么没情没义的,就差这一会儿工夫?回去不能加个班?男人苦苦一笑,那你说怎么办?
天霞笑了笑,好办,我们请她吃个饭吧。
男人头摇得拨浪鼓似的,吃饭,你是说请她下饭店?
天霞说,是啊,别看离着也不远,咱还真没请她吃过饭呢。
男人说,可你选的日子不对啊,你不看我这几天忙?
天霞故意说,我看不是忙,是你这当姐夫的小气,不舍得,钱都拴在裤带上了,一分钱也不舍得花。
男人就有些急了,谁说我不舍得啦,请就请,我请她还不行吗?
天霞就笑了,这就对了,我知道你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