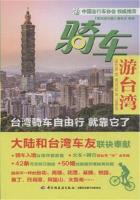溜出村口,我心里就瓦蓝一片了,就像头顶上的天。
再回过头看,我家的窑院悄没声息的,连树头上的麻雀好像也安静下来了。我和我妈吃午饭时,这些小东西还捣蛋得厉害,先是在电线上叽叽喳喳吵,后来一只突然骑上了另一只的腰背,下面的那只挣扎着反又骑到了上面,两只撕扯了半天,呼地钻到院当中那棵老柳树的头发里打闹去了。我跑出去挥着手吓唬了半天,它们才不再恋战了。这会儿我妈肯定还在睡,要不然早追出来了。
我正这么看着,从沟对面的塑料棚后转出了一个女孩,是麦子。
一看麦子在这里,我就知道她爹王铁成又在跟村长喝酒了,她肯定是给打发来看棚子的。王铁成原先跟我爹一起给城里人盖楼房,可他吃不下苦,两年没干满就跑回来了。回来后就在村口搭了这个棚子,成天待在里面侍弄鸡,来买鸡的都是些开车来的城里人,据说是因为他的鸡不吃饲料,是绝对的绿色环保食品。我以为这下他要发大财了,可麦子说去年他爹没挣了钱反倒折了本,我说你家的鸡一只卖八九十块,比天鹅肉都贵,怎么能赔了呢?麦子说,棚子里进了黄鼠狼,一口气吃了不少鸡。
我看了麦子一眼,扭身就跑。
清华你跑啥跑呀,等我一下。麦子在沟那边喊。
一听她这么喊,我跑得就更欢了,脚下好像踩上了哪吒的风火轮。麦子也在黄家洼上学,从前年村里的小学塌了锅,我们就都转到那里了。一开始,一起跑校的还有五个,麦子、小叶、铁蛋、三喜和我,可今年一过年,除了我和麦子,他们都转到城里或镇上上学去了。我和麦子相跟着走了半个月,班上就有人起哄说我俩好上了,偷偷摸摸搞对象呢。我觉得这很丢人,不管我妈和王铁成怎么说合,就是不跟麦子结伴了。
太阳像个大火盆,烤得我腰背火辣辣的,都快冒出油来了。
跑出老远,我以为万事大吉了,一回头,发现麦子早爬上了坡沟,顺着水泥路追上来了。我们村的人把这沟叫浮石沟,沟里到处都是烧得发黑的浮石。我想我得甩掉麦子,不能让她跟上来。水泥路的左侧有个小山包,山上有一片杨树林,我看了一眼便耗子似的钻进去了。进了里面,我找了棵树坐下来靠着喘气,隐隐感到树叶在颤动,好像是风在枝条间走动。我又透过树梢的缝隙往北边的狼窝山看,一团团棉花云正往山顶上爬,云团有些破旧,好像是让墨水弄脏了。我眼一眨不眨地看着,一团粉红突然飘了过来,挡住了我的视线。
想躲我?没门儿!那团粉红咯咯咯地笑起来。
一听这声音,我就知道是麦子来了。她脸跑得红扑扑的,像一棵开花的桃树,手里还捧了个饭盒。
你就是躲到天涯海角,我也能找到你。麦子又说。
我心里叹了口气,只能自认倒霉了,我想你这个麦子呀,你怎么就这么不知轻重呢?你不知道他们拿我和你瞎编排?我想说她几句,可是看着她红润的嘴唇,又不知说什么了。班上都有人说我亲过麦子吃过她的嘴了,我捧着麦子的脸,吧唧吃一口,又吧唧吃一口,吃得她的嘴都发黑发紫了。
我又看了一眼麦子的嘴,我想,吃嘴一定很香很有滋味。记得快过年时,我爹从工地上回来,捧起我妈的脸就大口大口地吃,越吃两个人的身子挨得越紧,简直像胶在了一起。我爹边吃边说,饿死了,月桂你不知道我都快饿死了。我妈摇了摇头,要吃快点,孩子一会儿就该放学回来了,当心让他逮着,逮着了看你这个当爹的脸往哪搁?我爹嬉皮笑脸地,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得饱饱吃一顿。说着就要把我妈往炕上抱,看他那样是要抱到炕上大吃一顿。一听他这话,我憋不住笑起来,其实我早回来了,要不是门在里面插着,我肯定会撞进去把他们逮个正着。听到我在窗外笑,我爹我妈倏地分开了身子,脸都成了红布。
你怎么老看我的嘴?麦子说。
谁说我看你的嘴了,你的嘴有什么好看的?
说是这么说,可我心里又不能不承认,麦子的嘴确实好看,不光嘴好看,眼睛、眉毛、鼻子、脸上的酒窝都很好看,跟她结伴走,你会忍不住多看她一眼。这么一眼一眼看下去,我的魂魄很可能会给吸走。奶奶活着时,常跟我唠叨,说好看的女人都是狐狸精,能勾走你的魂,勾走了你就没精气了,只能坐在墙根下晒太阳了。我想,麦子这么好看,肯定就是奶奶说的那种狐狸精啦。我不能让她勾走了魂,我得好好上学,考到北京考到清华去。我爹每次从外边回来,总是瞪着眼睛说,小兔崽子你要不好好念书,这辈子就算完了,就得跟着老子去工地上搬砖,把你受个死。
我的嘴不好看,你老看我干吗?麦子又说。
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没看你也不想看你。
你爱看不看,反正我是跟定你啦。麦子嘻嘻一笑。
你真赖皮,你是个赖皮的狐狸精。
我要是个狐狸精就好了,就谁也不怕啦,还用得着跟你?一个人去黄家洼上学也不怕啦。
一个人走怎么了,又不是在城市,谁会绑你的票?就算在城市也没人绑你,咱村的小凤不是给警察抓了吗?
我不信她会干绑票的事,打死也不信。
信不信也给抓了,她肯定干了坏事。
不许你这样说小凤姐,你不知道三铁匠多伤心呢。
麦子说着在我身边坐下了,手里仍紧紧捧着那个饭盒。我屁股不由往一边移了移,又在我和她之间画了根道道儿。麦子大睁了眼睛,这是在野地呀,在野地你还画道道儿?教室里我们的课桌让你画了,出了野地你还要划?你以为你有多香?我冲她笑笑,我就要画怎么啦,男生女生不得划清界限吗?麦子看起来很不服气,又往我这边蹭了蹭,说你想画就画,反正我就要超过你画的道道儿,超过了你又能怎样?我摇了摇头,心说碰上这样赖皮的狐狸精,谁都没一点办法。
你拿这个干吗,晚上不回家吃饭了?我指了指她的饭盒。
怎么不回家?不回家晚上我住哪儿,怎么吃饭?你给我做呀。麦子说着又咯咯咯笑起来。
谁给你做呢,我问你带饭盒干啥?
是我妈让我给老师带的饭。
我哦了一声,我妈也让我给老师带过东西。老师一个人住学校宿舍。
她男人在县城工作,平日里也见不到个影子,每到了周末,才开辆半新不旧的桑塔纳回来。可最近,老师的男人好像不怎么来了,听同学说,他好像又在外面找了个女人。那个女人很年轻很好看,是个狐狸精。老师肯定也知道这事,可她好像没一点办法,有孩子拖着,她还不想离婚。听说老师也想往城里的学校调了,要不然,她的男人就要被那个狐狸精吸尽精魂,再也找不回来了。我不明白大人们之间怎么那么多的事。
你知道吗,今天是老师的生日。
老师的生日?你连这都记得?
我当然记不住了,是我妈记得,我妈说你们老师今年肯定还是一个人过生日,我们得表示一下。
你妈真好。
我妈当然好啦,我爹也好着呢。我妈本来要给老师吃炸油糕,让我爹拦住了,我爹说麦子的老师喜欢吃莜面饺子,你就做这个吧。
看不出你爹这么心细。
那当然啦,我爹说,咱们这么做,其实也是为了麦子好。要是麦子的老师不高兴调走了,黄家洼学校肯定也得塌锅,到时谁知道她又会给撤并到哪个学校去?我爹真是为我操碎了心。
我不由想起了我爹,他这会儿肯定还在脚手架上忙乎呢。听说那座城市的好多楼房,都是我爹他们那个包工队盖起的。我问过我爹,我说你们盖了那么多楼房,你怎么不分一套呢,也好让我们搬进城里去。我爹说,这你就不懂啦,盖楼房的人都住不起楼房。就算真给我分上一套,咱们也住不起,得交水电费、煤气费、卫生费,这费那费的,你爹挣这几个可怜钱交得起吗?我爹又说,知道爹为啥给你们兄弟俩起了个清华北大的名吗?就是希望你们好好念书,将来都考个好大学,分到城里上班去。
对了麦子,你爹又在跟村长喝酒了吧?他真会享福,喝酒吃肉的。
我爹不是会享福,是村长找上门要喝的,他是村长,他说要喝酒,我爹总得给他个面子吧?
村长去你家喝酒,你爹肯定给炖了鸡肉吧?
我爹才不舍得呢,他还等着拿卖鸡的钱给我们换房子。
我知道你爹是个小气鬼,可是村长去了,他总不会连只鸡都不舍得杀吧?
村长人好着呢,他才没那么多讲究,有口酒就行了。
我想想也是,村长人还真的不错,就是喜欢喝口酒,喝醉了不是回家睡大觉,就是站到戏台上给人们开会。没人听他也呜哩哇啦讲,谁也听不懂他都讲了些什么,就像来了个外国人。一开始,还有人过来看看,后来就没人看了,瞅着他上了戏台,老远就躲开了。只有他的小皮还算听话,乖乖卧在台下当听众,尾巴一摇一摇的。小皮要是不听,老甘就会照着它的屁股踢一脚,边踢边说,你这个同志,你怎么不听村长讲话?
村长真好笑,我见过他出酒疯抱着小皮哭呢。他的女人跟上野男人跑了,他一定是把小皮当成自己的女人了。
这我也知道,我就是不明白她的心怎么这么狠,连小羊小驴都不要了。真是个狠心的女人。
还不是因为村长没钱嘛,男人没钱,女人就不稀罕他,就会找个野男人。
才不信呢,我爹也没钱,我妈还不照样围着他团团转?
你爹确实没钱,就会喂个鸡,离着二里远就能闻到他身上的鸡屎味,我看你妈迟早会嫌弃他,跟上野男人跑的。
臭嘴,你妈才会跟野男人跑呢。麦子生气了。
也就逗你几句嘛,还生气了?问你个正经话,要是黄家洼学校也得撤,再撤到张家洼,你还上学不?
不上,不上了。麦子使劲地摇了摇头。
为什么不上了?
这还不简单?你老是躲着我,不跟我相跟,你说我一个人还敢上?再说我是个女娃,我妈说了,女孩子就是不上学也能找个穿衣吃饭的地方。
你呢,清华你还上不?
肯定还得上,我要不去上,我爹会把我打死。我爹说了,你是个男娃,将来不光要养活自己,还得养活媳妇孩子,要是念不成书,考不上大学,还怎么养活一家人?
你将来还要娶媳妇?羞死人啦。
谁说我要娶媳妇啦,我不娶,我将来要么一个人过,要么和我哥过。我哥上次回来说,他也不打算娶媳妇,他发誓要当个作家。他说写东西要专心,什么都不能想,娶了媳妇麻烦事就多了。
什么?你和你哥过?你们一个清华,一个北大,两所大学过日子?你爹真会给你们起名呀。
那当然,至少比你的名字好,麦子麦子,多土呀。
你有多洋啊,不跟你说话了。
不说就不说。